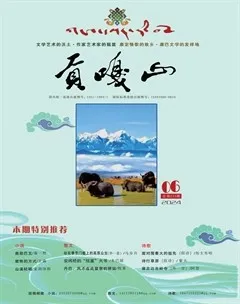每个人都在困境中

我曾是个货真价实的结巴,差不多有十二三年的时间都不能完整地说一句话,母亲总是提醒我,开口之前先把话在肚里过一遍。我照做了,我敢保证,每个字词被我吐出之前都是完好的,有规律的,有秩序的,可一旦跑出来就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所以,我不得不紧闭嘴唇,拒绝吐字表演。
如今我已经能够流畅地用语言表达一切,滔滔不绝时没有人会相信眼前的我曾是个严重的结巴,但我深知,那段经历影响之大,直到现在,我对口字旁和言字旁的字全无好感,觉得说话是体力活,常因说话过多而感到疲惫不堪,看见肚大口小的坛坛罐罐,有种同病相怜的压抑感……所以,我常会一整天不愿开口,打车时以写纸条的方式告诉司机目的地,掐灭朋友打来的电话——最后这点,希望我的朋友能够理解,一个曾经数年结巴的人偶尔会犯一犯说话厌恶症。
小时候,母亲常担忧结巴的我以后能干啥工作。谢天谢地,我现在所做的事竟与嘴巴没有什么关联。写作和绘画,构成我生活的主要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不爱说话,我才慢慢走上写作与画画这条路呢?
记不清是哪一年开始画钢笔画的。前不久老家翻建,回去收拾旧物,发现我的小学课本上空白之处都被自己涂满了,当时竟没有老师对我进行过批评,或将我画画的兴趣扼杀在摇篮里。大学时候,我读了建筑专业,专业全称为《建筑施工与管理》,偏理论,没有绘画课程,唯一和画笔有关的是画建筑图纸,用的是针管笔,从1.5毫米到0.1毫米粗,笔细到令人抓狂,性子但凡急躁一点,笔就不下水,我的好脾气大概就是那时候锻造出来的。
2013年,我一意孤行离开熟悉的建筑行业,开始所谓的理想追求:写作。这一行为被身边的人认为是脑袋进水。在此之前,我是一名建筑工程师,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在小城的建筑界里小有名气,那时正写长篇,工作很轻松,大多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辞去工作。我的理由是:一个人只能专注做好一件事。这句话很管用,重音落在“好”字上,它让家人不再反对,并对我有了一点憧憬,尤其是我的父亲。其实,我知道是自己内心对建筑行业的厌倦和抵触。那时候小城到处都在拆迁,重建,或者拆迁后荒芜着,待建的瓦砾中小草胆怯冒出来,我的内心会感到疼痛。人们那么热衷于摧毁,重置,将一切归零。我感到无比焦灼、无奈,写作让我变得越来越悲悯,让我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兴高采烈地去工地,春笋一样的楼群使我无比厌恶,看着和我一样进城拼搏的农民工们,他们白天像长臂猿一样在脚手架上自如攀爬,夜晚钻进鸽笼似的工棚,他们像是这个世界的新生物种,我的心底涌起阵阵悲凉。
毫无疑问,辞职后我过得不太好,因为从原本收入颇丰的状态跌进了一贫如洗,一点积蓄因借朋友而发生意外,我称那时的自己正经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对“困难”“苦难”“难处”等词极为反感,可以想见,我对自己名字里的“难”字又是多么深恶痛绝。
那几年,我写了一大批短篇小说,主题都与苦难有关。虽然自己的生活还没到达穷困潦倒的地步,但执拗地认为自己就是底层人民的代言者。这让人既感到高尚,又无比沮丧。那些小说赚了读者一点眼泪,同样,写作过程中我也常泪流满面,搞不清究竟为小说人物命运还是为自己,生活越拮据,越容易被感动,于是想想路遥,想想卡佛,觉得自己正离伟大的小说家们越来越近——我是指贫穷这一点。
现在仔细想想,画钢笔画大概就是那时候开始的,从苦行僧一样的写作状态里抽离出来,拿起笔,在白纸上随意行走。如果写作是对自己现实生活的精神救赎,那么,画画就是对写作的拯救。钢笔画一脉相承地延续了小说里的“困境”,那些现实生活里不被看见的角落,被彰显,被放大,被重新审视。破瓦、颓墙、断壁、枯树、石块……无一不在告诉我,每个人都处于困境之中。
我将自己的钢笔画称为涂鸦,的确,对于画画,我还是门外汉,我只是试图在繁密的线条中寻找自己的语言。沉浸在钢笔画的密密排线里,内心十分宁静,我又可以像小时候一样,紧闭双唇,拒绝说话。那些排列有序的青瓦,层层叠叠的青瓦,从秩序里跳脱而出的青瓦,旁逸斜出的青瓦,偶有破碎的青瓦……不正是我未说出口的词句吗?
曾有人问,你为什么总画这些颓废景物?为什么不画画新建筑,不画画新农村大瓦房呢?我对此付之一笑,从不作答。有人看到的是倾颓,有人看到的则是倾颓之下的坚固。再者,小瓦更具有东方建筑美学特点,在我眼中,它不仅仅是建筑材料,它还具有禅意,是境界,是修行,是轮回,是生生不息,是清静寂定,是叩问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