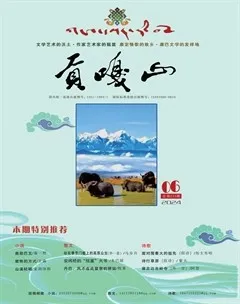马铃芋的春天
一
女儿出生一周左右,我在她一阵阵或是饿了的提示性娇啼,或是醒后不甘安静无声造声的轻哭,或是躲在被窝洋洋自得宣告存在感的哇哇声里,恍然懂了事理——我得努力再努力地为她挣口粮钱去!
虽然其时妻子的奶水比较丰盈,但从电视广播广告上可感受到,六个月断奶后,即便普通的分段分档奶粉,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当时,年前秋天刚操办过我与妻子的结婚喜酒,眼面上春耕开始,柴油、化肥等农资筹备,口袋只剩几十块钱积蓄的事实,总让我脸红心跳。女儿的降临,给了我巨大的幸福、希望和干劲。小小的人儿,会在我和妻子的谈话中,睁开眼睛,瞅一下,然后张开小嘴继续她那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的哼哼唧唧。每每这时,我的压力感倍增。这是1997年4月,我——个年逾三十的青年农民,在自打锣自唱戏,历经艰难盖了房子、娶了妻子、成为父亲之际,在将田野中七八亩承包地全部犁翻泡水之后,忽然动了要做生意挣钱的念头。实事求是地说,这事一半起因于我囊中羞涩,一半源于坐月子的妻子懵懂天真的诉求。那天她柔柔地说:“顿顿吃着不放盐的炖鸡汤,红糖拌米面,胃里泛的清水都快流成小河啦。大哥啊,能不能换个花样,譬如,马铃芋上市了吧,要不你烀些马铃芋给我换换口味可好?”
马铃芋是我们这里的方言,就是马铃薯,更大众的叫法为土豆。但这看似寻常的蔬果一枚,实现起来却并不轻松。妻子之所以认为此乃最简单不过的要求,是她脑海里有个误区。她娘家在无为长江中间洲岛上,距离这里有两百里路程。这里,有必要将我个人境况潦草介绍一下。因为家境贫寒,我是弟兄三人中的老大。年届二十八岁时婚姻事依然没有着落。乡谚云:“三个儿子急死之,三个女儿吃死之。”二十八岁那年夏天,我在上海某工地打工,妻子同学的姐姐、姐夫与我同一个工地,浦西工厂上班的她周末去工地玩,我们四目相碰,擦出数点火星。其后,我与她从相识相谈进入两情相悦阶段。如此交往三年,她顶住外界诸多压力与干涉,执着与我走到一张日历下过日子。她嫁过来尚不满一年,还不清楚我们这里是圩区,因为地势低洼、土质板结,从来不种马铃芋。而她娘家的江洲沙地及她大姐家所在的长江北岸三坝埂边,皆是适宜马铃芋种植的优质沙性土壤。月子里的她,以为自己想吃马铃芋,不过是一种呼之即来、唾手可得的日常菜蔬而已。而现实是,我们圩乡人想吃马铃芋,只能到离村庄七八里路远的集市去买。当然,集市摊位上的马铃芋也是菜贩子从外地批发而来,物以稀为贵,刚上市时段价格六七毛钱一斤。
我骑着自行车从集镇菜市场买回来十五斤。母亲问花了多少钱,我说十块。母亲说:“你真舍得,这能买三斤多猪油呢,买个两三斤吃新鲜不就得了,明明手头紧,还这般糟蹋钱。”当得知是她坐月子的大儿媳想吃,她马上收起絮叨,脸漾春风,小跑着去了我们房间,先亲一阵她的“心心尖”孙女,然后斜坐床边,温言细语与我妻子拉呱:“坐月子人哦,尽量不吃生冷腥咸辣类东西,还有芋头芋脑类作物,这些东西吃下作气,听话哦姑娘,忍一忍啊。当年我生你二叔、三叔(我二弟、三弟),就是馋嘴没忍住,吃了烀山芋,如今落下个嗝酸水、烧心怪毛病,每逢下雨、刮风作天变,那难受,胸口像有千万只手在抓在挠。”妻子将信将疑点点头。下午,隔壁婶娘来串门,她将这个话题求证,得到的当然是同样的答案。为让她彻底相信,我到有座机电话的邻居家,打电话给她大姐。她大姐家隔墙是代销店,店里有公用电话。通常,店主二贵子站家门口喊一声,她大姐就能听到。
她大姐让我捎话给她这个娘家人最惯最疼的小妹妹,说这个讲法都这么传,真真假假她也拿不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呗。“我坐月子那会儿,就被婆婆管着这不能吃、那不让吃。所以你还是劝我阿妹忍几天吧。”后来大姐又说,“这几天晴空大好,我们村庄家家在起马铃芋,你们要是喜欢吃,抽空过来一趟,只要你能拖得走,要多少装多少,这马铃芋没淋雨、没破皮也经得住囤,等阿妹(我妻子)满月,让她吃个够。”
“大姐这样豪气啊,当真要多少装多少?那我带个卡车过来装呢?”我打趣道。
“这真不是开玩笑,带个卡车过来,包你不放空。每家地里落下的,你捡个几片地,肯定能捡上半卡车。”
后来她说到关键点:今春天气回暖快,雨水顺调,马铃芋比往年成熟早,产量高,却馕市不值钱。贩子们到地头来收,头昂得老高——一块钱六斤,每百斤折秤五至十斤不等,反正都由他们信口喊价。随着往后越来越多人家开挖马铃芋,这价格怕是还要往下跌。
那一刻我一激灵,突然嗅到商机。她那里不到两毛钱一斤,我们这菜市场目前卖六七毛一斤,我装个一车回来,不说卖六七毛,就算卖四毛、三毛,不都有两倍、一倍利润?扣去杂七杂八的费用,怎么算都有得赚吧。
撂下电话,我三步并作两步赶回,告诉妻子,我要做生意,我要为咱宝贝公主挣奶粉钱去。妻子看我打了鸡血的样子,也是一脸兴奋,但几秒后她蹙眉说:“你在菜市场又没有摊位,你装回来在哪儿卖呢?”
“这个你不用愁,我们队里二伢子在菜市场开冷库,我们是穿开裆裤发小,我找他合伙,在他家门面边弄块场地不就行?”我答。
菜市场见到二伢子,当我说出那边收购价,二伢子惊讶、呆愣好一会儿。或是不那么相信,或是嫌马铃芋季节性生意时间短,赚头不大,他踌躇片刻后告诉我,他家冷库生意也即将进入旺季,马铃芋差价虽然美丽,奈何他腾不出时间,也抽不出人手来。但他热情地将我带到离他家不远,拥有连体门面、摊位的蔬菜批发商老徐那里,说你们俩谈谈,老徐家专做蔬菜批发零售,他搞这类比我内行。
我将无为那边地头收购价再绘声绘色重复一遍。我看见老徐的眉毛迅疾跳动一下。
“一块钱六斤,折秤另算,怎么会这么低呢?”他狐疑地盯住我眼睛。我听懂这里的“低”指收购价。
“那里是沿江大棚蔬菜产地,土质适合种这个,农户在田头低价卖,省得来回搬挪,好腾出时间与精力点种下一茬玉米。”我把大姨姐在电话里跟我说的复述一遍。
“你大姨姐那里马铃芋有我这里个头大、色相好吗?”老徐忽然一扭脸,指着他摊位上的马铃芋问。
我瞄一眼他的菜摊,凭往年在大姨姐家看到的马铃芋印象,拍胸脯答:“在地头刚收上来大小不均,小的与你这里差不多,整体而言,大的比你这大,她们那里是沙质土,马铃芋外观椭圆淡黄,较少丑垃疤害(方言,形容物体形状怪异丑陋)的,色相上眼。”
又聊过几句,老徐说:“这样吧,你用我店里电话,给你大姨姐那边再打一次,问问现时价格。新上市蔬菜,批发价一天一变,这个要搞准,打不得半点马虎。”我知道老徐还是不放心,他要亲耳听到产地那边讯息,便掏出小笔记本,找到大姨姐家隔壁代销店号码打过去。
店老板二贵子接的电话。他说:
“你大姨夫一家人下地起马铃芋去啦,这会儿大门掩着,家里没人。你有什么事跟我说,我回头转告他,或者叫他按这个号码回你。”
我在犹豫怎么回答,老徐朝我做个手势,让我按下电话免提键。
“哎……老板你好,我是刚才打电话的张兄弟朋友啊,我们想问问你那边马铃芋现在收什么价格,可方便告诉我们一个准数呢?”老徐身姿略作前倾,对着话机说。
“一块钱六斤,加上折秤什么的,估计每斤只能卖到一毛三四样子。唉,今年收成起来,哪知卖不上价。”二贵子话里夹着叹息,可以想见,他家马铃芋也种得不少。
“车子可以开到地头吧?譬如收满一辆141加长大货车,大约需多长时间?”我看见老徐脸上已泛起按捺不住的喜色。
“你要是确定来,给个大概时间,村里人家按你的时间点提前下地,你们来了就过秤,一小时老牌子(方言,轻松、完全之意)收满一车。”二贵子已然明白我们打电话的目的,答得越发详细,音调里甚至鼓动着诱惑。
挂了电话,老徐眼里放出光彩。
“小张,今天来不及啦,这样,我马上联系车子,明天你带路,我们叉伙(合伙之意)干。明早五点动身,到那里上午十点左右,先搞一车回来探探路子,可照?”老徐说。
“磅秤和本金你不用烦神,你只须明早准时到我这集合就行。”老徐不愧是菜市场历练出的生意人,从我脸上一个短暂飘忽,看懂我一时拿不出本金之涩,大大咧咧表明态度,慷慨解我后顾之忧。虽然第二天到达无为江边三坝埂——我大姨姐家村庄所在地泥汊镇后得知,有我大姨夫担保,那里的马铃芋可以“一趟压一趟”(今天一车现货赊账,明天过来付今天的欠款,如此循环)付款,但我仍然对老徐充满感激,第一次心血来潮做生意,不说遇到贵人,至少遇到了大好人。
翌日凌晨,我步行从家往集镇菜市场赶。三十出点头年纪,精力旺盛,脚劲足,七八里路程不见多累。沿途吮吸红花草沤烂后的泥臭、微风里裹挟的刺槐树花香,极目东边红色朝霞,放眼路两边水墨画般田垄田块,感觉这个春天里的一切都那么美好、清新、可爱。
哥做生意啦!某一时刻,我甚至张开双手,在小跑中恣意地喊出声来。
二
车子径直开到大姨姐家门口。
我从车上跳下来,刚晾完衣服准备下地的大姨姐好一阵惊愕。
本来早上动身时,我说打个电话通知大姨姐一下,让她多备点中饭菜。老徐摆手道:“不打不打,人还未动身就麻烦人家。虽是亲戚,怎么好让他们破费,到了看情况再说。”我想想也有道理,便依他。
大姨夫的母亲,我之前按妻子叫法喊“阿姥”,如今我们有了孩子,我改口喊阿奶。
阿奶在露出和大姨姐相似的惊讶表情后,很快将我们迎进堂屋,拿来茶叶、拎来水瓶给我们泡茶。老徐与车主师傅都说自己带了杯子,不用麻烦。然后,阿奶站到门口,朝通往田野的村路口大着嗓门喊:“你们谁带个话给我家二宝,就说他妹夫小张带着车子收马铃芋来了,叫他回家一下。”
二宝是我大姨夫的小名。无为东乡一带,习惯依照孩童在家中排序称呼他们“大宝、二宝、三宝”。也就十来分钟时间,大姨夫风风火火赶回。而这时,阿奶也从灶间端上一大碗热气腾腾的茶叶蛋,招呼我们吃。
老徐吃完一个茶叶蛋,折身出门去了二贵子家代销店,买回几样糕点和一箱娃哈哈AD钙奶,递给阿奶,说:“我们早上走得急,空着手来的,也不知买啥,您老人家别见外,这些给您孙子吃。”
阿奶顿了一下推辞:“瞧你们这客气,都是亲戚,还讲那些礼节干啥?”老徐说:“这不第一次来吗,后面还有得打扰吵闹哦。”言毕,轻轻将东西放到客厅边沿一个靠墙椅子上。
中饭菜很丰盛。大姨姐不光杀了一只自家养的鸡,还在代销店门口卤菜摊买了当地特色板鸭、肫爪、卤干子。饭桌上,大姨夫喊来陪客的堂兄弟老三格外引人注目——那遮住耳根的长头发便隐隐折射出一股“混家子”的不羁。几杯酒一喝,我和老徐方知道大姨夫的良苦用心。原来,老三真是他们这一带的“狠人”,农闲时出门,在外面工地给老板看场子,帮包工头管理工地,农忙回老家帮父母侍弄田地。四围村庄中,但凡有他不入眼之事,他总要闹出一些动静。当然,那个年代乡间有句俗语:“弟兄三四个,有个搭僵货。”严格来说,这些“搭僵货”们的处事方式带有一点霸凌性质,但他们本质不算坏,亦懂得“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在家门口一亩三分地上,对家门口人较少嚣张作威,某些时候还会为家门口乡亲利益挺身出头。所以,那段时间乡村土壤上,他们这类人,往往是让人既爱又嫌、不能认同却又不敢得罪的存在。
大姨夫在酒桌上对老三说:“三老板,这是我小妹夫,也就是你小妹夫,他们到这来收马铃芋,有把握不住的地方,你可得要罩着。”
老三将杯中酒仰脖饮尽,大着嗓门答:“兄弟
啊,我,你还不知道吗,跑远了我不敢讲,小张妹夫在泥汊江边这一带,遇有滋事的,告诉我,看我不喝唏(方言,训斥、怒骂之意)他!”
然后,借着酒劲,老三把自己两天前将一辆外地收马铃芋车子打跑的经过慷慨陈词一遍。其内容大致是那车子收货过程中,见地头马铃芋忒多,他们根本收不完,便将折秤数字不断放大,从五斤捅移(逐渐移到)到十五斤。本来这也没什么,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后来有农户表达不满,说那收货人不厚道,派人在路口拦住别的收货车不让进,自己在田头狠狠杀价。那收货人嘚瑟,报出县城东门因打架刚从监守所放出没多久的混混刘二疤来壮势,说刘二疤是他老表。
话至此处,老三一拍桌子:“他奶奶的,就这句话,把老子火惹上来。刘二疤算个球,人狠要狠在理上,他在东门怎么咋呼我管不到,把他名号往我们这儿搬,你唬谁呢?”
后面内容大约是,老三喝令那收货人,要么继续按每百斤折秤五斤收,要么立即将车开走,不许阻挠外地收货车进来。结果是,那车主没敢回嘴,拉着大半车货怏怏离开。
故事讲到这儿,老徐起身离开桌子,讲自己喝得有点多,去门外吹吹风醒醒脸。也就几分钟时间,老徐又轻步回堂屋,坐到自己座位,自上衣口袋拿出两包红梅香烟,恭敬放到老三桌面,说:“三老板,初来贵地,我们在这收货,你得帮我们照应着啊。”
老三抬眼看向老徐:“你这是干啥,小妹夫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这边你尽管放心,不会有人为难你们。”
老徐说:“三老板别误会,这里我们不熟悉,不知哪些人抽烟,哪些人不抽,这个呢,就麻烦你帮着散一散,可中?”
老三闻言,一抬胳膊:“好,话说到这份上,我就揣起来,帮你们散一圈。一会儿开磅,该怎么折秤就怎么折秤,新起的马铃芋见光少三斤,见风吹三斤,做生意起早摸晚不就是想挣两个,所以五斤、七斤折头你们定,但秤上面得规规矩矩,不能有猫腻哦。”
老三话音落,用眼扫了一下老徐的脸。
老徐响亮地答:“这个你放心,我这磅秤你们可以校验,是从国家计量局下属门市部配的。”
我所坐位置后背朝门,无意中回头,看见门外好几个人在张望。从他们沾有泥土的裤脚和鞋可看出,应是从地里起马铃芋回来的农户,在询问开秤时间及价格。
饭后到屋后小便时,我遇到从厕所出来的老三。老三将嘴凑近我耳朵,声音低低地说:“刚来这边收,那个搞秤(从磅秤或秤砣上设置机关,扣斤少量)悠着点,别太离谱就中。”
我一恍惚,没明白啥意思,老三已晃晃悠悠沿着后门小路走远了。
我把这话说给老徐听,老徐也愣了一下,而后点点头:“我心里有数了。”
下午只花两个小时多点,我们的车子便收满。我们开出的收购价沿袭之前来这里收货贩子们的价格,一块钱六斤,折秤为每百斤折五斤。
三
夜路满载车开得慢,回到家乡集镇市场,已是晚上十点多。在老徐家摊位前卸完马铃芋,等货车师傅离开后,我问老徐:“你下午说的心里有数是啥意思?”
老徐扫一眼四围,压着声说:“这三老板是混家子,更是明白人。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开秤半小时,拉马铃芋来的板车并不多,后来突然排起长队来。开始那半小时,起码有三四家,在家中或田头已称过斤两,他们挑出那些袋口扎起来的袋子码到一块,分明是在试探我们的秤有没有水分。他们回地里一宣传,我们的秤规矩,观望中的农户闻言纷纷下地开挖,货自然多起来。”
“那是,我们明里折多少就折多少,绝不会昧着良心去玩那见不得人的伎俩!”我笑道。
老徐忽然停住要接的话,目光在我脸上扫描一阵,半是叹息、半是给我上课说:“小哥哥,别太天真,一年中一大半日子不是天真热就是天真冷。也别那么多顾忌,老话讲,生意场上无父子,不搞点花样,一不留神就白忙活了。”
本来我想摸黑回家一趟,老徐说:“我这儿折叠床、被子都有,你今晚就在我家摊位边凑合一夜。明早天放亮我们还要从整堆马铃芋中挑一些大的出来,分成等级卖。销得快的话,我们明中午再带车子去你姨夫那里,这样后天不会断货。”
这话俱在情理中.我按下回家想法。铺开折叠床睡觉前,我看见二伢子门面里灯亮着,踱过去,他正按着计算器算账。我委托他回村庄时,帮我带几套换洗衣服来。
“呵呵,看来这马铃芋还真有搞头呢,老徐要带你大干一场呀。”二伢子笑道,“行,我老婆明中午回家,我跟她说。”
老徐清晨来摊位时,我已收好床铺,在菜市场厕所水池处刷完牙、洗好脸。
老徐从小山样堆放的马铃芋中,示范地拣出一些圆滚滚、个头大的马铃芋,说:“你照这个头和形状,挑一些出来,放大堆子边,一会我写个‘精品马铃芋’牌子,这种按七毛一斤零卖,剩余大堆子按一块钱三斤批发,五块钱起批,不给挑选,你负责拿方口铁锹装袋往秤上放,我收钱加记账。”
分等级卖,精品马铃芋受少数高要求客户青睐,又可在对比中衬托出大堆马铃芋价位划算。老徐生意人的头脑果然厉害,这撩人心、通人性的策略,让我心服口服得为其竖起大拇指。
一块钱三斤的价格很快在菜市场传开,需要买马铃芋或者跟风哄抢的顾客,在老徐家摊位前排起队。老徐家摊位上蔬菜品种很多,他老婆与一个雇来的小丫头也不时给我和老徐帮忙。十一点钟光景,除却挑选的小堆精品马铃芋还有三分之一,大堆子全部卖完。后面没买到的人几乎都要问一句:“明天还有马铃芋批发吗?”老徐亮着嗓门乐呵呵地答:“有,有,七八点钟上货,来迟了可就不一定有啊。”
一些常在老徐家买菜的饮食店及单位食堂客户,干脆撂下话,让老徐帮他们五十斤、一百斤地预留。某个间隙我听见,老徐对他老婆说:“下午我们走后,万一来了急要货的食堂、饭店及做红白喜事配菜的老熟客,可将剩下的小堆精品给他们,价钱按大堆子批发价收。”
四
中午在老徐家里吃饭。老徐开了一瓶酒,与我边喝边聊。他说:“兄弟,这里没外人,我把这车货的收支简单盘一下。我们在那里收上车是五千五百六十斤,回来实际卖出四千八百斤,加上没卖完的精品马铃芋四百来斤,也就是说,斤两上我们将那边折秤捺进去,还折掉三百多斤。这你恐怕没想到吧?当然啦,你大姨夫和老三家的一千多斤没有折秤,可其他四千多斤都是按一百折五斤收来,按理怎么也得超出两百多斤才对吧?我不瞒你,幸亏我带了一个大砣(做过手脚,可扣斤少两的砣),货收到后半车,我用这个砣在秤上扳回百来斤。即便这样,我们依然没填平斤两上的窟窿。那老三是行家子,和你说那话,意思是叫我们在磅秤里适当做点手脚,不然重量无法持平,归根结底,是刚出土的马铃芋折头太大。”
老徐一席话,让我哑在那里。折头这么大,我没想到。老徐早有准备,带去一个扣秤的大砣,我更没想到。一个看似简单的低价买、溢价卖的小本生意,居然牵扯进这么多弯弯绕。老徐接着说:“一会儿司机过来,我们先到县城计量局门市部,重买一个新磅秤。然后,你在车上陪司机聊天,我到塔山街一家私人配秤店,再配两个大砣,我们今下午不求多出斤两,起码要保住不折吧。”
虽然我心内对使用大砣极为抵触,总觉得这行径不道德,有龌龊负罪感,但这是合伙做生意,老徐是主心骨,容不得我反驳。
“兄弟,我家在菜市场,衣食起居比你轻松,你想你这起早摸晚地,不挣两个,对得起你这辛苦吗?”老徐看我不言语,缓了口气似安慰我,也像给我洗脑,“当然,秤上有眼,你姨夫和老三家我们不能用大砣。”
再去已是轻车熟路,下午三点半,我们的车直接开到马铃芋较集中的田块。这次动身前,我们打了电话,地里用蛇皮袋装好的马铃芋摆放得很多。不少人家正用那种手拉长柄铁犁,在加快速度翻犁泥土。无一例外,马铃芋甫一出土,每家都是疾速装进袋子里。我想起老三的“见风少三斤,见光掉三斤,沙沙土土再三斤”的提醒,懂得农户们这样操作,无非求得斤两多一点。同为种地农人,我能理解土里求财不容易。但此刻,身份转换,作为收货方的我们,无疑要承担更大的折损风险。
最先开秤的农户称过两磅后,从家里又拉来一板车,说是昨天傍晚起土的,放在家里堂屋。老徐笑着说:“好,好,统统带走。开饭店还怕大肚子啊,越多越好,越多越好。”
收货是我记账兼付款,司机站车上码袋子。老徐的手则在磅秤上一排大小挂砣之间,游刃有余地切换。
果然,开始几磅,每次秤完,稍留意,便可看到有人打眼色给过秤农户,过秤农户要么轻点头,要么微摆手。
很明显这几磅是测秤的!老徐的超前感知能力及娴熟的称秤手法让我又惊又怕。怕什么?怕他不小心露馅穿帮,也怕他将这本事用在我们后面卖货上。
这车货装满比我们预计的时间快,虽然动身迟,赶回集镇卸下马铃芋,也才凌晨一点的样子。我仍然在老徐家摊位边用折叠床打发了几个小时。由于昨天放出消息,人传人、话赶话,从菜市场开门,摊位前买马铃芋的人便络绎不绝。和昨天相同的批发价,同样是到十一点光景,大堆货全部售罄,挑拣出来的小堆比昨天略多一些。
老徐取出钱盒里五十元、一百元的大票子点一遍,再对照收货斤两粗略估算,不无得意地向我使个眼色道:“把昨天斤两亏空补起来啦。”
我明白,这归功于老徐一手运作的“大砣”功劳。
但不知为何,我高兴不起来,心里莫名地涌起一股对老徐,也对自己的嫌弃和厌恶。
五
老徐再次到货车司机家联系出车回来,满脸不悦。原来司机家人说,司机已经出车,叫我们另找别人。也就是说,司机在未打招呼的情况下,违背了之前一直帮我们拉货的口头约定。
也是这会儿,老徐老婆插话道:“你们只顾着在这边忙,西边零散地摊市场那里,今天也有人在成堆批发(马铃芋),我刚去看过,价格与我们相同,品相也差不多。看来,市场里有车子跟你们后面去那地方了。”
“千算万算,算不到人心深浅。估计有人出高价,让他(给我们拉货的司机)拉货兼带路去了。张兄弟,这马铃芋生意看来也快到尾巴啦。我另外去找车子,今下午再搞一趟回来,能否做得下去就看这趟啦。”老徐言毕,脸上喝酒时的兴奋一扫而光。
因为老徐老婆的提醒,副驾驶座位上的老徐,一路不停地留意倒车镜。过无为县城,他往椅背一靠,嘀咕道:“这哪里是收土豆啊,简直就像去捡金豆子啊!跟了这么多车,好几个车牌号我都认得,毛估猜,今天从我们那开过来不下七八辆。好生意硬是做成烂狗屎了。”
果然,到达泥汊江边马铃芋产地,收货车比往日陡增。我大姨夫村庄周边的马铃芋基本卖完,我们将车子停到与他家相隔三个村庄的地块。收货中途,离我们大约一百米地方,半个小时内又来两辆车,搬出磅秤开收。
收满这车货时间明显变慢。返回时从那两辆车旁经过,老徐朝其中一辆车磅秤处喊了一声:“李二泡,你怎么知道来这里的?”
“老徐啊,不是我说你,你不地道唉,有钱大家赚啊,你那几趟怕是赚肿了吧?”那个叫李二泡的并未正面回答老徐的问题,而是打着哈哈以责怪的口吻回怼老徐。
老徐也不生气,笑笑说:“呵呵,明天,明天你们就知道有多大赚头啦。”
这一趟,我们回到集镇菜市场接近凌晨两点。没料到的是,货未卸完,哗哗下起中雨。任凭我们怎样抡圆胳膊加速卸货,后半车马铃芋依然被淋湿不少。老徐拖大雨布时叹道:“看样子这车货一毫赚头都没啦。”他回屋睡觉前对我说,“张兄弟,晚上尖心点,雨停了,就要把雨布撤掉,让里面淋水发烧的马铃芋透透风。还有,明天不用分拣,统统以大堆货批发,但中饭前一定要卖完,这块地方下午要放东西。货卖光我们吃个散伙饭,把账算算。”
雨一直下到天亮才停,揭开雨布,马铃芋大堆上果然冒出淡淡的白雾,间或飘出一股腥臭异味。扒开堆子,可看见一些有伤口的马铃芋正在变色腐烂。
老徐来了,眉上打结道:“还是那句话,中饭前能卖掉就卖掉,卖不掉就处理掉,我等着这块地方摆其他菜。我刚在菜市场转了一圈,至少多出七八家在批发。”
“既然这样,我们是不是再降一些价来卖?”我请示老徐。
“都这个价了哪能再降,你是搞几趟就收手,强如玩玩,我们可是长年累月靠卖菜谋生,价格杀狠了这后面怎么卖?这样吧,但凡批发十斤以上的,你另外加送他们一铁锹,看可能抢点人气过来。”
上午,前几日排队景象忽然不见,我视线所及这一排门面,能看到三家商户在吆喝批发马铃芋。从品相可以断定,都是尾随我们车子在无为江边收回来的。
昨夜那场雨,给我们的马铃芋造成不小损失,但对我们圩乡的早籼稻秧苗栽插却是利好,从菜市场顾客的交谈中可得知,不少人家秧苗开始栽插。这时候,赶早上街买菜的人也比平时多。我家村庄的邻居们大约都知晓了我在集市卖马铃芋这事,纷纷绕到我这里看看,顺带称几斤。我想起老徐“十二点卖不完,宁愿往垃圾堆倾倒,也不能过低价售卖”的警告,既心疼也来气,索性自作主张,对所有来买马铃芋的家门口邻居,买多少送多少。在一旁收钱记账的老徐脸拉得老长,但他最终忍住不悦,任我这发神经举动继续。
即便如此,十一点半,马铃芋还剩四分之一。我对老徐说:“剩下的不卖了,我把小的、烂的剔出来扔掉,其余的我包辆三轮车,拉回去自家吃。”老徐吃惊地望望我:“这个淋过雨,算算还有不少,回去不能搁放,你在搞笑吧?”
“好歹也算做了回生意,回家给亲戚、邻居都送点。”我笑笑回。
老徐不再言语。吃过中饭,老徐将这几趟马铃芋的成本及开销都做了详细说明,其中包括磅秤、秤砣、送我大姨夫家的礼品,还有老三、货车司机及他自己抽的香烟,我们路上垫肚子的方便面,等等。关于磅秤,老徐说这个他留下,大抵与我拖回家马铃芋尾货价钱相持平。最终,我们每人盈利五百六十元。
与老徐打过招呼,我包了一辆三轮车将未卖完的马铃芋拖回家。出集镇一里来路,我看到一辆卡车装着马铃芋在倚路售卖,一块纸板上写着“马铃芋批发,十元三十斤”。擦车经过时,我瞅出卖马铃芋的人竟然是前两趟给我们拉货的卡车司机!
回到村庄,我让母亲把装回的马铃芋,每家分送四五斤。然后顾不上与妻子多交谈,卷起裤筒下地整田。其时,因妻子坐月子,我母亲是山里姑娘出身,不会插秧,两个弟弟一个上学、一个在外面打工,我只能把所有田地整好,择个日子请邻里及亲戚帮忙栽插。
插秧那天上午,当我拖着一板车秧把子送往圩中心田块,远远看到田里插秧的人超出我请来人数一倍多——村庄一大半人家都派了人手来打暴工(无偿帮忙)。
六
秧苗活棵后,我前往苏南建筑工地打工。我知道,我那份挣不脱的书生气,注定我不是,也不能成为做生意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