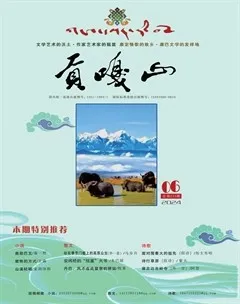山溪轻唱
一
和旦巴通过电话的第二天,我就买好了去往J县的班车票。
旦巴说,那年大地震后几个月里,工程队冒着余震的风险抢修出了一条小车车道通往省城。自从班车停运后,这条路上就有了近百辆越野车往来颠簸。这些“野猪儿”差不多是车况还行的二手车,开车师傅熟悉山路,都把车子开得被猎狗追着的野兔一样快。通话时,我就想象着那些疯狂的“野猪儿”在满是泥泞的坑洼道上如何跳跃着飞奔。
我知道自己是个一生都充满幻想的女人。这个性格影响了我的一生。
下了出租车,客运中心在半明半暗的天色里有些恍惚。昨夜脑子里幻想虚构的即将经历的场景还没散去,这让自己在这闷热的夏天生出了一些倦意。
客车亮着车灯在高速路上安静而快速地行进。时有灰暗的杨树和铁塔在后车光线里一晃而过,看不见更远的地方。不记得上一次坐班车是多少年前了,仿佛遥远得没了印象。这么早的赶赴,是一种充满期待的冲动吗?久违的感觉,让我一夜无法入睡,就像第一天入学,就像第一次拆开大学录取通知书,就像和他步入婚礼现场的前几分钟。
然而,一切都很快归于平淡。平淡的生活,平淡的婚姻,平淡的自己。
我渐渐认为,生活其实没有好坏之分,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往往就是一种抵消。工作上的业绩抵消了婚姻的不幸.精神自由的理想抵消了世俗的热闹欢愉,而内在的感性却无法让自己做到不悲不喜。在儿子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们都到了离巢的时候。以后的日子,将不再时时刻刻相互陪伴。
儿子要和同学去看大海,而我要去的地方却有些遥远——种潜意识里的遥远。
旦巴的家乡,离我所在的省城其实只有三百多公里,却要进入真正的大山深谷:要从狭窄的高山脚下蜿蜒盘旋近百公里,然后翻过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峰。这才是最近的遥远。
客车下了高速继续向前行进,只是弯道逐渐多了起来,天空显出微蓝,看得见山的轮廓。
隧道上方和左右亮着的彩色光带在无尽地扩张,却总是不见尽头。我感觉自己正在时间里穿行,不知道起点和终点,也不知道将在哪里停留。
他是我们年级男子篮球队的中锋,1.88米的高个儿,五官俊朗,这在大学校园,足以引来众多女孩倾慕的目光。那个时候的陈伟,自信、阳光、帅气,骄傲得只剩下了自己。
我不在最漂亮女孩子的队列,也不喜欢那些热闹张扬的场合。大学三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阅读,特别是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我在中文系班主任的引荐下也读过一些基础哲学,但只对周国平的文字情有独钟。我不喜欢高深莫测、绕来绕去的理论,只希望永远惬意地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即使是一些描写苦难的作品。
在大三进入实习期的时候,我没有挡住陈伟不舍的追求,与他建立了恋爱关系。大家都不明白,一直受女孩子追捧的陈伟为什么会喜欢上寂寂无闻的我——也许是厌倦了那些女孩子不加掩饰的虚荣和张扬,或是他后来告诉我的那样,他是被我安静内秀的气质所吸引。然而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因为谁也无法预料将来的变数和命运的指向。
班车从几公里长的隧道驶出时,一阵凉风突然就吹走了都市的喧哗与躁动。道路两旁的山势突然拔高,班车行进在河床右方的狭长公路上,向着没有尽头的深谷钻了进去。就像当年的我,一头就扎进了命运布好的婚姻陷阱,再也看不清远方的路途。
大学毕业后,我们被分配到了省城同一所知名的中学,我教语文,他教体育。一年后我们登记结婚,再一年后有了儿子东升。
他一开始就不甘心在操场上伴着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了却一生,更不甘心天天在这种没有光环只剩清贫的日子里耗费自己。他执意下海经商,要去创造自己都没弄明白的前途。
我知道他张扬飘浮的个性并不适合做生意,但还是没能劝住他。
后来,我最初的担心都一一兑现了:他不但亏完了我们的积蓄和亲友的借款,还吃喝嫖赌沾了个遍。那几年的我,除了努力工作,还要一个人把儿子抚养长大。
那个时候,我才发现爱情和婚姻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命运在把我认为最美好的东西撕碎给我看。
好在只要是我当班主任的每届学生都特别争气,总能在各个方面为我拔得头筹,让我还保持着一点仅剩的成就感,觉得生活还不算太糟糕。这些学生和儿子东升差不多是我最大的慰藉和支撑。
二
我从来没有奢求过自己的生活要有多少的浪漫和激情,反而在学校时我就规划过自己的将来:简单、平凡、自由。虽然对陈伟越来越不抱任何希望,但我依然努力维系着家的完整,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学习和成长。直到他把外面养的那个女人带回了家里,还说她是他生意上的合伙人。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也不止一次反省过自己:是自己不温柔、不体贴?还是自己矫情、固执,不懂得忍让?其实一切恰好相反:正是自己无底线的忍让和迁就,助长了他不知收敛的无能和无耻。
没有打闹,没有争吵。我选择心平气和地结束这段婚姻,而且必须与他割舍干净,从自己的生活和记忆里。
这么多年过去了,过去的我就是一个活在灰色童话里的小女人。如今的我已然中年,却仍然怀揣着少女时代的那点理想和浪漫,还是时不时地让自己活在梦幻里。
天是深蓝的,比大海还要蓝。晨阳斜洒在河谷右岸,纯净而炫目的阳光仿佛来自另一个天堂般的世界。好久没在这样干净透明的光亮里再现自己了,过去自以为看见的光亮,在此刻竟然退缩到了记忆的背后,显得黯然失色。也许我从来没有被真正的光明所照见。
在经历了婚姻的失败之后,我曾按自己的理解,把生活简化到了自以为的朴实无华:教书育人、陪伴孩子、阅读思考。这是我当时的疗伤手段,也是不让自己快速沉沦和堕落的最佳方式。
都市生活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诱惑,而深觉失败的自己,有着更加入骨的孤独和难耐的寂寞。在伤痛开始结痂时,我也尝试着开始新的生活。经同事和亲戚介绍先后与一名医生、一名公务员和一个小老板相处过。最终只有那懂得人心的建材老板和自己维持了半年关系。
理想和现实总有着无法逾越的距离。也许是我对生活太过理想而不得吧,此后的日子,我便不再对此抱有更多希望。想来,命和运,缘和分,从来没在我的身上结合一起吧。
儿子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我也放缓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开始上网关注一些优秀的博客和帖子。那段时间我认识了两个好友:何莉莉是个娇小的美女,小我十二岁,是一家装修公司的美术设计师;另一个叫葛雅的与我同龄,小我几个月,是省城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我们三个属相相同,爱好相近,何莉莉和我一个小区,葛雅也相距不远。
我们常常约在清静幽雅的地方喝茶、聊天、闲逛,渐渐满足于这种简单、自由的生活方式。我不再把目光投向虚无的天际,同时也放弃了对未知远方的好奇和向往。直到葛雅说到了旦巴。
葛雅说,她是无意中看到旦巴的博客并被吸引到的。没想到一个普通的藏族同胞有那么高的汉语言修养和朴实精准的文字功底。她一度认为,这是一个生活在涉藏地区取了个藏名的汉族文化工作者。她感慨地说,我们固有的成见证明了我们的无知。后来我们三个都成了旦巴的粉丝,他的博客每次更新,我们都是第一批读者,他的文章往往会成为我们聚会时谈论的话题。
坡度明显升高,发动机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从车窗向外望去,车子已经爬升了很高。道路的护栏下方是大雾弥漫深不见底的谷底,远处是顶着千年积雪的群山峰顶。我似乎忘记了现在已是盛夏,昨晚的我还在开着冷气空调的房间里失眠。
班车在“之”字形的盘山路上又绕了几个弯道,眼看就要接近峰顶了。这时连绵的群山只露出了白头青衣的峰顶,无边的云海和远处的蓝天白云连接在了一起。我们曾在旦巴博客的相册里见到过相似的景致。
翻过五千多米海拔的山顶垭口,道路向着下方以连续的“之”字,向远方山谷延伸而去。手机已经两三个小时没有接收到信号。人就这样,在繁闹的都市待久了,就会想着走出去,去享受一份诗和远方。不过,孤独的时间一长,自己又会害怕起来。
班车转过一道山梁,在远远望见一个镇子的时候,手机有了信号,我也接到了旦巴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他在下一个镇子的路边等我。
客车被前方招手的人叫停,旦巴和他爱人素梅在这里接到了我。他俩在镇上一家小店请我吃的午饭:一只铜火锅里煮得香软的腊肉、松茸和干野菜。
我们三人都是第一次见面。我这次出行有些突然,旦巴在接到我要到J县的电话时犹豫了一下,还是告诉了我不能全程陪同我的遗憾。他说最近要到州里参加一个教育方面的交流会。我当时在电话里告诉他,这次出行就是想一个人随意地四处走走。我说的是出自心底的实话,到了这里最好的体验方式就是凭着直觉去经历和感受。多少年来,我渐渐迟钝的灵魂,不敢有任何期盼和奢望,更不想此行带上任何功利性的目的。
旦巴懂了我的意思,说是会给我做一些安排。
三
和店老板道别后,我坐上了旦巴的面包车。他简单介绍了给我规划的行程,说是一切都可以根据我的决定调整。
面包车向着河流北岸的山林行去,山势高耸,树林浓密,高处的山林间还隐隐环绕着轻雾。我还在四处张望的时候,车子开进了公路护栏外一个小路口,穿过几棵大柳树间的小道,一面有几个足球场大小的纯净的湖泊出现在我们前面。旦巴说,这里山林间的湖泊都被称作海子。
眼前的海子里,倒映着蓝天和绿树。海子边上无数的鱼群仿佛在蓝天、绿树间游走。
旦巴夫妻从车里取出几张白面饼,撕成小块往湖里投喂。素梅递给我一小袋饼干,我也学着他们把饼干投向湖边鱼群,引来鱼群挤在一起翻滚争抢。旦巴告诉我,这里的鱼只能投喂,不能捕捞,海子对藏民来说是神圣的,在这里高声喧哗很容易引起落雨或者冰雹。
海子中央的水面光洁平静,像一枚蓝宝石镶嵌在浓郁的山谷,又像一面神秘的仙镜照见了我的前世今生。我想,也许我的前世定有一些罪孽和不堪,不然怎会有今生如此的不幸和缺憾呢?失败的婚姻是我今生最大的不幸,而陈伟正是我前世的冤孽。十多年来,我何曾真正绕开过他对我一生的影响呢?我到现在依然认为,婚姻的不幸对一个女人来说就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湖面无风,却有一股清凉轻抚着我的脸庞,滋润着我的双眸。守在静谧无声的海子旁,我生出了一种想哭的冲动。我是什么时候到过这里的呢?我搜索着荒野般的记忆,旦巴和素梅没有打扰我的出神。我记得旦巴曾在一篇散文里说:“都市人的心底容易堆积尘土和杂念,唯有大自然或者宗教般的情感可以洗涤。”
离开海子,旦巴和素梅陪着我继续向着山里行进。沿途的公路左侧下方有一些草坪,散落着三三两两游玩的人。经过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寨子后,我们继续向山腰密林行去。
旦巴说,我们现在所处的山林,就是当年红军翻越过的第一座大雪山,当然现在这座“雪山”只有隆冬的时候才会堆积起一层积雪。越往上,车子就像穿行在原始森林里,道路两旁都是几人合围的巨大松杉,枝头挂满了灰绿色的木须丝苔。
整个山林都散发着杉木和松林的清香,让人觉得心肺和精神都洁净舒张了起来。
不记得多少年没有这种感觉了,自从陈伟自甘堕落以来,我不管怎么装出没事的样子,都无法掩藏内心压抑的苦楚——看不到爱情,看不到未来,甚至看不到自己将来的结局。我的境遇在同事眼里是不幸的,我一直试图用平静和安然的日子去加以掩饰,也常用伪装的状态给学生们传递更多的愉悦与成长。唯独一个人的时候,竟不知如何面对自己。
面包车停在坡道旁,我们在道路上方的灌木丛里采摘了不少黑色树莓和草丛里黄色的野果,那是我第一次尝到过的独特而细腻的香甜味,是高海拔山林独有的味道。再往上走,我们就越过了山林,在接近山头散落着碎石的山坡上,开满了雪白和粉红的野生杜鹃花,一大片一大片地连接着下面的山林。
第一次置身于深山,第一次走进原始丛林,我从心底感谢旦巴用心的安排,让我感觉这一两个小时里,就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光阴。
此时,我由衷地生出了被自然沐浴着的感恩,感恩活着,感恩生活赐予的经历,包括那些自以为的不幸。
在接近山头的碎石沙砾间,旦巴让我亲眼看见到了真正的雪莲花。它仿佛由翡翠白玉雕凿而成,却突显着出尘的高洁和孤独。我没有伸手触碰它,生怕惊扰了它此时的修行。
我们来到人世间也是一种修行吗?我在心里问自己。
山顶有风无雪,我披上了自己带来的厚外套。第一次在连绵的青山之巅远眺,第一次沐着高原的山风回望。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也在此刻发现了自己真实的存在,我的那些过往,我的那些不幸和伤痛,被阵阵山风吹得支离破碎。
能不能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就一个晚上,我诚恳地说。
旦巴一愣,和素梅对视一眼后就开心笑了起来。他们耐心地给我解释了山林里的各种利害和危险,直到此时,我才被自己的无知和天真惊到了。
旦巴说,外地游客到了这里多数都很好奇,会把一切都想得非常美好。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太羡慕你们了,天天生活在这个神仙居住的地方。其实哪有那么好呢?他说,他们多数人都在物质、金钱里埋得太久,只是想暂时换个环境透透气或者休整一下心绪而已,他们并不了解山林生活真正的清苦和艰辛。
好在旦巴和素梅能够理解我的异想天开。他们商量了一下说,可以实现我的部分愿望,同意把我放到朋友家住上一两天。旦巴说,格西的家就在我们经过的海子上方二十多公里处。从上山经过那几家寨子到现在返程,手机一直没有信号,旦巴开玩笑说,格西大哥能不能收留你还不知道呢。
回程时,山林里的光线已经暗淡起来,气温也越来越低。旦巴打开了车里的暖气空调。
四
车子刚驶出树林就向路旁一个斜坡拐了上去,经过一段稀疏的灌木林,就到了一处山坡洼地。天色已经黄昏,眼前的牛棚子由青石垒起,上面盖着灰色的石棉瓦。
牛棚子四周不平整的地上散落着一些石块,一半埋在土里,一半露在地面,在黄昏的光线里若隐若现。一条黑影从墙后窜出跳动起来,传出几声粗犷的吠叫和铁链碰到一起的声响,接着一个高大的人影出现在棚子前面。
格西收短铁链,把那只黑色藏獒牵到了墙后。他掀开黑色的牛毛毡子把大家引进了棚子。牛棚子里的火塘吐着红红的火苗,在一股暖流包围过来的同时,我的眼睛也被木柴的烟雾熏出了眼泪。格西的爱人颁玛起身给我们让座,让我坐到火塘边一个矮长木凳上。他们的儿子达娃穿着短袍坐在火塘对面,他往火塘里小心地丢进一截木柴,然后用又大又亮的眼睛好奇地盯着我看。
我很快适应了棚子里的烟熏火燎。火塘里,铁三角架上放着一只黑色的铁锅,里面煮着黑茶。墙是黑色的,屋梁是斜搭着的一排粗大的树干,跟搭在上面的石棉瓦一起被烟熏得黢黑,还有扬尘垂挂在上面。屋子没有窗户,火塘产生的烟雾从墙体与屋顶树干结合的空隙飘出。棚里没有电灯,所有的光亮都来自火塘里的火光。
颁玛三十来岁,脸膛黑红,穿着长长的褐色毪衫,腰间一根花带子的下面系着半截黑色围腰。她用勺子把茶水舀到搪瓷杯里递给我们,又从火塘里取出一根燃着的枝条点着了一截颜色已经变黄的蜡烛。她把蜡烛安放在石缝间插着的一块铁片上,照见了角落里的小木案板。颁玛把一瓢白色液体注入案板的面粉堆里,开始和面。
颁玛用火钳把柴火下烧得通红的火灰拨开,把两个圆圆的面饼放了上去,再拨回火灰盖了起来。达娃挤在旦巴和素梅中间很是开心。旦巴给格西说了我的想法和他的安排,格西诧异地看了我一眼,有些不解的样子。
格西还是同意了旦巴的安排。晚饭很特别,是香软的酸奶烧馍和酥油,新鲜牦牛奶冲出的奶茶。那天我的胃口特别好,他们对我不挑食的样子给出了一脸笑意。
旦巴和素梅向我们道别说,明早他们都有早课,得连夜回去。格西把两个没了电的充电手电筒交给了旦巴。棚子外很黑,有山风吹过。旦巴说后天清早开车来接我。
回到棚子里,颁玛挪开煮茶的铁锅,把一个漆黑的浇水壶挂在一个从梁上垂下来的铁钩OQS40MU27wyVgIKBDwAGeg==上。达娃依偎在颁玛怀里静静地看着我。我从行李外包取出一盒巧克力递到达娃手上,达娃望着格西,格西笑着点了下头说,给老师说谢谢呀。达娃说声多谢丁岚老师,就接了过去。
挂在火塘上方的水壶很快冒出了热气,我取出洗漱工具到棚外刷牙,虽有满天星星,虽有银河横在头顶,四周却黑洞洞的有些吓人。山里白天和晚上温差很大,让我重回棚子前打了一个冷战。当晚,我和颁玛和衣挤在墙脚石块垒起的木板床上,格西和达娃铺了一张牛毛毡子,裹着两件大袍子睡在了火塘边。
入睡前灭了烛光,只有火塘里几段烧着的木柴忽闪着昏黄的光亮,黑墙上时有光影晃动。身体疲倦了,脑子却醒着没有入睡。我回想着这一天的漫长,就像做梦一般让我怀疑起它是否真实。经历过那些煎熬的日子又努力把生活安排得像那一回事后,现在的我才发现自己只是在虚耗时间,只是在光阴里漫无目的地晃荡。我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些时候走进这里,走进可以去用心体味的另一种生活。
听到屋外山风吹在林间吹进棚子顶缝哨音般的声音,听到狗链在石头上拖动摩擦的声响。我回想着白天的海子和满山的野杜鹃,身体的疲惫感很快袭来,脑子一沉就睡了过去。
五
我在松脂燃烧的烟火味和牦牛奶的香甜味里醒来。颁玛在一个瓷盆里给我兑好了热水,我舒舒服服地洗了脸,披了件外套走出了棚子。
清晨林边的空气清凉潮湿,不远处的林子绕着一条条白雾,看来昨夜下过一场小雨,我竟然没被惊醒到。地上的黑泥有点黏滑,我小心地踩在石块上走了出去。昨晚天黑时到的棚子,没看到棚子上方几十米远,还有一个用石块砌起用树干扎起的围栏。
格西正把两头牦牛关到围栏里。格西说,这个冬棚子建了快五年了,刚建时达娃才一岁多。他告诉我说,这个季节山上牧草好得很,他的三十几头牛都暂时寄放在夏棚子里,只有这两头奶牛每天要挤奶才关在这里。格西从棚子的瓦檐下抱了些柴火钻进了棚子。
有小股清澈的水流,从我脚边不远处向着下方草丛流去,哗哗轻响。空气干净透明,让我可以清晰地看到下方曲折环绕的公路,那是我们昨天经过的地方。
丁岚老师吃饭了,达娃站在门口牛毛毡子下向我招手。
颁玛先给我倒了一碗早上刚挤的鲜牛奶。早饭有蒸的馒头和洋芋,昨天煮茶的锅里煮着半风干的牛肉和野菜,野菜带着微苦的清香。闲聊中,格西说,旦巴和素梅是他们镇上中心校最好的老师,旦巴还是他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冬棚子缺什么都是请他开车送来。
在谈到当天的行程时,格西说,旦巴已经交代过由你自己安排,我只有两句话,不要走得太远,不要钻林子,好在这段时间沟里还没涨水,但也要注意安全。
颁玛给我备了一块烧馍、几块熟牛肉和一壶热水在双肩包里,并叮嘱我带上雨伞。格西在路坎上把他认为值得去的地方,用手指指向远处画了一个范围,约好了我回来的时间,又重复了一遍注意事项。
对面远山已有晨光铺在山头。我背了包,挎了单反相机向着格西手指的方向走去。我顺着昨晚面包车上来的小道来到了公路上。沿着寂静的公路走了一两公里的样子,我见到了公路右侧那一片格西提到过的草坪。
粉红色的小花铺满了“绿毯”,一直延伸到了右方矮树林和下方落差太大看不见的地方。此时,一抹阳光正从右方的树梢以肉眼可见的距离向草坪方向移动过来。我在朝阳斜抚过草坪花丛时,不停地按下快门。
当我再次立起身子放下相机的时候,太阳已经暖暖地罩住了草坪和身后的半个山腰。我此刻才嗅到了草坪上绿草鲜花清淡而幽远的香味。
我小心翼翼地沿着草坪边缘慢慢移动,心里充满了感激:一切刚刚好。如果经历也yUMsQeyrxaHyk0oyLvo9Xw==可以回放,也是刚刚好呢?我竟然生出了如此不切实际的奢望。
六
这台单反相机是何莉莉换机后送给我的,因为公司有个重要设计,她没能与我同行。
莉莉小我十二岁。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刚和老公离婚,她从广告公司离职,已经在家做了三年的全职太太。
何莉莉的老公大她五岁,年纪轻轻就继承了家族的服装厂。我问她当初为什么离职,她说她也不想,只是老公和他父母都说家里又不缺钱,把家管理好比上班更有价值。当时我就想,换作是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工作,把自己的生存依托在别人手上。
围着草坪的是一些灌木和无数的沙棘树。我在旦巴的博客里见过冬天的沙棘图片,一团团金黄的沙棘就像是黄玉珠团,而沙棘树像是伸向天空捧着日月的手掌,又像是挣扎着努力生长的年岁。
生命的本义是不是就是这种努力生长的样子呢?莉莉的单纯和善良让她暂时失去了挣扎和生长的时机。她教会了我茶道和摄影,我把读过的最好的文字推荐给她,我们都享受着片刻的岁月静好。就像此时灌木林间清脆的鸟鸣,那是又一个新日子里无忧无虑的歌唱。
前年,莉莉找到我哭了整整一夜,说她老公在外面养了小三还有了孩子。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最后还是同意离了婚。离婚后,她只剩下一套住房和为数不多的存款。她放弃了分手费,她要证明一些东西给自己和那个人看。她说,离婚后的她深感无所适从:当职业主妇的那几年,她差不多和整个职场失去了联系,她和时代脱节脱钩了。
水流的声音,欢快而激越,我在灌木林里间向前寻去。阳光透过沙棘林的间隙斑驳地落在我的身上,有野鸟在不远处快速地窜来窜去。
如果我和何莉莉能早些面对眼前的情景,也许心中的阴霾会早一些散去吧。
莉莉要强的个性使她并没有消沉多久。她在美术学院同学的帮助下,重新参加入职培训,很快就在眼下这家装饰公司做起了设计师。好在那些年她虽然离开了职场但却没有放弃过学习,较高的素质修养成就了她在如今业务上的提升。我在她和自己身上看到了人生无常和祸福相倚。
水流声越来越大,脚下松软的草皮也有些微微震颤,我感觉到湿漉漉的水汽迎面袭来。
这是一道平均两三米宽的溪沟,从沟壑的冲刷痕迹来看,涨水的时候有四五米的宽度。是溪,也是河,也许只有大山里才能形成这样的落差:水量大,流速快,溪沟里分布着大小不一的圆石。
溪水在石缝或石块上冲刷而下,下方被冲出一个平缓沟池,溢出的溪水又会落到下一个坡坎。溪沟两旁的灌木蓬起绿色枝条,向着溪流中间伸展过来,开满了白色的小花。
溪沟轰响的水流声掩盖了周围一切声响。我在溪床相对平缓的地方架起相机,调低快门把溪流拍成了绿叶碎花间的丝滑轻纱。相机可以虚化眼前的美景,却没法美化真正的现实。
世间的美和丑、好和坏从来都是对立的,却又不是绝对的。离婚后,我拒绝与陈伟再有任何牵扯,对于他私下里悄悄看望儿子,我都假装没有看见。在这个破碎的家里,最受伤害的可能就是我们无辜的儿子了吧。在近三十年的教书生涯里,我见过太多在单亲家庭里长大的学生,也见到过他们身上的不安、困惑和焦虑。好在自己孩子的成长环境相对稳定一些,心理上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这也让我少了一些担心。
太阳已经升高并炽热起来,我收起相机,脱去外套,取出面饼和牛肉,在溪岸树荫下的巨石上坐了下来。在渐渐习惯了整条溪流宏大的声响后,现在的我听见了石下清流的轻声吟唱。
人的一生漫长而短暂,一时一地的悲欢又算得了什么呢?儿子已经行进在即将独立的路上,而陈伟呢?我能想起的只是他年轻时候的样子,就像此时头顶上热烈的太阳。
不自律和不受约束的生活,堕落总比抗争容易得多。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编了一个谎言来学校找我借钱。我没有借钱给他,但看到他干瘦萎靡的样子时,还是隐约感到一阵心痛。我坚持着自己的决然,不想因为一时心软害了大家。
他后来进了戒毒所,那个跟过他的女人早两年就离开了他。这是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最后消息。
七
我背起背包走出沙棘林再次进入草坪时,看到很多撑开的各种颜色的雨伞斜放在草坪上,来游玩的人们的大半个身子都躲在伞里。草坪上铺着一张张塑料油布,上面堆满了各种零食和饮品。从模样和装束来看,差不多都是本地人。放下欲望和得失,生活的样子原来可以如此轻快。
我走过鲜花盛开的草坪,见到了颁玛和达娃。
颁玛手里拿着根树枝,达娃紧紧跟在后面,径直朝我走来。达娃再见到我时,已经没有了最初的羞涩,他跑过来喊了我一声。我见他一手拿着小火钳、一手提着小纺织袋,就问他做什么用。他说,阿妈放牛,我捡垃圾。颁玛搭腔说,除了冬季,来草坪玩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周末,县里、镇里都有人来,丢下的垃圾被风一吹到处都是。她说,小达娃四岁就跟着她收拾这些垃圾,已经两年了,来这里玩的好多人都认得他,达姓捡拾垃圾的时候,大家也会跟他一起把垃圾收拾带走。
达娃得到阿妈的夸赞又害起羞来,说声阿妈、丁岚老师再见,就跑去捡拾垃圾去了。
颁玛问我现在准备去哪里看看,我说没有目的。她说要不跟她一去采些野菜,我马上同意了。颁玛招手呼喊着达娃把牛看好,就带着我攀上了公路上方的小灌木林。
颁玛教我认识了蕨苔、石葛菜、水芹菜、鹿耳韭,教我如何采摘最嫩的部分。我一边采摘一边用相机把它们拍了下来。因为昨晚的新雨,地面还很潮湿。
我问起格西兄弟去了哪里,她说巡山去了。说起格西,颁玛话语就多了起来。她说,格西很早就是镇里搜救队的一员,自从他们在这里建起了冬棚子,镇里又给了他另一份工资,让他当巡山员,也就是检查进山人员违规用火和防止有人到林子里乱砍滥伐,所以除非遇上特别重大的搜救,镇里才会通知他参加。她说,格西每天都要骑着摩托车四处巡查,特别是那些危险的地段,时不时会有迷路的游客经过。
没多久,野菜就装满了三只塑料口袋。颁玛说,明天早上让旦巴带些回去。
我们走下公路的时候,达娃已经在路旁收拾好了一捆干树枝和一袋塑料垃圾。达娃背起那捆树枝,颁玛和我提着野菜,赶着牛走在了回家的路上。
颁玛取出发好的酵面开始和面,我主动去洗菜。棚子外用水是一段小木槽接引过来的小股山沟水,清澈无比却异常刺骨。在这个季节,只有雪山顶上融化的冰雪之水才会如此冰冷。我听到了马达的轰鸣声,格西骑着一辆暗红色的摩托车左拐右拐地绕开大一些的石块冲了上来。他把摩托车停在棚子后面,过来和我打了招呼,说是找了我们一圈,没想到我们回了家。
新鲜的石葛菜肉汤已经煮好,水芹菜腊肉包子已经蒸在铁锅里,夕阳的金色光芒照在了棚子上。我架好相机,邀请格西一家和我在棚子前自拍了一张合影,我搂着达娃蹲在格西和颁玛的跟前。
没有电灯,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信号和网络。我们在火塘前聊着记忆里的从前和未来的规划。格西说,达娃明年这个时候就要到镇上中心校上小学了,达娃一岁多的时候就拜寄给了旦巴,到时候就和旦巴干爸住在一起。我说难怪达娃在见到旦巴和素梅的时候那么开心。我问达娃想读书吗?他使劲地点头嗯嗯应答。
旦巴说过明天一早要来接我,于是我们休息得比昨晚早了一些。
棚子外面的风比昨夜还大,我侧身睡着望着火塘里的火光,把这一天的经历过了一遍。我是真的喜欢这种山里的生活,虽然自己并没有经历过山里的劳作和清苦。这是一种选择的结果吧,我喜欢这里的风、水、山、林,一草一木以及一切生灵。我更喜欢旦巴和素梅,格西和颁玛他们之间平淡朴素、相知相爱的夫妻情感,没有虚假做作的浪漫仪式,一切都朴实无华、坚实如铁。特别是在镇上见到旦巴和素梅时,发现他们随意一个微笑和举动都是那么心领神会,素梅自然柔和的气度更是让我心生敬意。我在和他们第一次接触时,就有了那种久违的清爽和放松的心境。
棚子外面的风声越来越大,有风钻进棚子,火塘的火光轻轻晃动了几下。很快,密集的雨点打在棚子的石棉瓦上啪啪乱响,外面雨声哗啦起来,一时没有停歇的样子。格西起身披上雨衣提着充电电筒出去了一会儿,后又带着一身寒气回到棚子里的火塘边。我听着山林间的风雨声,不知什么时候已然入梦。
八
天色蒙蒙亮,旦巴的面包车就停到了棚子外。他给达娃带来了图书和水彩笔,给格西带回了充好电的电筒和一桶摩托车用的汽油。
早餐,我喝到了颁玛从茶筒里倒出来的浓浓的酥油茶。旦巴说他和素梅上午有课,不好意思让我这么早赶路。我忙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同时对他们的关照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不知道昨夜大雨什么时候停的,山里的雨后晨曦比任何地方都清新安宁。棚子外光线还很暗淡,我们就在火塘边拍了几张合影。道别的时候,我说我一定会再回来看他们。格西一家三口把我们送到了公路入口,车子开出一段,我回头时还看到他们站在路口向我们挥手。
在路上,我向旦巴问起了达娃明年上学的事情。旦巴说这件事他和格西早在四年前就约定好了。他说,达娃不是格西的亲生儿子,是格西和他们两家共同的孩子。我完全没有听懂他说的什么。在我的追问下,旦巴给我讲起了四年前的一段往事。
旦巴、格西和更登是同一寨子里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好兄弟。后来更登也就是达娃的亲生阿爸选上了寨子里的民兵连连长,他和格西都成了镇里的搜救队成员,更登还是队长。那一年,达娃的阿妈在镇医院生达娃的时候难产去世,从此更登在有搜救任务的时候,就把达娃交给素梅或者颁玛带着。
四年前,在外地游客间兴起了徒步穿越,到这里的游客就多了起来。虽然镇政府早就下发过禁止非法进入山林的通知,但那些并不了解高海拔原始山林凶险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依然不断涌到这里。
那年夏季,有两对男女绕过检查站,偷偷钻进了冬棚子对面的山林。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的冬棚子。直到两天以后,那四名游客的亲属才向县政府发出了徒步人员失踪并请求救援的请求。
县里派出了搜救队,因为不熟悉地形,加之搜救范围没有通信信号,只能要求镇上的搜救队分组带队,县队抽人配合。那天一早,更登把七八个队员分成两队,约好了碰头的地点和大致时间,就带着干粮进了林子。
更登和格西每次出任务都在一个队里,他们搜寻了整整一天,也没有发现失踪人员的踪影。眼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到两队会合地点还要穿过山间谷沟和一段不大的林子。
经过那条谷底大水沟的双木桥时,大家已经打开了手电筒依次从上面经过。就在更登走过桥中央的时候,上方沟壁一块一人多高的巨石突然脱离,把更登和搭起木桥的两根木头一起推到了沟底。那个时候正是谷沟涨大水的时节。
旦巴说,那天更登完全可以躲开那块巨石跳到沟的对岸,他是看到危险转身把格西推开时遇难的。
后来,格西在这里建起了冬棚子,说是要在这里陪着他的更登兄弟。他和颁玛商量过,等达娃上了小学,他们再要自己的孩子。旦巴说,他们三个里面自己的条件最好,达娃上小学理应归他和素梅管了。这是四年前他们就已经商定好的。
旦巴和我都陷入了暂时的沉默。我没有问他是否找到更登的遗体,也没问他那几名游客是否得救。我望着车窗外前天经过的寨子和草坪,仿佛已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天色明亮起来的时候,我们又到了海子。我请旦巴在公路边上停下车子,想再见一眼它的姿容。从公路向下看去,海子又换成了另一种静谧的样子,仿佛装得下天,装得下群山,也装得下我的心事。
面包车转过山头时又一次停了下来。旦巴和我都走出了车外,那里可以望见远山,看到小镇的全貌。
此时,朝霞燃起了天边的一片云彩,云彩的形状就像一只正在涅槃重生的巨大火凤。“火凤”映红了我们的身影,我们的生命仿佛也燃烧了起来。旦巴也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他出神地望着天空火红的云彩,喃喃地念着什么。我想那应该是一段祝福和祷告的经文吧。
在小镇道别的时候,素梅送了我一串已经开片的星月佛珠。旦巴给我寻了车辆,送我去了下游的土司官寨,在那里,他的同学接待了我。再后来,我又去了J县县城,绕道州府,回到了省城。
回到省城的当天,我给旦巴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里有我这次出行拍的照片,特别是我们在火塘边和棚子外的合影。我想好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七年后我想让达娃到省城来上初中,就在我任教的学校。
这一夜,我一入睡就梦见了去过的那条溪沟:如月的溪水,如歌的清风,如诗的绿叶白花。在梦里,我仿佛听见了山溪轻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