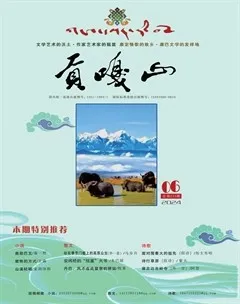南迦巴瓦

一
“那曲的牦牛是脚踩高跟鞋,身穿连衣裙,吃的是冬虫夏草,喝的是冰泉水。”小王一边开车,一边跟客人叨叨。腰间一把银色的藏刀随着车起伏,窗外是同样起伏而蜿蜒的雅鲁藏布江。
“拉的屎是六味地黄丸,拉的尿是太太口服液。”渔顺口接嘴,眼睛却瞧着那把藏刀,心想,这刀可比他嘴里的叨叨有意思多了。
“你咋知道?”小王没料到台词被抢,还是被这个一路上几乎都沉默的女孩儿,十分惊讶。
渔咋能不知道呢?去年也是从拉萨到林芝,也是走在这条线上时,司机也是这么掰扯的。只是,去年,她来这儿的时候,还是冬天,而现在,桃花都满山了。桃花自然是美的,不美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往这儿奔。但望着窗外粉嫩的桃花,渔忽然有些怀念去年的枯枝了。无花无叶,江畔山下,一片苍茫。在这苍茫之中,传来李飞单口相声一般的言语,倒真是别有一番意趣。相比,小王背台词似的语气,在这浪漫春色中,反倒显得寡淡了。
李飞是去年载渔来此的司机,但他是不让大家称他司机的。
“你们来西藏玩儿,嘴巴可得注意。招呼我们,千万别叫司机,得罪人的事儿。”
“为啥?”
“在这儿,大家管那拉猪拉牛的才叫司机。你要叫我司机,自个儿想想吧。”
于是,一路上,大伙儿左一个“小李”,右一个“李哥”。
“我去其他地方都自驾,西藏不行,得找个开车稳的。小李不错,回去推荐给姐们儿。”一个北京阿姨说。
“小李技术蛮好的,这4000多米的盘山路,我都没晕。”上海阿姨频频点头。
“那有啥……有机会带你们上珠峰108拐试试。”
“李哥有些驾龄了吧?”刚满二十岁的背包小伙问。
“猜猜,我多少岁就打转这方向盘了?”
“二十?”
“二十倒过来。”
“十——二?”背包小伙瞪圆了眼睛,赶紧给李飞递了一根烟,
“李哥,牛逼!”
李飞把烟挂在耳后,载客时他通常都不抽。但他其实却是个嗜烟如命的人——常在江湖跑,哪能不抽烟呢?
“我有次从拉萨开回兰州,三十个小时不带歇的。”李飞感觉到四周或惊愕或崇拜的目光,更有几分得意,“咖啡都不管用,靠啥呀,三包烟。”
“李哥,牛逼!”小伙竖起了大拇指。
李飞好烟,更好酒。他宣称自己在珠峰喝半斤白的,照样活蹦乱跳。这话把小伙惊得,只恨自己词汇太贫乏。
窗外弯一个接一个,窗里马屁一波接一波,司机的兴致也一浪高过一浪。
渔是车上唯一一个没有吹彩虹屁的人,但她觉得这个司机挺特别,她对一切特别的东西都感兴趣。
她大学时喜欢过一个男孩——辰,那是她的初恋,可惜他们并没有能走下去。辰说,他们不合适,因为她“太平了”。渔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脸红了。辰说,他不是那个意思。很多年后,在他们已经沦为朋友圈熟人后,渔相信他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因为他后来的女朋友比她还平。但渔又觉得,她宁愿他是那个意思。如此,在想起他的时候,只会啐一口“肤浅”,而不至于像后来那样,见到他那些“险以远而至者少”的九宫格时,心里总有种纠缠。当然,他永远不会知道她的纠缠,他只知道,她再没有给他点过赞,却不知道,她默默存下了好多他拍的照片。渔知道,他说的“平”是指生活,那被规范了的一马平川的生活。打个比方,渔的生活就像一湖静水,晶莹但毫无波澜,而辰的生活则是万顷山峦,绵延起伏。山,正是他热爱的——徒步、登山、攀岩,那些千姿百态的山峰和山谷为他塑形,让他的生活“不平”,生命“不平”。是这不平让他特别,是这特别牵着渔的心。
她想,她或许永远也成不了他那样特别的人,但这并不妨碍她对特别的想象与憧憬。所以她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变得很敏感,不放过一丁点儿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上的刺激。所以她搜集独特的风景,也捕捉独特的故事。所以她总会在李飞说“那有啥”之后,轻轻说,阿飞哥,再讲个更厉害的故事呗。
她也是唯一称呼他“阿飞哥”的人。
在去林芝的路上,车里有人忽然想“唱歌”,李飞找地方停了车。大家下车活动筋骨。他把耳根后的烟取下,打燃了火,走到河边,对着河抽起来。李飞长长吐一口气,于是那烟便缠着卷着飘起来,渐飘渐远,沿着河水的方向。
“这是雅鲁藏布江?”渔也走到河畔,走到李飞身边。
“尼洋河。”李飞并没看渔,头微微侧仰,又吐了口烟道,“雅江后天走大峡谷能看到。”
渔瞧着李飞的脸——被阳光抑或烟雾勾勒得线条分明的侧脸,在他不说话的时候,有几分忧郁,也因这几分忧郁,使得他看起来像一个人。
“你看过《阿飞正传》么?”渔问李飞。
“墨镜王拍的?”
“对!”
“没看。”
渔有些失望,她本来想说,你抽烟的样子,很像电影里的阿飞。
“但我跟墨镜王拍过电影。”
“啥?跟王——家——卫拍过电影?”渔惊得瞪圆了眼睛,声音直接提高了一个八度。
“那有啥……”李飞吐了口烟,回头看着渔说,“王家卫、吴宇森,香港那几个叫得出名字的,剧组我都待过。”
“你演了啥呀?”
“演啥啊,做制片,管剧组吃喝拉撒,就跟管你们似的。”
渔觉得李飞说话很逗,只是他一逗起来,就不像电影里的阿飞了。
“那谁比较难管?”
“还行吧。墨镜王人挺好的,我走的时候还给我一万港币,让我坐飞机回来。我拿着钱,立马买了当天九龙的火车票。他还给我打电话问到家没,我说到了,其实那会儿正在广州糖水铺子呢。”
“唱歌”的人都回来了,招呼李飞开车。“走吧。”李飞掐断了烟头,向车走去。
这时,天空中一只鹰飞过,以比尼洋河水流还快的速度飞向雪山。“阿飞哥,”渔叫住李飞,仰头指着那只鹰说,“你不应该开车的,你应该在天上飞。”
“为啥?”
“因为你名字就是‘飞’啊!”
“那你也甭坐车了,顺着尼洋河游吧。”
渔愣了一愣,而后笑了。“阿飞哥,顺着尼洋河,能游到雅鲁藏布江吗?”
“这么想去雅鲁藏江?”
“想!”渔顿了顿,“但不是为了看雅鲁藏布江。”
“那为啥呀?”
“为这个。”渔打开手机微信,点开了辰的头像。图片上是一排山峰,最高的那一座直刺长空。在最高的那一座顶上,有一个很小但很亮的圆盘。
“南迦巴瓦?”李飞眉头微蹙。
“对,南迦巴瓦!”渔肯定地点点头,见李飞神色有些疑惑,又有些得意地反问道,“怎么样,特别吧?”
“那有啥……只不过南迦巴瓦可不是想看就能看的!有句话叫‘十人九不遇’,说的就是它。”
“所以我才冬天来!”在含氧量最低的冬天来西藏,为的就是在这个晴天最多的季节来看南迦巴瓦。是的,此行西藏,渔唯一的愿望就是见一眼南迦巴瓦。
二
“你以前来过西藏?”小王问渔。
“去年冬天才走过这条线。”
“那今年怎么又来了?”不待渔回答,小王又自说自话,“不过冬天没啥看的,春天来是对的。”
渔笑笑,她知道,小王说的“对”,当然是指桃花。但这并不是她再来的原因。
“去年走到一半,接到通知,疫情原因,景点全关闭了。”渔解释道,这算得上一个原因,至少是一个能让人理解的原因。
提到疫情,车上又纷纷议论起来。
四川的阿姨感叹:“在家憋惨了,终于可以出来透下气了!”
“是啊,大家都想一块儿了,看来林芝要遭挤爆!”
“小王有得忙了吧?”
“别提了阿姨,我都三十五天没歇过了!带完你们,还有一波。估计得等花谢了才能喘口气!”
多好呀,渔想,林芝的春天来了,旅游的春天也复苏了。
“你在西藏跑车多久了?”看小王那张略显稚嫩的脸,与李飞的沧桑迥异,渔觉得他是个新手。
“今年第五年了!”小王有些自豪。
“西藏还待得住?”
“就去年疫情,到处都关了,差点就待不住了。幸好控制住了,还是咱们国家给力!”小王感叹道。
四年,说短也不短了,但与李飞的十年相比,却连一半都不及。可是,四年的,挺过了疫情;十年的,却没熬住。
渔今年计划到林芝时,联系过李飞。
“阿飞哥,今年春天再带我跑一趟林芝吧!”
“还想着南迦巴瓦呢?”
“去年不是没看到吗……”
忽然,屏幕静止了。半晌,手机那端才传来回复:“我跑不了了,车都没了。”
这次换渔发愣了。去年得知因疫情暂停所有旅游项目时,渔还安慰李飞,李飞却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还乐呵呵地说,大不了把车拆了做成板车,拉不了人,就拉菜去。在西藏十年,他啥没见过,疫情难不倒他。所以渔不相信疫情拖垮了他。渔本想说“莫不是真拆车拉菜去了?”但又觉得不妥当,李飞乐观是一回事,现实残酷又是另一回事,毕竟,很多公司都没挺过来,他一个个体户,又能有多大能耐。正犹豫如何回复,李飞的信息就又来了,他给了渔一个电话,说是哥们儿,靠得住,让她联系他。于是,渔找到了小王。
“小王打算在这安家了?”四川阿姨问。
“没想好。现在趁有得跑就先跑着吧,挣点钱,在哪儿安家也需要钱嘛。”
“我看来西藏做生意的人还挺多,一半的馆子都是我们四川人开的,看来还真是个挣钱的地方!”
“阿姨,说实话,挣是能挣点,但消费也高。蔬菜、水果都是外面运来,成本摆在那儿了。”
“小伙子没问题的,肯跑就不愁钱赚。”
“阿姨这话说得也是。我师父比我跑得久,如今都在林芝盘了套大房子了。自己住,也做民宿。可惜房间还没打理完,要不然都拉你们上我师父那儿住去。”
渔知道了,小王在这儿待着是有指望的——跑车换套房,有先例,就有盼头。
可是李飞呢?他在这儿十年,又为了啥?
这问题,背包小伙还真问过李飞。
“人们不都说,来西藏,就两种人,要么失业,要么失恋,李哥是哪种?”背包小伙一脸八卦地坏笑。
渔虽不喜欢这些个标签式的分类,但仍偏着脑袋,饶有兴致地等待着他的回答。
“我,失心疯吧。”
车上一阵爆笑。
“小李可真逗,瞧这样还没结婚吧?”渔瞥了一眼两眼放光的东北阿姨,她很想问一句,您是给婚介所拉生意来了吗?当然,不待她问,阿姨眼里的光就暗下去了。
“结过。”李飞干脆地回答,毫不遮掩,也无多余的解释。这俩字儿加上这态度,分明提示着一段故事,却也拒绝了所有的追问。渔有些吃惊,倒不是因为这个“过”字,纯粹因为这个“结”字。她压根儿就没觉得李飞会结婚。这么自由的一个人,咋会被婚姻捆住呢?就算他乐意,又有谁能受得了他这种状态呢?大概就是终于忍受不了他的“失心疯”才离的吧,如此想来,这个“过”字倒不足为奇了。一车的人都失了言语,气氛一度有些尴尬。忽然,车前方出现了一群挡路羊,一车人叫嚷的叫嚷,拍照的拍照,又兴奋起来。李飞按着喇叭驱赶,好容易才绕开了这群家伙。见大家兴味盎然,他又开始讲起了他那些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比如,有一年,他开车撞死了一头牦牛。
“李哥,这得赔几大干吧?”背包小伙晃着脑袋说。
“哎哟,我听人家说,牦牛浑身是宝,搞不好要上万呢!”上海阿姨撇嘴道。
“啥几千上万呀,那得赔命。”
“那你咋办?”渔迫切追问。
“跑啊!”
“跑?”
“不跑还能咋办?我靠,你们是没瞧见,十几个人提着长刀,骑着摩托就来追我了。当地有句话,刀出鞘是得见血的!那我只能往死里跑呀……”
“跑哪儿去了呢?”
“无人区。”
车上空气凝固了,良久,背包小伙才反应过来,竖起了大拇指:“勇闯无人区啊,李哥,牛逼!”
“那有啥……又不是没去过。以前还经常捞人呢。”
“捞人?”渔一脸不可思议。
然后,李飞就把那天南海北,戈壁沙漠捞人的事儿讲了一通,最后,讲到了珠峰。近些年珠峰热,徒步的、登山的、拍照片的、拍视频的,络绎不绝。自然,捞人这活儿也接二连三。按李飞的话说,活的有,死的有,见着时还活着,下山路上死的也有。这一个个的跟不怕死似的,其实哪又是真的不怕死呢?只不过是无知罢了——对自然无知,对自己也无知。
有一年,李飞遇着一姑娘,上大本营后高反致幻,把衣服全脱了,非说自己在海边度假。给她内衣,不穿,还说这没比基尼好看,要换好看的。没办法,只得把她打晕,再用睡袋裹着,运下来。李飞还说,在这5000米海拔之上,零下20摄氏度之外脱衣服的还不止这一个。他亲眼见过好几个疯狂脱衣的,严重失温了,衣服脱完,气也就没了。
渔听得目瞪口呆。她的心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不仅仅为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事,更因为李飞叙述生死时那平常的态度——对死没有丝毫的避讳,讲死就像讲生,讲生就像讲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明明只活了小半辈子,却恍若在轮回中辗转了无数世,并且每一世,都留下了记忆一般。
而渔对于死亡,是没有任何记忆的。
在她二十多年的人生里,来自父母和外公外婆的爱,就没有缺席过一天。至于爷爷奶奶,在她出生前就早早去世了,对他们的生,她没有记忆,对他们的死,她也没有记忆。她没有许多朋友,一二知己,已给了她足够丰盈的情感慰藉。她至今单身,辰是她唯一有过的恋人。马尔克斯说,父母是隔在死亡前的一道帘子,而为渔遮挡死亡的,岂止一道帘子,简直就是一座山。这座由爱堆成的山,在这二十多年都密不透风,直到两年前,才裂了一道缝。
也是两年前,在她的心裂开的前一天,她从辰的朋友圈知道了藏东南有一座山,叫南迦巴瓦,有一条江,叫雅鲁藏布江。山江之间有一座峡谷,叫雅鲁藏布大峡谷。人们说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上第一大峡谷,可在她此后的梦里,在她飞到比南迦巴瓦更高的天穹往下看的梦里,这世界第一的大峡谷也不过就是喜马拉雅的一道裂缝。
如今,她站在这道裂缝里,耳畔是雅鲁藏布江滚滚的水声和比江水声更加激情澎湃的导游解说词,她却无动于衷。她仰着头,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江流拐弯处的那片天,她知道,南迦巴瓦就在那里,但那里除了浓云,什么也没有。
这是个阴天。很不幸,又是个阴天。
三
去年就是这样。当然,去年她并没有走进这道裂缝。
去年冬天,去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前一晚,渔失眠了。躺在客栈小屋的床上,身上压了一床厚被和一床厚毯,渔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辗转反侧。万籁俱寂,只听得她怦怦的心跳,一下接一下,在夜里横冲直撞。伴随着这猛烈的心灵冲撞,她的脑海里也上演着一出碰撞——南迦巴瓦和雅鲁藏布两个名字,此起彼伏。无法抑制,无法忍受,渔索性起床。
她裹着毯子,蹑手蹑脚走到客栈大厅。只见灯亮着,火炉里的牛粪饼也烧得正旺,李飞坐在卡垫上抽烟。
渔有些吃惊:“阿飞哥,你没睡?”
“你不也没有睡吗?”李飞眼里也有些惊讶。
“我是太激动了。”
“激动个啥?”
“明天就能去大峡谷,就能看南迦巴瓦了!”渔兴奋地说。
李飞不说话,掐灭了烟头。
“阿飞哥,你瞧见过南迦巴瓦的真容吗?”渔扑闪着眼睛问。
“那有啥,来一次见一次,日照金山都见过。我在西藏跑这么多年,啥没瞧见?”
“你手机有照片没,给我瞧瞧呗。”渔说着,凑到李飞跟前。
“我给你找找。”李飞翻开手机相册,十张里面有八张都是雪山。珠穆朗玛、希夏邦马、库拉岗日……他眉飞色舞地给渔介绍,可是讲了一圈都没有南迦巴瓦。手机存储空间有限,南迦巴瓦的估计给删了,这是李飞的解释。渔有些失落,她裹着毯子走到了客栈门外。过了一会儿,她兴冲冲地跑进大厅,无比激动地说:“阿飞哥,我们明天肯定能见到南迦巴瓦!”
“你咋知道?”
“跟我来。”说着,渔拉着李飞走到了客栈外,然后她抬头指了指天空。满天繁星,像千盏酥油灯,把高原的暗夜照亮。
“我妈说,有星星,第二天就是大晴天。晴天,不就能瞧见南迦巴瓦了吗?”
一些破碎的画面闪过李飞的脑海,他想告诉渔,山里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但瞧着渔一脸天真和期许,他忽然有些不忍。要浇冷水,也让老天来浇吧。毕竟,明天怎样,明天的那一刻怎样,谁也不知道。
第二天一早,天不亮他们就出发了。零下18摄氏度,一车人都在哆嗦,上海的阿姨更是抱怨连天,都不止抱怨早上冷,连昨晚住宿没有空调暖气和热水,都絮絮叨叨了好久。渔很想替李飞怼两句,没做好身体和心理的准备,干吗冬天上西藏,去海边度假不香吗?但瞥一眼李飞,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渔也不吭声了。李飞说,太阳出来就好了。于是,一车人都开始祈祷太阳。渔也默默祈祷,但并不是为了暖和——太阳会带来南迦巴瓦,要是能看见南迦巴瓦,就这么冻着,渔觉得也值。
晨光熹微中,他们来到了巴松错。湖心岛上措宗寺的门还没开,阿姨又有些嘟囔了,但渔觉得很好—一成为当日第一批造访巴松错的人,还挺特别的。好像为了更加凸显这种特别的感觉,渔又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坐在石头上看湖。
在她与湖静对的时光里,山退却了,岛退却了,树退却了,路也退却了,只剩下一池碧水和一双凝望池水的眼睛。渔觉得好舒服啊,那是一种她不知道应该如何描绘的舒服。她想,辰来过这吗?大概没有吧,否则他的九宫格里怎么会一张巴松错的照片也没有。于是,她决定拍下这纯粹的湖水,可当相机打开时,她失望了——镜头里的巴松错和她眼中的仿佛不是一个,眼里的那么美,镜头里的却那么无奇,只是一滩绿色而已。“怎么会这样?”渔喃喃自语。
“太平了。”她脑子里猛地蹦出这三个字,心里一惊。是的,这是辰对她的形容,而此刻,再没有任何语词比之更能形容眼前的湖。于是,她不再觉得辰没来过这里了。他来过吧,只是因为太平了。他的确对她说过,“太平”对他是一种压力。她百思不得其解,她以为只有变动不居和高高在上才会造成压力,平怎么会呢?但此刻,她有一点明白了。平有一种力量,摄住一切,退却一切。太平的湖,没有办法留在他的镜头里,太平的人,没有办法留在他的生命里。
“咋了,冻傻了?”李飞拍了拍渔。
“没,看湖呢。”
“这湖里长飞鱼,蛰眼睛了呀?”
渔先是一愣,而后才意识到是自己动了情,眼圈竟不自觉地红了。
团友逛完岛,陆续回车上。渔发现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色,连上海阿姨也笑嘻嘻的。原来是渔独自观湖时,李飞跟大家宣布了一个好消息:
“今晚给大家改善住宿,上八一镇,空调、热水、电视、网络都有。”
“不是住大峡谷吗?”渔皱起了眉头。
“刚接到通知,大峡谷封了。”李飞叹了口气。
“为啥?”
“疫情呗。跟你们说,上面有政策,西藏执行力是排头的,就这两天,别说大峡谷,全藏景点都得关。”李飞解释道。
车上有一两声叹息,但仅仅一两声而已,毕竟这是政策,是不可抗力。上海阿姨此时倒特别理解,好像用大峡谷换一个条件好的宾馆,划算。只有渔,眼圈又红了——去不了大峡谷,意味着连等待南迦巴瓦的机会也没有,这趟算是白来了。
李飞瞥了一眼沉默的渔,深深吸了口气,然后对大家说:“这样,中午镇上吃个饭,下午带你们去鲁朗小镇看看。”
“李哥,鲁朗有啥看的?”背包小伙来了兴趣。
“国际旅游小镇嘛,林海、草原,去了就知道了。”
“阿飞哥,午饭后直接送我去宾馆吧,下午的行程我就不去了。”渔知道,李飞是想给大家一点补偿,但她已没有心情享用了。
“怎么,不想看南迦巴瓦了?”李飞嘴角上扬,目光中有一丝诱惑的意味。
“想啊。可你不是说去不了大峡谷了吗?”渔感受到了他目光中的意味,但她要求证。
“谁跟你说只有大峡谷能看了?色季拉山口也行。”
“色季拉山口?”
“去鲁朗会经过。还去不?”
“去!去!”渔像暗夜里忽然发现一颗明星一样激动,“能看就行!”
“看不看得见可不是我说了算。”李飞撇撇嘴。
“你不是说你去一次见一次吗?借你吉言咯!”渔已是乐不可支。
李飞不再答言。
色季拉山口,海拔4720米,厚厚的雪,覆盖了大地。大家下车后拍雪景、扔雪球、打雪仗,只有渔没去凑热闹,只跟着李飞径直朝靠北的平台走去。那里,是眺望南迦巴瓦的地方。渔兴致勃勃地朝前走,可兴致却随着脚步的前移不断下降。终于,当走到边界线时,她的激动和热情都降到了冰点,因为眺望对面,天色暗淡、阴云密布,随便什么山都见不到轮廓,更别说南迦巴瓦了。
渔手指对面的浓云道:“阿飞哥,南迦巴瓦在那儿?”
“是。”
“我还能看见南迦巴瓦吗?”
“看不见,云太厚了。”李飞似乎也有些怅惘。
渔仰头看看天:“可是明明有太阳啊!”
“太阳在你头上,又不在它头上……”
而后,是两个人的沉默。就在李飞打算招呼渔离开时,渔忽然做出了一个令他吃惊的动作。她举起双手,四指并拢、拇指张开放在嘴角,鼓足腮帮,冲着对面,一下接一下地吹气。
“你干啥呢?”李飞目瞪口呆。
“吹……吹气,把云,吹……吹散,就……就能看……看见了……”将近5000米的海拔,渔早已气喘吁吁。
且不说隔了十万八千里,就算近在眼前,这么厚的云,风都吹不散,嘴里呼两口气就散了?只有小孩子家才这么异想天开,大人听了都想笑,但李飞却笑不出来。那气,吹没吹到对面的云,不知道,但每一丝都吹到了他心里。轻轻柔柔,却搅得他记忆翻江倒海。
“别吹了。”李飞拉着渔往停车处走,再放任一下,她怕是会晕过去。
“我看不到了是吗?”渔有些凄然。
“回来还有一次呢。”
“原路返回?”
“对,还走这儿。”
于是,渔刚暗淡下去的眼神又明亮起来。
盘山而下,群山间是随着山起伏的树林。山下是小镇,牦牛散落在草地上,优哉游哉。但无论是林海,还是草地,都没能引起渔的兴致,她满脑子都是南迦巴瓦。所以,回程再盘山时,渔的心跳也随着海拔的上升而加速,这当然不是因为高反,而是因为,在云的上方,渔看到了太阳。太阳下的云也非先前的乌黑一片,而是半阴半白了。
到色季拉山口时,渔蹿下车,直奔北面的平台。虽然南迦巴瓦并没有露面,但渔看见太阳在变亮,云在变淡。她又开始吹气,她想,等云全部散开,南迦巴瓦就能出来了。
四
“但我终究没有等到南迦巴瓦。”渔告诉小王。她清楚地记得,她是被李飞拽上车的。她说,再等等云就散了,但李飞说什么也不等了。
下山时,渔仍不死心,双手趴在车窗玻璃上,眼睛也贴在床上看。忽然,一个明亮雪白的影子从她眼里划过。紧接着,车经过一个超90度的急转弯继续向下,那个影子被甩在了车后。
“阿飞哥,刚才侧面的是南迦巴瓦吗?”渔在车里冲李飞大叫一声,心跳到了嗓子眼儿。
李飞朝后视镜瞥了一眼,停顿了几秒,说:“不是。”斩钉截铁的两个字似一盆冷水从天而降,把渔的心彻底浇凉。
“我哭了。”渔是笑着跟小王说的。笑,代表那种伤心已经过去了,代表即使现在眼前仍是阴云笼罩,她也不会像去年那样落泪了。“你知道吊诡的是什么吗?在我眼泪落下的一刻,天空开始飘雪了。”渔不明白为什么南迦巴瓦头顶的太阳越来越亮,而自己头上却开始落雪,她将之解释为老天对她的共情。
“山上就是这样。”小王无比老练地说,“司机拽你走是对的。”
然后小王跟渔讲了一个故事,关于他师父的。
故事发生在十多年前。“是个冬天。我师父自驾,带着老婆上色季拉山。他老婆吧,”说到此,小王冲渔笑笑,有点无奈的样子,“跟你一样,就琢磨着看南迦巴瓦。一开始,对面也是乌云,等了两个多小时,太阳从云里钻出来了。又过了一会儿,对面山的轮廓开始出现了。但就在这时,色季拉山口开始下雪。我师父说走,他老婆不答应,非说再等等。我师父想,反正车上备了防滑链,就再等等吧。再说,我师父谁啊,跟职业车手一起玩儿越野的。按他的话说,他老婆都是他沙漠里捞出来的。”
“这自信!”渔不由得感慨。她忽地想到了背包小伙,要是他在,又要竖大拇指称“牛逼”了。进而她又想到了李飞.要是计他师父和那个十二岁就掌方向盘的李飞比试比试,谁更厉害呢?
“我师父就这么骄傲一人。所以他有啥怕的。老婆想等,就陪她等呗。”
“等到了吗?”
“没有。看着云移开了,一眨眼,又罩上去了。这边雪是越下越大,眼看着天要黑了,总不能在山上过夜吧。装上防滑链,下山。一个转弯,迎面一辆车。来车打滑,师父为避让,撞山了。”
“啊!”渔倒吸一口凉气。
“我师父还好,伤得不重。他老婆瘫了。过了半年,走了。
小王说过,发生这事儿的时候,他还不认识他,他也还不是他师父呢,但他的神情仍显得很伤感。
“你和你师父感情很深吧?”
“那是。我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刚来西藏时,我门都摸不着,都是师父接了活分我。我跑得最多的就是林芝这条线,因为他自己不想跑。印象中,除了第一次他带我跑,之后他再没跑过,接来的活儿通通给我。问他为啥,他说没意思,跟珠峰、阿里比,太没意思。有一年春天,我从林芝回来,约他喝酒。我说,春天的林芝是真美。他不吭声。我说,你没瞧见那南迦巴瓦,从桃花堆里长出来似的。看见南迦巴瓦了?他问。我以为他来兴趣了,就使劲儿吹了一番。然后,他跟我讲了这个故事。讲完,就醉了。对了,那是他唯一一次喝醉。”
五
“小王,过来帮我们看看。”几个阿姨凑在卖特产的小摊前,召唤小王。
“他说这刀是他们的特色,我想给我们家那口子买一把。你瞧瞧怎么样?”四川阿姨手握一把小刀询问。
“工布响箭,易贡藏刀,是特色。”小王没有点评刀,自己倒是拿起了一张弓,对着南迦巴瓦的方向比了个射箭的姿势。
“这天上又没太阳,你射什么?”渔走过去问小王。
“有个说法,工布族最好的弓箭手能进入太阳的世界。”小王认真地说。
渔笑了,因为她喜欢这个说法。
“终于见你笑了。放轻松嘛,我们今晚住村里,直对着南迦巴瓦,一定有机会守到的。”小王放下了弓,“来挑点特产,这刀也有女士的。”
“我想要这把。”渔压根儿不看摊子上的刀,而是直指小王腰间那把她看了一路的藏刀。那把刀很小,刀鞘加刀把不过十余厘米,刀把是深红色,刀鞘通体银光闪闪,上面还镶嵌了几颗红珊瑚和绿松石9b08f44971d49771addf7b19a8633f15。
“这可不便宜。”小王紧紧握住刀,像一松手就会被抢走似的。
“怎么卖?”
小王伸出三根手指。
“三千?”
“三万。”小王心中暗笑,看吓不退你。
但渔没被吓退,她反让小王解下腰间的刀给她瞧。她用手在刀把和刀鞘上摩挲一番,又抽出刀,仔仔细细瞧了一阵子,方递与小王。她只说了一个字:“值。”渔当然不懂藏刀,但真正好的东西,是有一种“共识”属性的,那种共识就是不需要懂也知道好,就是它既摄得住你的第一眼,也经得起你反复看。
这下小王先是一愣,然后将刀挂回腰间,悠悠地说:“谁知道呢……”渔看见小王的眼神忽然暗淡了,他望了望对面的阴云,有些茫然。
“放心,我买不起这把刀。但你能告诉我它的来历吗?”渔从小王的眼神中,觉察到了这把刀背后一定有个故事。
“是一个男孩的。”
“藏族人?”
“汉族。”小王顿了一下,似乎在思索如何去讲述这个故事,毕竟真有些没头没尾。
“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我是在鲁朗遇见他的。那时下着雨,天快黑了,他四下找不到车,问能不能搭我的。他说他要去大峡谷.能往那个方向走一截就行。我正好要到林芝,便捎上他了。路上,他告诉我,他从一个叫拜峰台的地方下来,滑了一跤,包滚山下去了,手机、钱包都没了,自己又淋了雨,所以样子很狼狈。但他又很兴奋,一个劲儿感叹幸好相机还在。”
“搞摄影的?”
“大概吧。他兴致勃勃给我展示了照片。说实话,我跑这么些年林芝,要说南迦巴瓦,也见过不少次,但从没见过他照片里这么特别的。”
“南迦巴瓦?”
“对。”说罢小王又叹口气,好像觉得魔怔了——怎么又是南迦巴瓦。
“怎么个特别?”
“日月同辉。而且,那月亮就刚巧在南迦巴瓦主峰峰尖上,感觉像要把月亮刺破一样。”
渔心里一惊,她打开手机,点开辰的头像,放大,再放大,霞光辉映的南迦巴瓦主峰上,的确是一轮圆圆的月亮。退出头像,进入他的朋友圈,最后一条正是这张头像的图片,时间显示两年前,地点定位是“鲁朗·拜峰台”。她的心在颤抖,但她仍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听小王讲下去。
“到了八一镇,我说要不就在这住一晚。他说不行,他必须去派镇,朋友在那儿等他,明天一早他们要进大峡谷,还说要徒步去墨脱。我说那我们得在这儿分手了,他开始翻身上的口袋,但除了一些拍摄零件和一部老式手机,啥都没有。瞧他那窘样,我说,算了.不用给钱了。他要了我电话,存在了他那部老式手机里,说等他回家再联系感谢我。又用那个手机给我回了电话,让我也存下他的号码,然后就走了。”
“走了?”渔一脸不解,“那这刀哪儿来的?”
“你听我讲。他走了,可是过一会儿又找回来了。他说他找不到车,请求我再帮忙找辆车去派镇。我说你小子太倔了,心想,这咋还赖上我了。就在这时,他从身上摸出了这把藏刀。他唰地抽出刀子,瞬间银光四射,比手电还亮。”
“行刺?”渔瞪大了眼睛。
“我也以为,所以呆住了。他放声大笑,收了刀,递到我手中。就再帮我一下吧,他恳切地说。我松了口气,可我要这刀也没用啊,于是还给他。他说,你别小瞧了这把藏刀,这是拉孜的一个老铁匠打造的,这可比我全身家当还值钱。见我不作声,他又说,我还舍不得给你呢,就当抵押在这儿的谢礼,回头我再管你赎,赎金你说了算。”
“你答应了?”
“算这小子走运,我刚好有个兄弟晚上要去那儿,就帮他联系了。”
“他就走了?”
“对。然后,”小王摊摊手,“就没然后了。一开始我想着他在山里徒步,也不方便联系。等了一周不见他消息,我就用他留给我的手机号拨回去,关机了。”
“你们之后有再联系吗?”
“咋联系?我连他叫啥都不知道,只有这个手机号,只能反复打,打得我都背得了,13666666999。”小王顺嘴就念了十一位电话号码,语气中颇有些愤愤然。
“1-3-6-6-6-6-6-6-9-9-9。”渔一字一字重复了一遍。
“呵,你记性真好,不过这号倒也真是不错。”小王口气有些戏谑。
“是啊,这还是我选的。”渔喃喃自语。
自那年冬天,辰独自雨崩徒步朝圣失联两天后,渔拉着他买了一个待机时间超长的老人机,然后花了50元选了这个号。辰说没必要,渔说我乐意。6是顺利,9是长久,渔希望辰的每一次行走能都顺顺利利,而自己和辰的感情能够长长久久。
可是,9并没有能够发挥它的作用。而6呢,两年前,当渔的心被划开一道裂缝时,她就知道,大概也没用了。
她是在电视下方滚动栏看到的那条消息:一男子徒步雅鲁藏布大峡谷失踪。当时,她心里就颤了一下,但她想,不会这么巧的。然后她开始等待,等辰的下一条朋友圈,等电视的下一条消息。但这一次,她什么也没等到。在这两年里,她也曾数次拿起手机,但始终没有拨出号码。分手后,他们没有任何联系,如果电话接通,她该说什么?说她仍然关心他,然后让他嘲笑吗?而如果没接通,天啦,那就是比接通更可怕的事,她没有勇气去直面另一端永远的缺席。
“如果有一天,他来找你赎刀了,跟我说一声好吗?”渔恳求小王。
“为啥?”
“买刀。”渔眨了眨眼。
“那他要是一直不来呢?”
“你一定要留着这把刀。”渔眼神坚毅。
这一次,渔终于住进了索松村。客栈就对着南迦巴瓦,渔有了更多等待的时间。
太阳落山,云包裹着南迦巴瓦。月亮升起,云散了一些。渔把相机架在三脚架上,她想拍下南迦巴瓦从云里钻出来的过程。
“这架势,你是不打算睡觉了?29214a9e3d0fa81225eaf9cf203c206a”小王说。
“如果一夜不睡能换一秒南迦巴瓦,那便值。”渔凝视着那缓缓移动的云。
见她如此痴迷,小王凑到她跟前,故作神秘地说:“告诉你一个法子,召唤南迦巴瓦的。”
渔转头看小王,睁大了眼睛,一脸期待。
“你就对着它吹气,一直吹,把云吹散,山就出来了。”
渔愣住了。小王以为她不信,遂补充道:“你别不信,这是我师父告诉我的。”
“你师父?”
“对。师母走了以后,师父又带我跑过一次林芝,也没见着南迦巴瓦。此后,他就再没跑过了。去年,疫情来了,生意不好做,有个林芝包车的活儿,他就给接了。”
“看见南迦巴瓦了?”
“本来是没的,”小王摆摆手,“可师父说,车上有一姑娘,冲着南迦巴瓦吹气,还真把那云给吹散了,所以返程从色季拉山口下来时,南迦巴瓦忽地就从后视镜里冒出来了。”
“真的是南迦巴瓦?”渔急迫地问。
“那还有假。打那以后,我师父就不跑车了,在山脚下盘了套房子做民宿,这样,就能天天看南迦巴瓦了。”
“你师父,”渔顿了顿,似乎在琢磨一个恰切的词,“特别,挺特别的。”
“那是。不过那姑娘,也挺特别的。”说着,小王比了个吹气的动作。
渔笑了。
对着南迦巴瓦,渔又开始吹气。云还舍不得离开,但月光却在逐渐深邃的夜色里,变得清亮如银。在阒寂的夜里,道道月光,如支支利箭,刺破云层。渔好像看见了辰,与南迦巴瓦的主峰一点点浮现。她知道,他将和她一起,看着南迦巴瓦的长矛在月落日升中刺破苍穹。而当太阳的光辉洒遍雅鲁藏布大峡谷时,她将和南迦巴瓦一起,看着他升入阳光中。她还知道,在不远的地方,李飞也和她一样,这样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