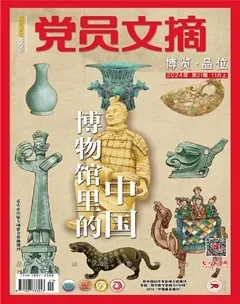绍兴:在历史的延长线上
 n
n
浙江绍兴为何人文荟萃,群星璀璨?
n对此,蔡元培先生在为第一版《鲁迅全集》写序言时,就曾给出了一种解释,他引用王献之的一句“行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描绘故乡绍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随后接着说,有了这种环境,于是便有了王逸少(王羲之)的书,陆放翁(陆游)的诗,直至有了为新文学开山的鲁迅先生……
n行走在绍兴老城
n如果从地理与历史两个角度去看绍兴,就会发现它与众不同之处。地图上的绍兴有着鲜明的辨识度,北部平原临杭州湾,东西南三面群山连绵。整个市域水系四通八达,密如蛛网,一些地方河流、湖泊密集程度甚至超过了道路。说到历史,如果从大禹算起,直至近代,用人文与经济两把尺子来丈量,全国范围内,绍兴也是数得着的“优等生”。
n绍兴是江南水乡的代名词,在某种程度上,贯穿于山地、平原中的水网可以看成是绍兴文化的底色,错综复杂的水网犹如一条条交织的文化线索,每一条单独拿出来都可以在历史中独立成章——王羲之之于中国书法,王阳明之于中国哲学,徐渭之于中国绘画,蔡元培之于中国教育,鲁迅之于中国文学……而这些线索在历史的拉力中凝聚起来,最终造就了绍兴的文化面貌。
n城市化步伐太快,古典的绍兴需要放慢脚步去感受,行于仓桥直街的石板路上,小巷商铺鳞次栉比,黄酒铺泛着丝丝酒香,桥头几个孩子在嬉闹,循声望去,仿佛瞥见了古城一抹远去的身影。如果将视角拉回到清光绪年至民国初年,从老城西北角迎恩门沿水路进入绍兴老城,将会看到水乡的日常——229座小桥将河道与街巷连成一体,乌篷船在密集的河道里穿梭,社戏的日子乌篷船在桥下挤作一团,桥上的人探着头看热闹。途经王羲之、王阳明、徐渭旧宅,路一转,在桥头或许就会与青年蔡元培和从三味书屋放学归来的少年鲁迅不期而遇,甚至在狭窄街巷里转个身又与阿Q、孔乙己撞个满怀。说实话,绍兴名人故居密度之高可以冠绝全国,要是在其他地方,每个故居都能“理直气壮”地成为当地名片。在蔡元培故居门前问当地人,绍兴有多少名人故居?“太多了。”答者用手指着鲁迅故里方向说,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对于绍兴人来说,名人太多,故居转弯便是,见多见久了,便如邻居一般,自然而然成了老城烟火气的一部分。这一低调,反而大气十足。
n越地的文化性格
n在地图上,如把视角放到绍兴老城之外,众多历史遗迹将从水网和山岭皱褶中显露出来。兰亭、王阳明墓、大禹陵、鉴湖柯岩、王羲之墓……名人故居与历史遗迹呼应,几千年的文化累积层清晰可见。
n因为水,大禹来到越地,娶妻生子,留下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佳话。治水成功,大禹在此聚会诸侯,论功行赏,祭天封禅,绍兴古称“会稽”因此得名。这次大会被看作是大禹建立夏朝的象征之一。晚年大禹再次来到会稽大会诸侯,病逝并安葬于此。关于夏朝是怎样的存在?考古学上仍有许多地方需要破解。但据考证,大禹在越地后人一直传承至今属实,如今大禹陵旁的禹陵村是全国姒姓最集中之地。
n因为水,绍兴先民“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越王勾践为富国强兵、灭吴争霸,接受大夫范蠡“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之业”的建议,走出南部山区,修建山阴故水道。运河建成后,越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大为提振。最终,北上征伐灭掉吴国,勾践成为春秋最后一位霸主,这是绍兴最早的高光时刻。
n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灭吴后勾践放弃了都城绍兴,为求霸中原,不远千里迁都到临近齐国的琅琊(今山东青岛附近)。因过于激进,勾践此举一直为后世诟病,进入战国,都城又被迫迁回江南。
n衣冠南渡重塑了越地气质。如今提到绍兴人,总会浮现满腹经纶的文人雅士形象,倒常常忘了尚武才是越人最早的基因。在历史需要时,越人的锋芒便显露出来了。事实上,绍兴那些开宗立派的文化巨匠,多是文武兼备之士。将心学运用于军事,战功显赫的王阳明退隐之年仍被召赴广西平叛,后逝于得胜归乡途中;泼墨画宗师徐渭在胡宗宪帐中为抗倭效力,屡建奇功;鲜有人知道北大校长蔡元培曾是武力推翻清朝的践行者,一度热衷于研究炸药和行刺;鲁迅手中的笔,骨气之硬,力道之劲,锋芒之锐,“一个都不宽恕”的战斗精神能抵万千雄师……犹如柯岩风景区那座鬼斧神工般的石柱“云骨”,几十米高耸的石柱,像从天而降的重剑深深扎进地里。上大下小,远看似一股腾空而起的缭绕青烟,几分诗意几分诙谐;近看,则会被它刀削斧劈的粗糙外表感染,头重脚轻,却抗住了时间的捶打,抵住了风雨的侵蚀,就是屹立不倒,一身坚韧不拔,桀骜不驯的倔强骨气。“云骨”的名字好听,生动又意味深长,好似是对绍兴文化性格的一种隐喻。
n衣冠南渡与文化再造
n绍兴既支撑过越王北伐的雄心,也接纳过永嘉南渡、建炎南渡的仓皇。两次南渡对于当时的朝廷来说,终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两次南渡,都是中原历史上空前混乱与残酷杀戮的时代,而文化却剑走偏锋似的迎来了意外的繁荣,只能说幸有越地庇护。绍兴坐拥山水屏障,易守难攻,社会安定,山川秀丽,经济富庶,成为落难的北方士族理想中的东山再起之地。南渡使中原文明奇迹般在此完成了融合与升级,终破茧成蝶,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文化的走向。
n到兰亭时,也是一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日子,离三月三上巳节还差几天,但相信春天的轮廓与1671年前并无太大不同,崇山峻岭依旧在,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景致亦然。曲水流觞原址已不可考,这并不重要,那年暮春的雅集已在中国文化谱系里枝繁叶茂,这足矣。刻有康熙亲书的《兰亭集序》和乾隆题记的双子碑,高大的身躯立于兰亭,就像“这一伟大传承”的践行者和捍卫者。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正好50岁,天命之年的人才会对生命有如此洒脱通透的感悟。两年后,崇尚清俊洒脱、放浪形骸的王羲之放弃仕途,听从内心召唤,选择寄情山水,搬至嵊州金庭山中,6年后终老于斯。如今离王羲之墓不远的金庭镇华堂村是王羲之后裔最大聚居地。王羲之54世孙,90岁的王伯江老人是村里名人,有访客时,他便会热情地写上几幅字相赠,正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书法在村里既是文化传承,也是对祖先荣耀的一种守护。
n王阳明墓距兰亭不远。与王羲之一样,50岁那年对王阳明同样意义深远,1522年春,他的状元父亲王华去世,王阳明回到绍兴,之后这一待就是6年。这段时间,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讲学。绍兴成了当时全国思想重镇,建书院蔚然成风,最终这里成了王阳明心学圆善之地。1527年9月,王阳明再次被嘉靖征召,出征广西平叛。出发前夜,王阳明宴请学生,饭后王畿和钱德洪继续向王阳明请教,师徒几人移席到宅前天泉桥上,听了王阳明讲解,两人顿悟,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天泉证悟”。如今,天泉桥在一次考古中被发现,修葺一新后,成为融合传统与当代艺术的王阳明故居的一部分。
n秀丽的山水、优雅的人文风韵,厚重的历史文化,以及发达的现代制造业,构建起了一个立体的绍兴。如今的绍兴入夜后一副灯火辉煌的都市气派,江南水乡隐于夜色中,像是等待明早苏醒的烟火日常,也像是在日月轮转中,蛰伏着蓄势待发。一个地方的兴衰,总是有其惯性,这背后隐藏着一条历史的延长线,当人文与经济相辅相成之时,沿着这条延长线,你就能看到它的未来。
n(摘自《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