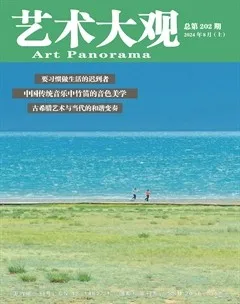从“书”到“书”
摘 要:书籍凭借其多重身份与深厚的文化内涵,自古以来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至今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当代艺术中,书籍不仅作为创作材料,也凭借其形态特点成为艺术载体。许多艺术家将书籍作为创作核心,探索其超越物质形态的文化与思想价值。书籍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更逐渐成为艺术创作中的思维方式。将书籍作为思维方式是一种新的视角,拓展了创作边界。本文从“范式”角度出发,研究书籍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分析书籍属性如何成为创作逻辑,并探讨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艺术中的独特意义。
关键词:当代艺术创作媒介;书籍艺术;范式;书籍思维;艺术家书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357(2024)22-00-03
“书”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定义、结构、属性以及其所承载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在艺术表达中,书籍的价值毋庸置疑,然而其作为创作媒介的必要性相对较弱。尽管如此,书籍与艺术的关系早已超越其物理形态,许多艺术家通过打破书籍的边界,将其作为思想载体融入其他艺术形式,使书籍转化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
在数字时代,艺术作品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观众通过简单的点击便可欣赏电子屏幕上的作品,纸质书也逐渐被电子书取代。面对这一背景,重新审视书籍作为创作媒介的价值,运用其延伸出的思维方式,有助于赋予书籍新的生命力,并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新的视角与可能性。
一、艺术创作中的“范式”与变为“范式”的书
(一)艺术创作中的“范式”
艺术家在创作中的思维方式形成了特定的艺术思维。这种思维具有“范式”——即在艺术反映和改造世界时所使用的理论与方法。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首次提出“范式”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模式。范式研究多集中于史论领域,但艺术创作思维也有其范式。艺术中的范式是艺术家看待世界、提出问题并给出艺术解决方案的方法论,对艺术创作过程起到指导作用。尽管每位艺术家在创作中追求个性化表达,通过不同的艺术体验与构思推动独创性,但作品中依然存在共性。
首先,艺术家通过不断的自我尝试,逐步形成了各自的方法论,这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内在的共性。例如,大地艺术家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劳德以“包裹”作为其核心创作范式;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作品作为同一时期的艺术风格也因相似的创作语境而存在共性。此外,创作材料作为艺术表达的载体,也促进了共性的产生,例如,学科的划分通常基于材料与媒介。
常见的艺术创作思维方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形式和材料为导向,另一类则以内容和表达为起点。以形式和材料为导向的创作,强调艺术家对媒介的探索。以大卫·霍克尼为代表的艺术家通过对材料和形式的深入研究,推动了艺术的发展。以内容和表达为导向的创作,史前艺术中就已显现。杜尚提出,理念应优先于媒介,艺术家应先确立理念,然后选择最适合表现这一理念的媒介。两种艺术思维并非彼此排斥,它们共存并相互影响的同时,每个时代的艺术流派都为它们注入新的意义。理解并研究这些不同的创作思维方式和范式,不仅有助于解析过去的艺术,更为未来的创新提供了养分。
(二)变为“范式”的书
书籍作为一种载体,其形式和定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地域和文化中展现出多样性。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书籍是“一堆带有文字或图像的相关纸张”,然而在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演变中,这一概念远不止于此。
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是讨论书籍历史时的关键线索。中国最早的书籍形式是商代的“简策”,大约公元前六世纪。这一时期,书籍主要为权力机构所用,春秋战国时期则逐渐成为传播知识文化的重要工具。
在西方,书籍长期用于记录信息、辅助管理和宗教用途。书籍在那时被赋予神秘和权威,人们对书籍和文字有着敬畏之心。然而,随着印刷术的普及,书籍不再神秘,成为日常消费品,“成为一种日常消费品,与肥皂、土豆无二”[1]。如今,随着数字化发展,书籍形式进一步拓展。
每本书籍的形式和内容由其创作目的、逻辑和叙事方式决定。如中国古代的历史书籍有编年体、国别体、纪传体等多种叙事方式,不同的体裁服务于特定的历史记录功能。现代书籍则在装帧、材质、排版等方面反映其目标群体和用途。幼儿书往往采用安全、耐用材料,配以简单插图,适合感官发育;字典排版紧凑、内容简洁,便于快速查阅;官方文件如“白皮书”则注重严谨的结构和简练的表达。
不论是书籍内容的形式,又或是书籍外观的特色,这些属性相统一,使书拥有了“范式”,成为艺术家创作的灵感来源。
二、书籍与艺术
(一)书籍艺术家
书籍是人为生产的结果。那么“书籍的创造者”又是谁?“作者写的不是书,作者写的是文本”,文本被作者、编辑、设计师、插画师等转化并最终定型;出版者决定开本、纸质和价格,书籍的生产包括大量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在这种书籍作为劳动产物的逻辑中,艺术家只负责图,与作者、其他书籍制作者的关系是合作关系。因此,插图师在这个时期这个名字比艺术家这个称号更为合适。
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书籍成为商品,生产力和技术发展,书籍的阅读者数量大幅上升。出版商邀请艺术家为书籍创作插图这一行为,助长了艺术品市场中出现拆书出售版画现象。书籍是一个能以较低的预算获得最高收益的方式,书籍商品化的传播能最大限度地让自己的作品在公众间流通,极大地提高了自己作品的浏览覆盖面。艺术家由此逐步介入,开始与作家、诗人合作,将个人的创作愿景在书籍制作的过程中扶“正”,慢慢摆脱插图师的固定工作,最终承担了整个书籍制作的任务。
部分艺术家甚至自建出版社或书店以实现自我推广。他们用行动证实了:“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接触艺术”的理念,艺术创作在书籍的语境下摆脱了空间和金钱的限制,为艺术家在书籍与商业的交叉领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比如,墨西哥概念艺术家乌利塞斯·卡里翁,他于1975年创立了“其他书籍”(Other Books and So),这是第一个专注于艺术家出版物的空间,并在1979年转变为“其他书籍”档案馆。
(二)书籍艺术作品
艺术家书是书籍艺术作品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艺术家书(artist’s book)指的是视觉艺术家以书籍形式创作的作品,我们常用这一更宽泛的术语来指代艺术家之书和书版印刷。”[2]从历史溯源,艺术家书拥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活动区间,它与出版、版画和传统书籍工艺有着重合的时间轴,但又不能被完全包含在这些概念中。
出版物是激浪派的核心。由作曲家拉蒙特·桑顿·扬编辑,乔治·麦素纳斯设计并于1963年出版的作品《选集》(An Anthology)包含了十几位激浪派艺术家的作品,内容包含约翰·凯奇的《4分33秒》的乐谱,以及其他艺术家的诗歌、图像、散文等。这本书是“艺术家书”这类艺术形式的早期表现之一,即书籍内容就是艺术。
文字不一定是最重要的部分,也不一定是语言的载体,文字可作为无意义的符号不传递任何信息,图像同理。内容、结构可以被打破,物理结构也随着艺术家的创作理念被重新解构,变成一种材料,最后连书籍的固有样貌也消失,只留下被书籍洗礼过的观念,形成了以书籍为核心的艺术创作思维。
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存在的书籍
(一)书作为文化符号与艺术创作
许多艺术家以书为题材或材料进行创作,表达对“文化”的思考。书的文化象征意义在这些作品中被自然运用。
但核心都是以书籍作为思维方式、围绕着文化的符号进行的创作。他们的创作思维大致遵循着这三个步骤:一是捕捉到书籍在文化符号语境中的角色与其创作主题所拥有的平行并置关系;二是切入书籍的视角;三是书籍语言转换。
(二)书籍“范式”与艺术创作
书籍这种“理所当然的”物体形态激发了艺术家渴望打破僵局的冲动。其各种物理属性,在结构、理论,甚至哲学范畴中也引发了艺术家的思考。
菲奥娜·班纳创作的《南》(The Nam)是一本重2.388公斤,1000页,没有章节、分页与段落的书。这本书连续描述了六部讲述越南战争的电影,但反常态的排版使读者在翻阅时无法完整提取到原电影的内容,战争的紧张感在重复叙述中逐渐变得平淡。赫尔曼·德弗里斯的作品《机智》则通过完全空白的页面制造空白感,呼应尤利西斯·卡里翁在《制作书籍的新艺术》中提出的观点:“世界上最美丽、最完美的书是只有空白页的书。”这些作品的极简或过载的形式,都是对书中内容常规性的排版所发出的挑战。
迈克尔·斯诺的作品《封面到封面》则通过摄影将书籍、书页属性具象化,相机从不同角度拍摄同一对象,将图像定位到书页最大值,使读者难以区分正面与背面。在一次采访中,斯诺谈道:“页面是双面的。总有‘另一面’的存在这件事,可以感受到照片的二维性,体验到摄影中的压缩。”这种独特的物理结构与书籍的语境紧密相关,只有书这种媒介才能传达这一艺术构想。
哈尔特·丹尼尔的作品《带我去见你的领袖》则通过将护照与艺术结合,巧妙碰撞了身份与权利的象征。
此外,书籍的制式、读者群体及其使用场景的联合构建也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与思维范式。以“菜谱、读者、厨房”为例,厨房不仅是菜谱的使用语境,更是读者进行实践的空间。三者之间的联系构成了“范式”,从而触发创作。
迪特·罗斯在他的作品《平面废物》中把自己生活中的废弃物、食物等塞进袋子里,放进档案夹保存。档案夹通常用来存放重要文件,一定数量的档案柜存放在同一空间里构成档案室,本应装有“重要文件”的夹子放的却是艺术家产生的“废物”。此作品除了利用“档案”的属性,艺术家也通过“归档”这一行为,使观念清晰表达。
最后,艺术家通过书籍范式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结合,呈现了新鲜的艺术模式。尽管书籍的某些特性在其他媒介中被消解,但其核心特质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重新定义了原有形式,赋予了新的内涵[3]。
在摄影艺术中,书籍通常是摄影物理载体的首选。除了上述提到的迈克尔·斯诺的作品,美国摄影艺术家爱德·拉斯查的摄影书强调了书籍作为独立艺术存在的观念。拉斯查通过朴实的拍摄手法记录日常事务,是他所称的“事实的收集”和“现成品的收藏”[4],因此,在书籍与摄影合作的时候,摄影本身的技术性被弱化,书籍赋予了其新的意义。
雕塑艺术中,书籍的形态常被拆解、重组或置换。雷切尔·怀特里德的作品《无题(黑皮书)》与《无题(图书馆)》通过雕塑探索书籍的“负空间”。书籍的物理特征依旧可见,但它们已不再具备可读性。
阿比盖尔·雷诺兹的《晦涩阅读》展示了书籍、影像和行为艺术的融合。通过记录九个人的“阅读过程”,探讨了书籍的“阅读性”及其与图书馆空间的关系。这种跨媒介的合作是书籍作为创作思维的典型体现。
书籍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不仅连接了不同艺术形式,还为未来跨媒介、跨材料和跨学科的艺术实践提供了新的启示。艺术家通过对书籍媒介的不断探讨与实践,扩展了创作的广度与深度,提升作品的创新性与艺术价值。
四、启发与局限
在过去的六个世纪,书籍的足迹遍布全球,它记录了世界历史并保鲜着知识的果实。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书籍是足够“资深”的媒介,不仅为文明进行编码,还不断更新自身面貌,在艺术创作中为艺术家带来新的感官与思想启迪。
给书籍下一个永恒的定义是困难的。从结绳记事到活版印刷,再到万维网与虚拟现实的出现,书籍一直在变化,但始终顺应时代的步伐。书籍的演变与思维的成长共享同一条时间线。书籍的变迁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为艺术创作者提供了反思自身思维方式的契机。然而,书籍的变化不是吐故纳新,书的历史与书的经验至今仍大有裨益,创作的思维同理。
当代艺术创作正处于信息爆炸的媒体时代,信息的输入输出速度极快,思想流动不止,社会景观日新月异,共同构成了艺术创作所面临的复杂情境,梳理创作思维是乱中理线。书籍作为艺术创作的思维方式在接下来的研究会如何变化是不可定论的,已知的是,将更需要凝神静气的思考态度去破解盘根错节。
参考文献:
[1]马丁·里昂斯.书的历史:西方视野下文化载体的演化与变迁[M].龚橙,译.北京: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2017.
[2]简·罗伯森,克雷格·麦克丹尼尔.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年以后的视觉艺术[M].匡骁,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2.
[3]顾丞峰.装置艺术在中国[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1.
[4]托尼·戈弗雷.观念艺术[M].盛静然,于婉莹,译.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20.
作者简介:曾冯璇(1999-),女,湖南湘潭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媒介、书籍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