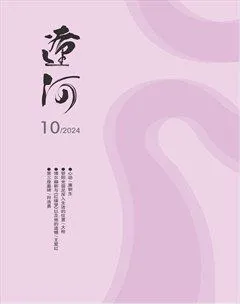博尔赫斯与《红楼梦》以及他的遗憾
《红楼梦》无疑是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博尔赫斯经常谈的中国小说。他对此书赞美有加,但也存在某些疑惑。这种感觉非常准确,即使是国内的“红学”爱好者(包括红学家)也未尝不是这样。《红楼梦》无疑是一本奇书,是影响世界文坛的名著。我记得,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希望成为一个中国人。
多年之后,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已是83岁高龄的法国著名作家让·马里·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读老舍和莫言的作品时,感觉自己像中国人。写到这里,我的心就有点儿不平静了。看了那么多外国文学名著,我怎么从来没有产生想成为别的国家的人的想法呢?
勒克莱齐奥与中国有比较深入的联系,几年前他还来过中国。但是,博尔赫斯生前却未能到访中国。有文字记载,1981年12月,博尔赫斯在家中接待了来访的中国外交官黄志良,这表明他与中国有一定的接触。博尔赫斯说:“我有一种感觉,我一直身在中国。”(《神秘的岛屿——博尔赫斯访谈录》/西川 译)。他对中国的感情属于天然的魔力。这位大文豪留下的文字中,提到中国的地方实在不少,他的名篇《小径分叉的花园》里的主人公就是一个中国人,故事当然是虚构的。有研究者认为,这篇小说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博尔赫斯在谈到《红楼梦》时联想到“迷宫”。“彭冣的花园”与“大观园”似乎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部小说好像长得没有尽头,博尔赫斯在抱怨《红楼梦》人物众多难以辨别时还说,“我们好像在一幢具有许多院落的宅子里迷了路”(《博尔赫斯全集·文稿拾零》之《曹雪芹〈红楼梦〉》 徐鹤林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小径分叉的花园》是仅仅六千余字的短篇小说,但像《红楼梦》这部一百二十万字的长篇巨著一样,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建议,那些嫌《红楼梦》太长,想读还没有准备好的读者,不妨在闲暇时先看一看《小径分叉的花园》。她几乎与《红楼梦》一样好。她……好,您听出来了吗?这是一个句式,博尔赫斯先生经常用。
中国文化对博尔赫斯有很强的磁力。中国,是博尔赫斯经常挂在嘴边的时髦辞藻,也是在他的文字中时常跳出来的字眼。他的《恶棍列传》中那篇《女海盗郑寡妇》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有资料称,这个清朝的女海盗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女海盗郑一嫂。她原姓石,乳名香姑,又称郑石氏,广东新会籍,前夫姓郑,因排行而俗名郑一,新安(今深圳宝安)人。博尔赫斯的小说奇崛、智慧、深刻,天马行空,想象独特,他惜字如金,不惜在一个传说中龙飞凤舞、笔走龙蛇、夸夸其谈,大概不仅仅是为了表现一个有别于林黛玉的东方女性身上所拥有的近乎于男子汉的勇敢、刚毅与不屈不挠的精神吧。
在这里,请允许我斗胆说一句,我几乎拜读了博尔赫斯所有的那些被翻译成中文的书。
突然,我想起博尔赫斯的另外一篇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有一位评者好像陷在这个不大的“迷宫”里了。其实,富内斯与郑一嫂比较一下也没有那么难理解。一位作家的作品必定带着作家本人的影子。如果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那么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呀?在我看来,不管是林黛玉还是郑石氏,都是作家笔下成功的人物形象。“郑寡妇喃喃说:‘狐狸寻求龙的庇护’,然后上了大船。”如果不知道郑一嫂接受朝廷招安,正是鲜花怒放的42岁的生命,最后在一场台风中坠海身亡,就别言语博尔赫斯的文笔是多么简洁而诗韵悠长了。他写的“美好的结局”,郑寡妇不会死,“五湖四海成了安全的通途”,人们“唱歌作乐”,甚或忘却了那一声情不自禁的叹息。博尔赫斯说,郑寡妇“起了另一个名字,叫‘慧光’”。听这名号,肯定不在庙里,是在哪座庵上,就不得而知了,博尔赫斯先生从来不写长篇小说。
博尔赫斯是不会猎奇的,也不爱哗众取宠。他有超强的记忆力,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如同《三国演义》里的张松张祭酒一般。博尔赫斯的视力有先天的障碍,所以,先天便赋予了他另外一种超强的能力。后来,博尔赫斯双目失明了。“就像夏天的傍晚,天慢慢黑下来,失明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您看,博尔赫斯说得多好呀!多么有诗意。他是天才,天文地理,古往今来,五湖四海……博尔赫斯在这个过程中借助于听觉,有如此广泛的涉猎就不足为奇了。我在仰望这位文学巨匠的同时,发现他所读的中国书已经很多了,《老子》《庄子》《孔子》他读过,《道德经》他读过多种译本,伯特·阿伦·翟里斯写的《中国文学史》他也读过,他对中国文学有一个大体了解。不过,他阅读的中国小说是屈指可数的,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这不难想象,有案可查的有《红楼梦》《水浒传》,另外一本就是《聊斋志异》了。博尔赫斯承认自己“不懂意大利文”(《博尔赫斯全集》/《七夜·但丁》 陈泉 译),“永远搞不懂中文……”(《神秘的岛屿——博尔赫斯访谈录》),否则,他是不会去读《红楼梦》的翻译版本的。博尔赫斯说:“译作不可能代替原文。可是译作可以成为读者接近原文的一个途径和一种推动。”(《七夜·但丁》)。1940年,博尔赫斯曾亲自将《红楼梦》节译成西班牙语,根据张汉行先生考证,参考的是王际真的英译本。根据这个译版,博尔赫斯翻译了《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和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两个片段。抑或,博尔赫斯想成为中国人的念头,大概是通过《红楼梦》这条“途径”和“推动”产生的。博尔赫斯说,西方最伟大的发现是东方。我说,博尔赫斯最伟大的发现是《红楼梦》。
在《博尔赫斯谈话录》(【美】威利斯·巴恩斯通 编;西川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博尔赫斯说:“我读的是英文和德文两种译本,但是我知道还有一种更加完备的,也许是更忠实于原文的法文译本。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红楼梦》这本书就像它的书名一样好。”英文和德文版本分别是王际真翻译的版本与库恩的译本。博尔赫斯所知道的法文译本,有人推测是李治华所译。我们知道,文学翻译能够保持原著神韵的难度很大,尤其是像《红楼梦》这样的具有诗歌品质的文学名著。这本书有几个名字,不管是《石头记》《风月宝鉴》还是《红楼梦》,就像一个人有好几个名字,一个作家使用了多个笔名一样,仅仅是代号而已,并不影响实质性的内容。尤其是《红楼梦》这本书,它不是那种一点就通的简单易懂的书。在中国文化界漫长的阅读过程中,它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研究机构——红楼梦研究学会。拥有绝佳的阅读条件与雄厚的中文基础的中国读者,似乎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不读五遍《红楼梦》基本上没有发言权。这个结论未免有点儿夸张,不管是专家还是一般的读者,你想说尽管说好了,没有人阻拦,但会有人暗自发笑。这与读几遍《红楼梦》没有什么关系,关键是你说出的话有没有可信度,更不用说学术水准与权威性了。“红学”纵向划分为旧红学、新红学、当代红学三个时期,横向划分为评论派、考证派、索隐派、创作派四大学派,各派又细化为若干分支,主要包括题咏、评点、鉴赏、百科、批评、曹学、版本学、本事学、脂学、探佚学等。
“红学”既然是一种学问,就不是一般的复杂、深奥,不能按照这个思路继续深入下去了。博尔赫斯先生煞费苦心,付出了很多心血,他所称赞的《红楼梦》,我基本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好法了。他好像对那块来自天上的石头更感兴趣。博尔赫斯说:“《红楼梦》全书充斥绝望的肉欲。主题是一个人的堕落和最后以皈依神秘来赎罪。”(《文稿拾零》——曹雪芹《红楼梦》徐鹤林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这也太过偏颇了吧。实际上,博尔赫斯的文学与《聊斋志异》和《水浒传》更接近一些。他所写的玩刀动枪的小说,哪一篇不具有“拦路打劫”(这是博尔赫斯对《水浒传》的评价)的品质。至于聊斋便无需赘言了,否则,博尔赫斯也称不上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
很多时候,一个作家的话可信度不是很高。他的习惯用语如果不是小说中人物的语气——这纯粹是作品的需要,那么,就是一时兴起,如同喝醉了酒,是不算数的。博尔赫斯还说,他想成为英国人,或者是别的国家的人,就是不想做阿根廷人,死也不在阿根廷(1986年6月14日,博尔赫斯在日内瓦辞世)。难道我们就此认定博尔赫斯没有国家的概念,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回过头来,我继续揣摩博尔赫斯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中国人?是哪个朝代的中国人?博尔赫斯是不会动刀子的。他从小就是一个腼腆的人,上学的时候没少受人欺负,他父亲为此给他买了一把刀子。于是,他把畏惧转移到这把刀子上。我记得,莫言先生评价幼时的自己,不无诙谐地说,他有三大缺点,而博尔赫斯至少有两个。两位文学大师有那么多优点是相同的,他们的缺点也必有相似之处。比如,博尔赫斯的长相确实有点丑。顺便说一句,长得俊在很多方面并不是中国男人的优点,有才能才是优点。博尔赫斯另外一个性格上的缺陷则是怯懦。他确实是这样一个自谦的人(《博尔赫斯大传》【英】埃德温·威廉森 著;邓中良、李菁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我从来没有说过,有哪一个中国人是怯懦的?虽然,怯懦属于人天性的一部分,即使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也不例外。打架,博尔赫斯不行,与女人交往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博尔赫斯最想成为的中国人应该是贾宝玉。因为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滋生这样的想法。这个英雄般的形象不仅可以弥补博尔赫斯在成人礼上所遇到的尴尬,还可以弥补他一生中,甚至是荣誉所带给他的所有遗憾。我敢说,《红楼梦》是所有中国作家的“母亲”。毫无疑问,谁得到“母亲”的偏爱越多,谁取得的成就就会越大。新时期,中国作家还遇到过一位“母亲”,她就是《百年孤独》。创作这部世界名著的大作家是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他才像中国人呢。在中国,他似乎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人,名气仅次于莫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是受了博尔赫斯的影响。博尔赫斯的非凡之处可见一斑。
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的博尔赫斯是影响世界文坛的超级作家。我看了一份资料,有十位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遗憾中,博尔赫斯排在第二位,第一位当然是现实主义的“喜马拉雅山”——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之所以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这位早已经名噪世界的大作家,根本没有必要给这个新兴的奖项抬轿子。与其相比,博尔赫斯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不是因为他对这个奖项熟视无睹。在他的散文随笔、文稿拾零,包括他的谈话录中,这位大文豪经常说尤金·奥尼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罗曼·罗兰、福克纳……他们一一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等等。
所谓作家就是最完美的人,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那些高尚的品质是一次又一次接受精神的磨砺所锻造出来的,假如说有什么缺点的话,恐怕是骄傲、自负、刚愎自用与特立独行。
博尔赫斯之所以没有登顶斯德哥尔摩山脉大约有一千零一条理由,凡是对博尔赫斯有所了解,系统地读过他作品的人,无不吃惊地发现,他从事文学创作,真是文学之幸,也反证了文学的崇高。博尔赫斯的生活条件太优裕了,堪比大观园里的贾宝玉。衣食无忧,真是神仙一般的日子呀。我突然想起了作家张爱玲在小说中令主人公说出的那句惊世骇俗的话,爱情是为了活着。作为一种句式,拿来供批判用,我把它平移到文学领域:文学是为了活着。文学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养活了一大批爱做梦的幻想家。别无他求,也无可求之处。许多所谓的作家为生计而写作,情何以堪。博尔赫斯不是为生活而写作的人,他也不需要夫人去借钱维持日常。博尔赫斯的作品缺少人间烟火,这也许是特殊的生活条件所造成的遗憾。另外,那些爱读长篇小说的读者,在博尔赫斯这里多少有点失望吧。
世人皆知,诺贝尔文学奖奖金的实质分量,以及使人一夜成名的伟大力量。当代社会越来越重视一个成功人士的知名度,那些得到实惠的人只知道偷着乐。鲁迅先生在世的时候觉着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太多,中国的作家包括他自己还不配“享用”。我见过这一段文字的描述,嘴角也是上下不停地抖动。谈到诺贝尔文学奖,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中国大作家的第一反应,根本没有想到诺贝尔文学奖潜在的无可估量的价值。
据说,马尔克斯写完了《百年孤独》就鲤鱼翻身住进了别墅。毛姆是为了赚钱而写作,只能算二流作家,这对一流作家的要求也太高了吧。难能可贵的是,博尔赫斯是不屑为了什么目的去写作的作家。一个人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法国的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任何文化实践的参与都带着阶级属性的色彩。博尔赫斯不是贾宝玉,他是博尔赫斯家族中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至于博尔赫斯的独立人格与显著创作风格需要从他的成长过程和心路历程中寻根溯源。
有一种说法,博尔赫斯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政治因素。这顶帽子仿佛有点大,令人沉思。真正的艺术一定是按照艺术本身的规律运行、发展的。心有杂念、怀抱企图的人古来有之,他们才会在文学作品中发现非文学的政治因素。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内容不管从哪个方面讲,往往对所谓的政治极其不利。优秀的文学作品一般具有多义性,就拿《红楼梦》来说,鲁迅先生就有这样的评价:“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阅读文学作品,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文本上。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会发现文学家许多个人的品质。我不得不说,诙谐幽默几乎是所有艺术大师最显著的特点,博尔赫斯也不例外。试看他的作品,看看有没有弦外之音,看看是否如此。
博尔赫斯说,讽刺可以诱发包括麻风病在内的皮肤病。在纳粹末日即将到来之际,博尔赫斯公开支持德国。1944年,他创作的《小径分叉的花园》是德国的间谍(尽管他是中国人)成功地给柏林输送了情报,炸毁了那个叫艾伯特的城市。借用他人之语,博尔赫斯在教你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他把阿道夫·希特勒称作慈善家,火葬场就是这个杀人魔王的发明。他用手指着火葬场的烟囱,说了这句天大的笑话(《沙之书》之《一个厌倦的人的乌托邦》)。博尔赫斯有种族歧视的观念,从称呼上就能看出来了,他对奴隶制抱有怀恋之情。在一篇小说中,他把活活累死的黑人奴隶,说成是“忘恩负义,竟然生病死掉”(《恶棍列传》之《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让人不可理喻的是,博尔赫斯居然跟宗教也开这种国际玩笑。他明明知道“要解释一种宗教是很难的,特别是一种你并不信仰的宗教”(《七夜》之《佛教》/陈泉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他依然毫不避讳地解释了一万言(只多不少)的佛教。在《外乡客》这首诗中,他是这样写的,“在各种教派里面,神道最不足道”(《天数》 林之木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试想,在所有的道路中,除了神道哪一条道路是畅通无阻的?看吧,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可真敢信口开河。博尔赫斯从独裁者手中领取的那个奖,未必不是一种带有报复性的具有彻底性的大幽默。
实际上,任何事情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难道不是我们在世界上可以继续存活下去的理由?博尔赫斯在一篇小说中,借用主人公的语气说:神是公正的……我们常说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
属于博尔赫斯的“公正”在中国,在全世界的读者中。有人说,博尔赫斯炒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鱿鱼。博尔赫斯说:“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成为另一个人。”他在与巴恩斯通的谈话中,还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我不该为自己的错误而抱歉”。想想,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