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算拥有一段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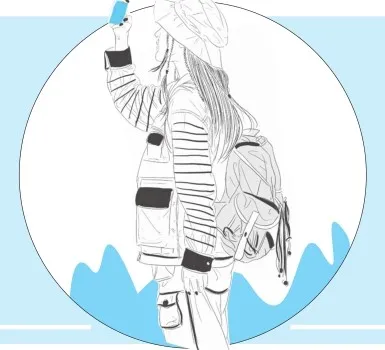
旅游是一种典型的体验式消费品,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人早有非常成熟的论述。
比如与朋友夜游赤壁的苏轼,就即兴将一般意义上的实物与一段旅程做了精彩的对比:对于实物而言,是“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换句话说,要想消费它,必须以实质性的占有为前提。
而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却是我们通过感受与体验就能拥有和消费的,“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从这个角度解读,苏轼那篇了不起的《前赤壁赋》不啻是一曲写给体验经济的颂歌。
顺着苏轼的思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究:人可以拥有一间房屋、一件电子产品、一个家庭,这里“拥有”二字的含义清晰而明确,甚至有严格的法学定义作后盾。
但是对于像“旅程”这样的体验式消费品,我们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拥有,这或许能引发一些有趣的思考。
哲学家告诉我们,拥有的最极端方式(同时也是最古老的体验式消费)就是吞吃:原始人相信,假如一个人吞下其崇拜的动物,那么他就能与之同化,获得该动物象征的力量和品格。
饱餐一顿之后,“权威、制度、理念和图像都可以被内心吸收,永远保存在五脏六腑之中”,无人能够夺走。
我时常想,在不少现代人对待旅游的态度中,其实还闪烁着类似的原始智慧,他们也一心想把风景中的珍奇、壮美、静谧吸收到体内,永远保存在脏腑之中,只不过他们“吞吃”“同化”风景的途径从食道换成了相机的镜头;对这一类游客来说,不带相机就没法旅行,因为它不只是诸多装备中的一件,更是旅行的终极目的和归宿——这些人通过相机来拥有自己的旅程。
比起“吞食式”旅游者,更进一步的,也许就要算“集邮式”旅游者了。
全球各处旅游目的地是他们的收藏品,每到一个新地方,相当于集邮家又拿到了一件珍稀的小型张或首日封。
法国人司汤达曾说:“收藏癖令人偏狭、善妒。”原本具有开阔眼界、陶冶性情功效的旅游,在不少情形下反而变成了津津于矜夸攀比的炫耀性消费,这不能不让人钦佩司汤达的先见之明。
17世纪以后,西欧的富裕家庭大多会出资让年轻人在成年前跟随导师,深度游览欧洲大陆,见识各地的文化瑰宝、风土人情。这种旅行往往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来被定名为“壮游(Grand Tour,字面意思是‘大旅行’)”。
父母认为,只有经过壮游的历练,孩子的教育才算真正完成。
从我们的话题看,壮游也算得上人们“拥有旅程”的一种方式:年方弱冠的少年第一次真正走出家门,长时间漫游异国,经受文化熏陶,领略世间风貌,这段旅程对于他们今后的人生来说无疑是极为宝贵的财富。
父母的出资转化成了子女的文化资本,旅行在这里具有重大的投资意义。
说到底,我们之拥有旅程,其实也与我们拥有其他各类实物的方式没有太大分别:对于旅程,我们可以吞食消化,可以积累收藏,甚至还可以投资获益。
只不过,我们与旅程的关系会产生更为深刻的自我影响:我们怎样拥有旅程,也就把自身塑造成怎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