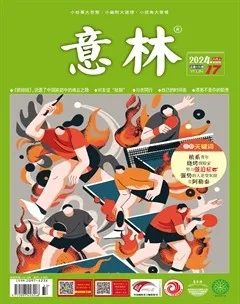记住你的名字
刚走进车棚,又听见高处纸箱里的那只野猫发出一阵低吼,充满敌意。它盘踞在此很久了,我很担心哪天它会突然从高处跳下来抓伤女儿皮皮。进屋后,我和我妈说到此事,皮皮从书房里探出头来:“妈,召开家庭会议吧!”
皮皮、我、我妈围坐拢来。“我先说。很简单,这事是外婆的囤积癖造成的,纸箱一个又一个,摞得高高的,猫当然会来做窝。想解决的话,扔了箱子就行。”皮皮抢先发言。
我却有些犹豫:“天冷了,大猫挺可怜,但我又没法让它有产权意识,明白这车棚是我们家买的。”
皮皮望着我:“要么它流落街头,要么你承受恐惧,只能二选一。”
我妈和皮皮商量:“这样吧,我们把箱子开口换个方向,背面对着车棚内部,开口对着通风口,上层空间归它,下方归我们。你觉得可以吗?”
皮皮对外婆竖起大拇指:“圆满解决,散会。”我们的家庭氛围一向如此。我妈看着皮皮的背影,眼里满是欣赏。
对孩子的角色设定,是能起到鼓励或打击作用的:你把孩子当大人,在这种角色的积极暗示下,她就会越来越成熟;你把孩子低矮化、幼稚化,总是以经验去不倦教诲,总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去强势管控,孩子的自我,就会不断地被侵蚀、瓦解,最后被彻底摧毁。一个失去自我的人,就像死掉根系的树一样……这世界上有种可怕的隐形伤害,就是“大树底下不长草”。
专为家长所用的“教育”这个词,实在是有点自恃,很多时候大人是比不上孩子的。有段时间,皮皮和老师、同学的相处陷入了困境,她很痛苦。很久以后,她才无意中提起,我心痛不已,问她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她却说:“我不想你难过。你又能怎么办?无非多个伤心的人而已,没必要,我自己能处理……”那么小的孩子,一点点消化掉伤心,控制着情绪不流露,慢慢想出办法改善处境,单枪匹马地应对着这个世界给她的“痛”。念及这些,我既心疼,又钦佩。
随着她的“自我”逐日发育成熟,我可以越来越多地把她还给她自己。我和皮皮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在平等地相爱,而不是一个主人在照顾软萌的小宠物,也不是一个智者在完成他的教学作品,更不是一个“狱警”在监管“囚犯”,大家开心地做着朋友。
人,应该是一个一个的人,一个有自己名字的人。
爱,也是这一个人去爱另外一个人。作为她的朋友,我能够做的,不过就是反复提醒:记住你的名字!
(本文入选2024年湖北省武汉市中考语文试卷,文章有删减)
黎戈,作家,南京人。著有《时间的果》《私语书》《心的事情》等作品。
《意林》:家长总是忽略了孩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要做好这一点,家长应该怎样做?作为孩子,又应当如何做?
黎戈:我并没有很强的“家长”这种身份意识。大多数时间,我都沉浸于自己的工作和阅读之中,也没有过多地去关注小孩。除了保障小孩的安全健康,我在其他方面的管理欲较弱,小孩就像天地间的植物或一杯茶,有她自己的生长节奏和火候,生命自会完成它自己,尊重这个节奏就好了。她能把自己长好,作为家长,要有这个信心。
我女儿的回答:如果家长提供足够民主的环境,小孩自然就成为独立的个体了。如果家长很专制,小孩就不可能成为独立的个体了。谈不上“怎么做”了。
《意林》:从文章中可以看到,您的家庭氛围十分融洽和谐,您和女儿之间有过冲突吗?你们之间是如何化解冲突或者您是如何引导的?
黎戈:冲突自然是有的。不过我女儿是那种内核很稳定的小孩,她不一定会顶撞我,而是默默坚持她自己的想法。其实我也在向她学习这种处理方式。生气时,我会到外面走很远,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就能静观这件事,尽量过滤掉情绪就事论事。常常,经过反省,确实是我做错了,这时我会向小孩道歉。养小孩的过程真的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内心梳理,我发现了自己很多的问题,也有了修正的机会。谢谢我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