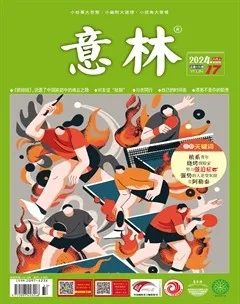走出去,才发现小镇的美好
小镇,一个矛盾多义的词,总有不同的语调。
第一次遇见小镇,它的语调是欢愉的,带有岁月静好的安稳。它温柔如细雨,抚慰着我们每一寸的成长,告诉我们家乡的风、家乡的山、家乡的雨、家乡的美食、家乡的笑语。
时光漫漫,当我们长成一个青年,感觉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小镇突然有了沉闷的语调。它预示着“一眼望到头”的日子,预示着平淡与乏味的结局,当然想逃离它。
走出小镇,我们变成了赶时间的人,搭上快速前进的列车,终日忙忙碌碌。这时的小镇,是温柔而伤感的语调,告诉你家乡的美好,也告诉你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
看过太多逃离小镇的故事:年轻人一无所有,和父母“讨价还价”,想要逃离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父亲沉默不语,母亲苦苦劝说:“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为什么不听老人言?”年轻人大吼道:“我就是要离开这个地方,我只想做自己!”
小镇不好吗?小镇太好了。生活慢慢,找到稳定的工作,朝九晚五,一日三餐,将来会贷款买一所漂亮的房子,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生一个可爱的孩子,日子悠悠过,是所有人羡慕的样子,是小镇给予的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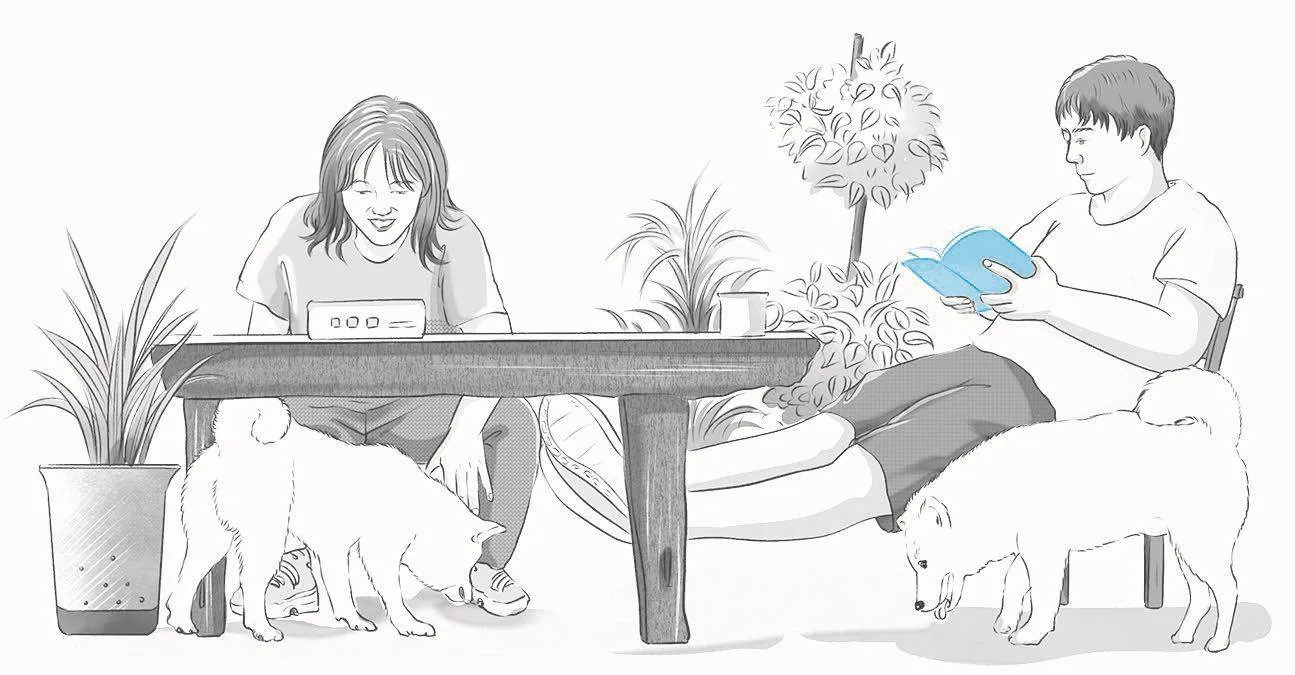
然而,幸福的模样是相似的,沉默的大多数也是相似的。在这个熟悉的小镇,每棵树是相似的,每个人的早餐是相似的,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也是相似的。渴望不同,反倒成了异类,在小镇里显得格格不入。
寻找不同可笑吗?一点也不可笑。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彼得·汉德克说:“我是凭借不为他人所知的那部分自己而活着。”理想主义大概就是这样:深知相同而去寻找不同。
也许搭上逃离小镇的高铁,就能摆脱平庸;也许逃离小镇的相同,就能将自己的独特安放;也许逃离小镇的日复一日,就能拥有充满无数可能的明天。
也许,也许,小镇该是逃离的。
几年前,小镇乐队“五条人”火了。
他们随便说几句话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欢乐,随时上热搜。他们穿着“破拖鞋”、说着咸湿的广东普通话、在《乐队的夏天》讲着三分钟的“脱口秀”、随心所欲换歌,把自己成功“淘汰”,有小镇青年的真实与不羁。
当他们的音乐第一个音响起,人们瞬间回到熟悉的小镇,回到那些最为平凡,亦最为真实的日子;令我们恍悟,那个曾经厌恶的小镇,原来在走出去后才发现它的美好。
外面的世界,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互不干扰,很少一家人团坐吃饭;不带手机导航,可能随时都会迷路……
而我们的小镇呢?曾经嘈杂零乱的菜市场,走出去才发现那里的热闹是最为零碎的热爱;曾经吃腻的街边酸辣粉,走出去才发现那是最为温情的安慰;曾经拥挤不开阔的小街道,走出去才发现那是回家最近的路。
小镇早已不知不觉成了我们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不急不缓,只活在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