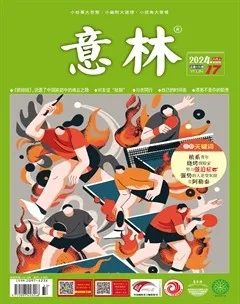我,“985”工科女转行做厨师
一个人选择成为厨师的故事本不应该有什么特殊的,但如果加上一系列修饰语——“‘985’名校生”“建筑系转行”“海外留学”“‘95后’女生”,或许应该再加上“在被男性统治的充满野蛮、汗水、油烟的后厨里”——这个故事就很难不变得激动人心。今年28岁的崔迪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她来自新疆,是上海两家融合菜餐厅的主厨。一路走来并不顺遂,崔迪到底经历了什么?
以下是崔迪的自述。
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做厨师
上大学的时候,我看了动画片《中华小当家》。主角是一个13岁的中华少年,他说想要做出让人信服的料理,这也是我做菜的初衷。同济大学一直有“吃在同济”的说法,每年都有“厨神争霸”大赛。我觉得很好玩,每年都报名参加,第一年没进决赛,后两年都得了冠军。
第一次参赛之前,我没怎么做过饭,只能在宿舍里开小灶。那时候烧的菜比较简单,可乐鸡翅、大阪烧……做完就和室友一起吃,如果大家觉得好吃,我也会很开心。当时,我觉得自己也许可以尝试把厨师当作职业,就去学校附近的餐厅兼职,体验一下真正的后厨工作是什么样的。
当初报考同济大学建筑学院的风景园林设计专业,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这个专业的介绍,说它是用人类所知道的生物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以为这个专业就是种种树,我还挺喜欢动植物的。其实做菜也一样,去了解食材的特性,对它们进行一些“解剖”和“重置”,最后它们变成美食。大学毕业前夕,我本想升校内的研究生,但没有拿到名额,便想去法国学厨师。但这个决定被家人阻止了,我爸说,读了本科再去读专科不合理,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做厨师?我妈却说,如果你真的喜欢、能够坚持做下去也是可以的。
最后,我们都做了妥协,我先去瑞士读酒店管理的研究生,再找机会学厨艺。

在瑞士读研,有很长的实习时间。我在米其林网页上把瑞士的餐厅投了个遍,最后面试上了比利时一家二星餐厅。通过面试的那天晚上,我连洗澡时都在傻笑。
在比利时的日子很纯粹,也很封闭。后厨里只有我一个女生,而且是亚洲人。每天起床到上班大概只有15分钟,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
那时,我经历了厨师生涯里最难挨的时光。有时候会不小心割伤自己,有时候则因为食物过敏浑身又肿又痒,此外,还要忍受同事的嫌弃和冷暴力。
2020年,我开始了正式的厨师工作。法餐后厨极度讲究等级秩序,更别说餐厅里来一个女生。西餐后厨对于体力要求没有那么高,反而耐心、细致的女生会更有优势。中餐馆后厨对女生来说相对更难。
我记得当时去一家中餐厅面试,负责人把我带到后厨,把厨房的燃气灶和抽油烟机打开,整个厨房“呼呼呼”地响,声音很大。他说:“你来掂一下这口锅。锅里需要装满水,把它掂平,稳住15秒。”就算对男性来说,也很需要力气。他想让我知难而退。
颠勺是中餐后厨的基本功,既靠技术又靠体力。大家下班后,我就加班练习颠勺。
如何审视“学历浪费”这件事
入行时,我24岁,当时实习的比利时餐厅档口的负责人才21岁。
24岁对于从厨来说已经很老了。有时候会觉得我绕了好远的路才走到这里,也有人说我学完建筑再去当厨师是“学历浪费”。
但仔细想,每一步都没有浪费。记得刚投递实习简历的时候,那家比利时餐厅官网上主厨介绍中的一句话,深深击中了我:“我一直以来想成为建筑师,于是我在盘子里搭建我的作品。”
主厨设计的菜品里,也有风景园林设计的思维:biotope(群落生境)、aqua(水)、flora(植物群)、fauna(动物群)。我当时忍不住惊呼:果然,建筑和烹饪是相通的!
风景园林设计专业教会了我设计的思维,我觉得这也是我能这么快成为主厨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厨师来说,怎么设计一道菜是需要自己领悟的,它没有具体的方法论。厨师需要的,除了审美,还有你对不同风味、不同食材的组合。比如,西餐里面会做很多蔬菜泥,也会做很多脆片,它们搭配在一起,是一种质地的碰撞,脆的东西和很滑的东西混在一起,会产生变化和复杂的口感。虽然风味不一样,但两种食材搭配起来必须有共同点。比如,小鸡炖蘑菇,鸡和蘑菇的共同点是鲜味。但我对食材没有设限,怎么组合都可以,只要做出来好吃。
现在来看,我好像是幸运的。很多人会来问我转行的经验。我的从厨之路其实很坎坷,留学花了30万元,回国后的第一份厨师工作,月工资只有5500元。后来想去中餐后厨,却总被劝退。疫情防控期间,餐厅不营业,工资几乎没有,每个月还要交房租,我只好先找了一份美食编辑的工作。即便这样,做了选择之后,我就不会再去对比。
所以,比起寻找什么是热门的,跟风报专业,对我来说,了解自己、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更重要。因为真正的热爱是不会背叛你的,它会跟着你一直走下去。
为什么有人总觉得做厨师不如做建筑师,其实大家不是很愿意说自己的志向是做一个服务人员。在瑞士读酒店管理专业时,老师跟我们说,服务也是一门需要智慧的学问。作为厨师,我觉得能通过自己的创造,让别人觉得好吃,这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