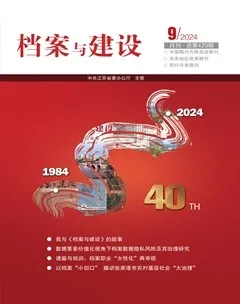遮蔽与规训:档案职业“女性化”再审视
摘 要:档案职业中女性占比更多是既存的现象,但档案职业“女性化”是基于现象产生的论断。对该论断的形成进行溯源,可发现其存在标准不一、逻辑预设等问题。此外,该论断的加强更遮蔽了档案职业存在的性别垂直隔离与“地板效应”等问题。进一步透视上述现象与论断,可发现性别本质主义与职业刻板印象规训了从业者与研究者,被建构出的“档案职业女性化特征”需要予以匡正。未来的档案职业讨论应倡导“去性别化”,不仅有利于档案职业吸纳多元化人才,也有助于实现对档案工作者个体素质的聚焦、整体队伍的关注,建构起性别平等的职业文化,从而推动档案职业与女性就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档案职业;性别平等;职业性别隔离;职业刻板印象;“女性化”
分类号:G279.2
Covering and Training: A Reexamination of the Feminization of the Archival Profession
Xie Shiyi, Zhang Yifan
(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
Abstract: It is an existing phenomenon that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in archival profession is higher, but the “feminization”of archival profession is the assertion based on the phenomenon. Tracing the origin of this asser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different standards and logical presupposition. In addition, the strengthening of this assertion has obscured the problems of vertical gender segregation and "sticky floor effect" in archival profession. Further examining the above phenomena and asser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gender essentialism and occupational stereotype have disciplined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therefore the constructed “feminine characteristics of archival profession” need to be corrected. In the future, discussions of archival profession should advocate “de-genderization”, which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absorptiiMq42Krs1eJb8tLbqvpzHgtuI3aRboPDg/y/D627PZA=on of diversified talent in archival profession, but also helps to realize the focus on the individual quality of archivists and the whole team, and build a gender-equal professional culture,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al profession and female employment.
Keywords: Archival Profession; Gender Equality; 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 Occupational Stereotype; Feminization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妇女平等就业和妇女事业发展。2021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要逐步消除职业性别隔离,促进女性对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掌握和应用。[1]2023年5月,《中国妇女报》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也进行了“打破偏见,科研有她”的宣传,致力于打破女性职业刻板印象。2024年4月,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女性申请年龄放宽至40岁,旨在为女性创造更为友好的科研环境,拆除女性科研人员的隐形障碍。针对女性的职业性别隔离与职业刻板印象已经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在此背景下,档案界对于女性工作者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2021年国际妇女节,《中国档案报》推出了专门文章展现档案中记录的女性贡献,以及当今女性在全球档案事业发展中的职责担当,强调档案部门既要鼓励女性主动寻求档案职业发展的机遇,也努力促进女性在职业上的平等发展,打破社会对职业女性的固有印象。[2]我国档案界也有学者提出过档案职业“女性化”的观点[3],认为档案工作者中女性占比较多且女性有着从事档案职业的优势。然而,亦有学者指出档案职业“女性化”观点并不合理[4]。且最近的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字揭示,近年来档案专职人员中女性所占比例变化不大[5]。如此,档案职业是否存在“性别”特征,在提倡平等就业、消除对女性偏见的当今社会,档案职业“女性化”这一论断对于档案职业与女性就业又有何影响,相关问题值得思考并有待解决。
1 溯源:档案职业“女性化”论断的提出
档案职业具有“女性化”趋势这一论断,首次出现是在2001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举办的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21世纪的社会记忆”上,胡鸿杰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女性化:中国档案管理的职业走向”议题。[6]在这之前,俞志华在《谈档案队伍的最佳结构》中已提出了档案队伍须关注性别结构的问题,认为男女在心理、生理等方面有诸多区别,女同志细心、认真,可安排在档案整理、提供利用等岗位,男同志则可安排从事档案收集与深层次开发。[7]
在档案职业具有“女性化”趋势这一表述被提出后,多位作者表达了不同观点。王协舟[8]提出档案职业的发展趋势之一便是档案职业主体具有女性化趋势;饶圆[9]则认为仅从档案职业女性所占比例65%左右很难得出“档案职业女性化”的结论;王玲等作者[10]则直接沿用了前人“档案职业女性化”这一表述,认为这一论断体现了女性性别优势,同时指出社会迫使女性将家庭放在首位,从而使档案职业成为女性最佳选择,并且提出在信息技术方面女性档案职业者明显处于弱势,因此在发挥性别优势的同时必须加强学习,更新知识。
2008年,胡鸿杰等[11]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基于统计结果,他认为女性在档案专职人员队伍中占有优势比例,同时受女性的先天性格特征和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档案职业成为女性发挥性别优势的重要领地。最后,胡鸿杰也提出,应正确引导社会尤其是女性树立正确的档案职业观,淡化档案职业的性别色彩,吸引更多男性加入档案职业。
近年来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对细节的补充上,杨绿汀[12]撰写了相关硕士学位论文,文中通过调研,系统补充了数据,得出女性数量明显大于男性数量的结论,认为档案职业女性化现象已是既定事实。马伏秋[13]则在概念界定上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女性化”意味着“档案职业主体中原先女性没有那么多,现在越来越多”,而在女性进入职业工作领域比例增多的背景下,档案职业女性占比在此期间增加1.5个百分点,是符合社会发展的一种十分正常的现象。
纵观以往对于档案职业“女性化”的论述,可以发现:首先,大部分学者(如胡鸿杰、王协舟、王玲等)是认同档案职业女性占比较多即可被视为档案职业存在“女性化”趋势或特征这一论断的,仅有少数学者(如杨绿汀)基于女性占比更多且有增加趋势,直接将档案职业“女性化”视为现象;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如饶圆、马伏秋)对此论断的依据提出了质疑。其次,大部分学者认为女性具有从事档案职业的优势是因为女性的一般特质适合档案职业,并且女性自身的择业观念使她们选择了档案职业,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了社会的传统性别观念也是女性选择档案职业的影响因素。最后,对档案职业“女性化”进行关注的学者,通常都认为档案职业女性占比更多会产生负面影响,档案队伍的性别结构失衡不利于档案事业长久发展,并对此提出改进对策。
2 分析:档案职业“女性化”辩证
2.1 遮蔽:档案职业“女性化”论断之弊
档案职业中女性占比更多是既存现象,但档案职业“女性化”是大多数学者基于现象产生的论断。通过回溯可发现,档案职业“女性化”这一论断,既有研究存在内涵指向不一、隐含预设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论断的一再重申和强调使得原有的职业性别探索趋于平面化,一些细节被比例所遮蔽,应有的完整、立体的职业性别抽象并不到位。
(1)对档案职业“女性化”未形成一致内涵解释
某一职业“女性化”尚未有统一的定义,但社会学中有feminization一词,指女性在某一职业占较大比例而使这一职业女性化。[14]较早关注到“女性化”的教育职业,认为“女性化”往往指的是某一职业队伍中女性的数量不断增加,且其比例明显高于社会常态性别比例(约1∶1),以及教师群体成员个性及行为带有明显的柔软化特征的现象。[15]
关于档案职业“女性化”,马伏秋[16]对此的界定是“档案职业主体中原先女性没有那么多,现在越来越多”。胡鸿杰等[17]则根据档案职业从业女性的比例不断提高,认为档案职业具有女性化趋势,但对于档案职业“女性化”并未给出明确定义。杨绿汀[18]认为档案职业女性化这一现象的形成是由于档案职业女性从业人员在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但对于档案职业“女性化”的含义也未进行阐述。此外,不少学者直接使用了档案职业“女性化”这一表述,并未对其含义进行解释。
可见,当前学者对于档案职业“女性化”并未形成一致的内涵解释,并且,档案职业“女性化”这一论断得出的依据大多还是档案职业中女性占比更多这一现象,立足点基本在“女性”而非“化”上。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出版的《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2017年我国图书、档案、文博人员女性总人数16.5万,占比65.5%,这与1996年至2004年女性档案专职人员所占65%左右[19]的比例并无明显差异。档案职业从业者中女性占比更多是既定的事实,但女性所占比例多年来并未有明显提升——这显然与当初学者提出的档案职业具有“女性化”趋势不符。
(2)对档案职业女多男少现象的成因Sgyx/Vp6xIyXeDSfVdope+Qek0tnmOOztBP7CwCx52M=与不利影响存在预设
一方面,现有研究在分析档案职业“女性化”的成因,即女性选择档案职业的逻辑时,通常从社会逻辑与先天逻辑两方面进行分析。社会逻辑方面,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女性选择档案职业也是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社会对于女性常以对家庭所尽的义务而非职业成就来衡量她们的价值,相对稳定、轻松的档案职业便成为最佳选择。[20]但关于先天逻辑方面,大多学者认为女性具有从事档案职业的一般性格特征,即“女性天生具有耐心、细心、吃苦耐劳等特质,与传统档案工作所需要的特质十分契合”[21],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女性的自然亲和力能够提高档案服务工作的质量、提升档案部门的形象[22]。然而,女性与男性实际上并不存在多少天生的差异,有研究[23]对1400多个大脑的MRI(磁共振成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女性的大脑并不存在明显的内部一致性,男性的亦是如此,这些发现与之前相关的研究一致,即不同性别群体间大多不存在能力和素质差异,即使存在也非常微弱。可见,所谓的适合档案职业的一般性格特质并非女性天生便具有的,学者所认为的女性从事档案职业的先天逻辑无法自洽。
另一方面,档案职业“女性化”的论述通常是伴随着女多男少这一现象需要改变的观点出现,即便学者认同了女性具有从事档案职业的优势,依旧认为“女性化”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部分学者提出淡化职业性别色彩的对策时,强调需要吸引男性加入档案职业,原因却是男性在程序设计、软件开发方面具有天赋[24],女性从业人员信息化技术应用能力薄弱[25]。然而,根据韩锡斌等对中国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调查,女教师与男教师的信息化能力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26],可见,所谓的女性的信息技术能力薄弱这一理由并不一定成立。并且,档案职业女性工作者实际上也为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妇女报》就对档案馆的女同志推动实现馆藏档案数字化管理的事迹做出了报道[27],“安全计划”项目(Project SAVE Archives)也是由女性Ruth Thomasian创建[28],由女性档案工作者Suzanne Adams推动了项目的数字化发展[29],女性档案工作者对于档案信息化发展的贡献是不容小觑的。除此之外,学者并未给出较为合适的女性占比多不是好现象的理由,通常只是直接提出需要优化档案人才队伍的性别构成以推进档案事业顺利发展[30]。
因此,档案职业“女性化”这一论断,很可能是学者受到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在预设了女性的信息化技术能力薄弱等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的情况后,将档案职业女性占比更多这一事实,变成了需要关注和改变的“问题”,“女性化”与否的论断通常包含着学者自己的价值判断,并非对档案职业女多男少现象的客观反映。
(3)忽视了档案职业中存在的性别垂直隔离情况与“地板效应”
职业性别隔离现象指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因为性别差异而被分配到不同类型的职业中,从事不同类型的工作;职业性别垂直隔离则指在相同职业中,男女分布可能表现为某个性别总是处于高级别或水平[31]。根据201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的数据,2017年我国正高级职务中女性占比仅32%,档案职业的具体情况没有进行数据公开。但笔者对目前我国国家档案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31个省级(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馆的领导队伍中女性占比情况进行了部分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总体上档案馆领导队伍中,女性占比约24%,大约1/3档案馆的领导队伍中完全没有女性。可见,档案职业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群体中,女性占比是极低的,档案职业性别垂直隔离的情况是存在的。
除了性别垂直隔离现象,还需要注意到档案职业存在的“地板效应”,即档案职业中女性沉淀在基层的比例更高。[32]胡鸿杰等在《档案职业状况与发展趋势研究》中,对女性档案专职人员统计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1996年至2004年全国女性档案专职人员所占比例较稳定,大致维持在65%左右;县级女性档案专职人员基数最大,所占比例最高,且总体呈现了明显的增势;中央、国家机关女性档案专职人员基数最小,所占比例最低,且呈现了明显的递减趋势。[33]全国女性档案专职人员中,占比最大的是基层档案工作者,而非所有档案部门女性占比都更多,“地板效应”十分明显。关于图情档学科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显示,女性表现出科研论文产出底层人数过多,中层不足的情况,并且女性教师中拥有中高级职称的占比仅为男性的75%左右[34],女性职称晋升的速度在总体上低于男性,女性职称晋升的困难程度要高于男性[35]。在档案科研工作者中,女性沉淀在基层并且晋升困难的情况也同样存在。
虽然档案工作者总体上看来女性占比更多,但实际上大部分女性只是承担了基础工作,沉淀在基层,并且档案职业领导层中仍然EllvB7ggjhdq8E0UroaiJA==是男性占比更大。因此,仅以档案职业总体的女性占比为多数,就认为档案职业存在“女性化”趋势,是不合理的。并且,这一论断还会造成对档案职业同样需要引起关注的性别垂直隔离现象和“地板效应”的遮蔽。
2.2 规训:档案职业“女性化”现象之本
对科学解释进行匡正固然重要,“错误”背后的原因更值得深思。无论是女多男少的职业现象,还是论断为“女性化”并“问题化”的研究现象,都只是社会性别观念之于档案职业的投射。两种现象的一致(确有更多女性进入档案职业)与不一致(女性在职业中占比更多不一定等同于“女性化”且不利)都十分生动地展现了社会的规训,甚至后者展现得更为明显——社会规训之于思想的影响往往早于行动。一切无常事物,无非譬喻一场。在档案职业性别研究中,一些机理有迹可循。
(1)性别本质主义对于性别观念的深刻影响

在学者论述为何女性更加适合进行档案管理工作,并且具有从事档案职业的先天优势时,大多数学者的理由都是女性的一般特征更加适合档案工作,比如女性的性格安静、更有耐心,适合从事比较稳定、舒适的工作;而男性性格有冲劲、耐心缺乏,适合有创造力、竞争力的工作。[36]但这很可能是由于学者陷入了性别本质主义的误区,将女性生理特征作为其性别建构的基础[37],把女性性格特征归纳为温柔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将男性特征归纳为理性的、独立的、理智型的[38]。性别本hIWJpg5DBR0vT+sk+2AlPg==质主义宣扬生理决定命运,通过社会习俗、文学作品、媒体等各种途径,润物无声地使其内化成了人们共同的社会心理和集体无意识。[39]这可能解释了为何学者会认为女性天生便具有这些适合档案职业的内在特质,将社会塑造的性格特征作为了档案职业女性适合从事档案职业的先天优势,同时也解释了为何学者认为女性占比更多会对档案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意识层面上的影响通常悄无声息,难以被察觉,并且渗透到各个方面。社会希望女性更加耐心、细心,从事更加稳定的工作以适应社会分工的需要,并且在教育过程中对于女性和男性也是以不同的标准进行教育。虽然国家一直鼓励女性就业,但社会仍然强调女性照顾家庭的责任和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40],将所谓的“女性性格特征”作为女性更适合且更多从事“辅助性”和“服务性”工作[41]的原因。档案管理工作的特性是辅助性、服务性、保障性的[42],因此,档案工作便成为社会规训下适合女性的职业选择。
(2)职业刻板印象对职业选择的直接作用
职业刻板印象指的是对某种职业的预想态度,职业刻板印象往往会决定求职者的“职业偏好”[43],即大多数人会根据对职业的刻板印象进行职业选择,并且个体对某个职业的认知越少,刻板印象就越强[44],而社会规训的各个环节,例如家庭、学校、社会舆论等,都会对个体的职业认知产生影响。
虽然我国档案事业不断发展,但社会民众的档案意识仍然存在着短板[45],民众对档案职业的认知度并不高且具有明显的刻板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众对档案职业的了解与选择。李秋丽[46]曾对普通公众的档案馆认知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档案馆的知名度偏低,在公众心中也是传统的严肃封闭形象,公众甚至都不知晓档案馆及档案展览。Caitlin Patterson[47]研究揭示公众对档案工作的传统印象是档案工作者惯于采取消极被动的态度,虽然愿意奉献工作,却既无法掌握财富也缺乏影响力。在这一背景下,未接受过档案专业教育的人往往可能根据对档案职业的预想来判断自己是否适合该职业。
此外,社会的职业性别刻板印象也直接影响了两性对于档案职业的选择。在性别本质主义的深刻影响下,社会的职业性别刻板印象随之形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包含一个由个性特征、社会角色、行为和身体特征联结而成的网络,并且具有连锁性的复杂关系,职业性别刻板印象会直接影响人们对女性和男性在各种社会背景下的行为的推断。[48]李佳宁对大学生的职业性别刻板印象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存在外显和内隐的职业性别刻板印象,认为男性适合从事专业技术型职业,女性适合从事服务型职业,并且男性的刻板化程度显著高于女性[49],社会规训对于男性的作用更加明显。社会对于男性往往提倡阳刚、理性,认为男性应该从事有风险但高收入的职业,档案职业在人们的印象中并不属于这一类职业,并不符合男性的职业偏好,而男性的刻板化程度更高,这使得愿意学习档案专业和选择档案职业的男性可能迫于社会压力转向了所谓的适合男生的专业与职业。
3 讨论:档案职业“性别化”探讨澄明
3.1 档案职业是否存在“性别”特征
其一,档案职业对于男性求职者不存在主动排斥的情况。档案职业中女性占比更多是目前的现象,但近年来档案职业女性从业者的比例并无显著上升,这意味着也有男性在不断进入档案职业。况且档案工作并非仅能由女性完成,对男性不存在主动排斥的情况——不像母婴护理师(俗称月嫂)等职业存在明显的职业性别排斥,只是男性更少选择档案职业,而这种更少的选择并不是因为生理上的不适合,往往源自心理上的标签化认知。
其二,已进入档案职业的男性的专业认同与女性无显著差异,同时掌握着话语权与影响力的档案职业领导队伍中男性占比较高。作为职业动机的主要组成部分,职业认同感在档案人员从事档案8t0k+dKr5uCBmUWcdDCWcg==工作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50]根据余益飞[51]的调查,就档案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水平来说,虽然女性高于男性,但不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在档案学教师中,男教师的职称普遍高于女教师,工资水平也相对较高,可以获得更多学术资源,认同水平略高于档案学女教师。档案职业中占比较少的男性,并不存在明显的“局外人”认知,相比于获得更少资源与话语权的女性,甚至有时认同水平更高。
基于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尽管档案职业中女性工作者占比更高,但档案职业并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壁垒”,男性求职者未受到档案职业的主动排斥,已加入档案职业队伍的男性在职业认同上也与女性无明显差异,因此,档案职业并不存在明显的“性别”特征。
3.2 档案职业“女性化”论断对档案职业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虽然档案职业“女性化”的论断让社会关注到了档案女性从业者对于档案职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但档案职业“女性化”这一论断,很有可能在强调消除性别偏见的当今社会,对档案职业和女性工作者带来潜在的消极影响。有研究表明,给某项工作贴上“女人的工作”这样的标签时,会让从事这项工作或希望从事这项工作的男性面临负面偏见。[52]当学者对档案职业“女性化”的论断一再提及并表示赞同时,无疑是给档案职业贴上“女人的工作”的标签,这将弱化所有档案工作者为档案职业发展共同做出的努力。
与此同时,学者在阐述档案职业“女性化”会对档案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时,强调了女性从业者存在着以下情况:信息化技术应用能力欠缺,对新兴档案服务方式不够敏感,成就动机低、懒于自我发展[53],选择档案职业是源于自我否定、不思进取的想法等[54]。这些论述过于强调了女性工作者的缺点与短板,而且这些缺点可能只是个别档案工作者存在的情况,也不仅限于女性。因此,当不断强调档案职业“女性化”这一论断时,不仅是在不断加强对档案职业的刻板印象,也是在不断强化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这不仅会让社会公众对档案职业的认知产生偏差,也不利于消除性别偏见,建设性别平等的文化。
3.3 档案职业“去性别化”的重要意义
2013年开始,全国档案事业统计调查工作已不包含对档案人员性别的统计,这或许是官方层面有意对档案职业“性别”特征的弱化。研究表明,女性和男性的差异是被文化放大了的,实际上性别内部的差异远远大于性别之间的差异,并且所谓的“女性化”职业并非基于所谓天生的性别生理差异,而是基于文化人为建构的结果。[55]因此,对档案职业的“去性别化”意味着淡化对“性别”角色的关注,这不仅有助于对档案工作者整体的关注,更有利于档案职业建构一种性别平等的文化。
第一,“去性别化”有利于档案职业吸纳多元化人才。第五十六届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强调,消除两性偏见不仅有益于妇女儿童,而且有益于男人和男童,他们可以得到通常被认为“女性化”的就业和机会。[56]档案职业“女性化”的论断不仅有可能让想进入档案职业的男性转向所谓的“男性职业”,也可能让不具备所谓“女性特质”的女性被阻拦在外。人才是新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与核心动力[57],如果女性和男性都能够脱离性别视角来进行职业选择,摆脱档案职业“女性化”的影响来看待档案职业,那么就会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兴趣、能力来选择专业和职业,而非考虑所谓的“女性”和“男性”气质,档案职业也能够吸纳更加适合档案工作的多元化人才。
第二,“去性别化”能够加强对档案工作者整体的关注与培养,弱化对性别群体的特别关注。孙大东关于档案职业公信力的调查显示,在档案职业主体中,档案职业道德对公信力的影响力最大,档案职业人员的性别、年龄等因素的影响力微乎其微[58],因此,“去性别化”可以聚焦讨论档案职业更加需要关注的问题。同时,档案职业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阶段,“去性别化”有助于对所有的档案工作者和档案专业学生开展包容性的数字素养教育,消除课程开展过程中的性别偏见[59], 以助力档案工作转型为目标,而非以解决所谓的女性工作者的短板为目标。
第三,“去性别化”有利于实现对档案职业工作者个体素质与能力的聚焦。档案工作并非由某一性别群体的工作者来开展,也并非由具备某些性格特质的群体参与工作,而是由一个个不同的工作者来共同推动档案职业的发展。高素质的档案干部人才队伍,就人员结构而言,应是配置合理、人尽其才的[60],因此,档案职业的“去性别化”可以凸显个体间的差异和个人的优势,档案馆在招聘和分配工作时,便能够更加注重个体的能力和特质与岗位的匹配程度,而非因为工作者的性别就预设其更适合某项工作或某一岗位。
4 结 语
档案职业“女性化”这一观点体现了学者对于档案职业中占据较大比例的女性从业者的关注。然而,这一论断本身存在一定的逻辑问题,并因结论的扁平遮蔽了背后更为立体且深刻的职业现状。这一研究现状的出现,结合档案职业中切实存在的女多男少的现象,生动地展现了职业选择中社会之于个体的规训——在性别本质主义与职业刻板印象的影响下,档案职业被建构成“女性化”从而“问题化”。在倡导性别平等的今天,“去性别化”应该成为档案职业探讨的取向。望此文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阐释,进而推动档案职业与女性就业的健康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档案文化要素的本质及其演化研究”(项目编号:20CTQ03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贡献说明
谢诗艺:确定论文框架,撰写与修改论文;张伊凡:整合资料,撰写论文初稿,参与论文修改。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EB/OL].[2023-06-11]. https://www.nwccw.gov.cn/2021/09/27/99339694.html.
[2]洪秋双,雒方莹.档案与女性职业发展的紧密关联[N].中国档案报,2021-3-4(03).
[3]学者胡鸿杰于2001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举办的“21世纪的社会记忆——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上,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女性化:中国档案管理的职业走向”议nxb6j1lUaJ/WSM/UyLZb7sYfTbsaH7Mf1xd2BYLSyc8=题,首次提出了档案职业“女性化”这一观点。
[4]如饶圆、马伏秋等学者曾提出反对意见,详细论述见本文第一部分“溯源”。
[5]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出版的《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2017年我国图书、档案、文博人员女性总人数16.5万,占比65.5%,与1996年至2004年全国女性档案专职人员所占65%左右比例无显著区别。
[6]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论文集编委会.21世纪的社会记忆 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论文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42-147.
a+T6zLEXc7BAeUBCD51V1QbJcJaYAGDG2/5idwzLwxA=[7]俞志华.谈档案队伍的最佳结构[J].浙江档案,2000(11):11.
[8]王协舟.档案职业状况与发展趋势研究——研究意义与基本思路[J].档案学通讯,2006(1):12-14.
[9][20][22][24][54]饶圆.理性回归:“档案职业女性化”的质疑与反思[J].档案学通讯,2008(2):13-16.
[10][21][36]王玲,华惠.档案职业女性化的一些思考[J].档案与建设,2008(12):20-21.
[11][17][19][33]胡鸿杰,吴红.档案职业状况与发展趋势研究[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134,132,131,131.
[12][18][25][53]杨绿汀.我国档案职业女性化现象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7:V,12,49,54.
[13][16]马伏秋,李丽环.档案职业空间拓展路径探析[J].档案学研究,2018(5):91-95.
[14]苏红.多重视角下的社会性别观[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74.
[15]傅松涛.教师群体女性化现象初探[J].教育评论,1997(5):22-24.
[23]相关研究参见 JOEL D,BERMAN Z,TAVOR I,et al.Sex beyond the genitalia:The human brain mosaic[J/OL].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5,112(50):15468-15473.[2023-07-09].https://doi.org/10.1073/pnas.1509654112.该篇文章截至2023年11月7日,被引用297次,期刊近5年影响因子IF12。
[26]韩锡斌,葛文双.中国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调查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8(7):7.
[27]贾莹莹,杜峰,陈玥.数字化管理让档案“活”起来[N].中国妇女报,2023-04-24(08).
[28]Project SAVE helps Armenian culture connect to its roots[EB/OL].[2024-01-09].https:// hyetert.org/2018/02/14/project-save-helps-armenianculture-connect-to-its-roots/.
[29]The Armenian Weekly.Project SAVE Archives announces professional transitions,welcomes new archivist[EB/OL].[2024-01-09].https://armenianweekly. com/2020/12/14/project-save-archives-announcesprofessional-transitions-welcomes-new-archivist/.
[30]钟婷.档案馆档案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问题研究[EB/OL].[2023-07-01].https://sdaj. hunan.gov.cn/sdaj/dagyw/daxh/xslwdag/201609/ t20160927_3293422.html.
[31]童梅,王宏波.市场转型与职业性别垂直隔离[J].社会,2013(6):122-138.
[32]吕芳.我国公共部门的职业性别隔离问题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22(2):108-115.
[34]谭春辉,汪红信,王仪雯,等.图情档学科高校教师科研论文产出的性别差异[J].图书馆论坛,2023(9):65-75.
[35]谭春辉,李明磊,王仪雯,等.科研人员职业生涯成长轨迹的性别差异研究——以图情档学科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获批者为例[J/OL].现代情报:1-16[2024-06-13].http://kns.cnki.net/kcms/ detail/22.1182.G3.20240130.1624.002.html.
[37]章燕作.多丽丝·莱辛作品中的空间意象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2:136.
[38]章立明.身体消费与性别本质主义[J].妇女研究论丛,2001(6):4.
[39]韩廉.解构性别本质主义:女性主义对先进性别文化的贡献[J].妇女研究论丛,2004(5):10-13.
[40]许艳丽.基于社会性别的家庭时间配置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04:66.
[41]任远.转型期就业城市社区就业状况与社会政策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78.
[42]张辑哲.维系之道:档案与档案管理[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103.
[43]李竹梅.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M].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16:150.
[44]张益民.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研究[M].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21.
[45]黄夏基,刘鹏飞,黄宣坚.论档案意识普及与提高的主要目标群体及推进路径[J].档案与建设,2023(9):24-27.
[46]李秋丽.公众视角下的档案利用服务探析——基于普通公众的档案馆认知调查[J].档案管理,2022(4):99-103.
[47]PATTERSON C.Perceptions and Understandings of Archives in the Digital Age[J].The American archivist,2016,79(2):339-370.
[48]克劳福德,昂格尔.妇女与性别——一本女性主义心理学著作[M].许敏敏,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109.
[49]李佳宁.性别角色与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的关系及其干预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20:56.
[50]孙大东,白路浩.论《“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人文关怀理念的呈现及实现[J].档案与建设,2021(7):9-13.
[51]余益飞.档案学专业认同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2:33.
[52]特博,多林.我们为什么会对工作怀有性别成见[EB/OL].[2023-08-10].https://www.bbc.com/ ukchina/simp/horizon-40857309.
[55]莫兰.女性职业发展“去性别化”仍任重道远[N].中国妇女报,2018-12-15(02).
[56]妇女地位委员会.使年青男女、女孩和男孩参与促进性别平等[C/OL].[2023-08-12].https:// www.un.org/womenwatch/daw/csw/csw56/panels/ panel5-moderators-summary_ch.pdf.
[57]周林兴,黄星.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档案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逻辑理路[J].档案与建设,2024(1):3-10.
[58]孙大东.档案职业公信力调查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7(4):49-53.
[59]卜卫,蔡珂.数字素养、性别与可持续发展——从“性别与发展”理论视角探讨数字环境下如何促进性别平等的发展[J].妇女研究论丛,2023(3):44-57.
[60]顾俊.打造高素质档案干部人才队伍[J].档案与建设,2023(7):4-7.
(责任编辑:张 帆 李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