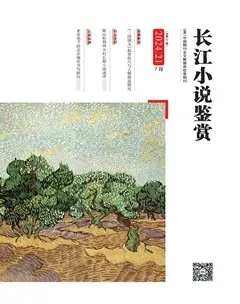从疏离到对话:萧红的离乱之感与抗战前期小说创作
[摘 要] 在回忆学生时代的集会经历的文章中,萧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疏离,这一叙述姿态关联着萧红独特的战争理解。对战时弱势群体与日常生活的持续关注使得凝聚着个人感觉的“旷野”被重新激活,成为萧红在文学中追问个体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意象。“旷野”背后是萧红主张作家贴近表现对象的战时文艺观。梳理《旷野的呼喊》集可以看到萧红与抗战文艺主流的紧张关系,以及萧红的战时书写与文坛中心的对话价值,进而使得对小说集的评价方式从美学的、抗战文艺的回归到更贴近萧红创作脉络的轨道中。
[关键词] 萧红 《旷野的呼喊》 抗战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21-0019-06
一、从“铁路”记忆到战时体验
1937年12月,《七月》杂志刊载萧红的《一条铁路的完成》,在这篇“救亡运动特写”中,萧红回顾了自己在哈尔滨读书时期参与学生运动的经历。为了反对《满蒙新五路协约》,保卫路权与主权,东北学生以及社会各界于1928年底发起游行示威活动。九年过去,为着抗日救亡的热情,萧红写下她在这次运动中的所见与感受,这篇小文中却记载了一段并不算“热情”的心理活动:
我只感到我的心脏在受着拥挤,好像我的脚跟并没有离开地面而它自然就会移动似的。我的耳边闹着许多种声音,那声音并不大,也不远,也不响亮,可觉得沉重,带来了压力,好像皮球被穿了一个小洞嘶嘶的在透着气似的,我对我自己毫没有把握。
“有决心没有?”
“有决心!”
“怕死不怕死?”
“不怕死。”
这还没有反复完,我们就退下来了。因为是听到了枪声,起初是一两声,而后是接连着。大队已经完全溃乱下来,只一秒钟,我们旁边那阴沟里,好像猪似的浮游着一些人。女同学被拥挤进去的最多,男同学在往岸上提着她们,被提的她们满身带着泡沫和气味,她们那发疯的样子很可笑,用那挂着白沫和糟粕的戴着手套的手搔着头发,还有的像已经癫痫的人似的,她在人群中不停地跑着:那被她擦过的人们,他们的衣服上就印着各种不同的花印。大队又重新收拾起来,又发着号令,可是枪声又响了,对于枪声,人们像是看到了火花似的那么热烈。至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完成吉敦路”这事情的本身已经被人们忘记了,唯一所要打倒的就是滨江县政府。到后来连县政府也忘记了,只“打倒警察;打倒警察……”这一场斗争到后来我觉得比一开头还有趣味。在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我相信我绝对没有见过,但是警察我是见过的,于是我就嚷着:
“打倒警察,打倒警察!”[1]
“没有把握”与“不怕死”之间的矛盾显露出萧红对集会的复杂态度,作者反复书写自己感到的压力,并发现了行动目的在狂热情绪中变得模糊不清。与“抗日救亡”热情高涨的氛围并不算融洽的这种叙述语调说明1937年的萧红已经觉察到了救亡运动所呈现的某种慌乱与幼稚的形式,以及运动中弥漫的让人备感沉重的流血氛围。
半个月后发表的《一九二九年底愚昧》中,萧红将抗日救亡运动的体验与“中东路事件”期间政府主导的学生游行联系起来。[2]虽然标题以“愚昧”区分了两次学生运动的性质,但自发示威与政府主导游行的并列仍产生了运动目的两相抵消、运动武力性质凸显的客观效果。冲突、暴力的一再彰显说明萧红的紧张情绪正指向运动本身。在思考集会限度与反刍个人体验的过程中,萧红确立了对学运与救亡的叙述姿态。
参与者萧红与回忆者萧红之间的张力为我们梳理抗战前期萧红的战争感觉提供了阐释空间。张力效果的来源可以追溯至萧红的战时体验:回顾学生运动经历时流露的复杂情绪显然与作者在上海、武汉战时的个体感受相关。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寓居于上海的萧红在次日写作《天空的点缀》,记录平常生活因战火颤动的时刻以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触,充斥着对战事的疑问与不确定。结尾处萧红将目光放在短刀上,“对于它我看了又看,我相信我自己绝不是拿着这短刀而奔赴前线”。刀、匕首与武器的反复辨认透露出战时环境下萧红对武力的绝对敏感。确认战争就是流血与暴力后,萧红难免感到沉重,随之陷入“战争是要战争的,而枪声是不可爱的”挣扎中。[3]而当着手抗战救亡的宣传写作,萧红自然能够发现学生游行与战争本身所共享的混乱形式,她开始剥离抗战热情中抽象、狂热的成分,识别暴力本身对个体心灵和具体生活的伤害[3]。
由于“铁路”事件带来的动乱感受关联着萧红的战争感觉,所以在这两篇回忆文章中,作者选择用“铁路”事件引起的日常生活经验与个人情感体验为战争想象赋形。在抗战前期,萧红对战争的理解存在着一种从“救亡”到“铁路”记忆的展开方式。
一年后写作的短篇小说《旷野的呼喊》里,“铁路”记忆在萧红笔下重现。小说讲述青年曲线抗战,破坏日本人修建的铁路最后被捕的故事,着重展示抗战边缘人物未知、迷茫与无助状态。此时“铁路”所代表的侵略、反抗与国别争端成为背景,小人物面对战争切身的迷茫与悲痛摆上前台。这显示出萧红试图对追溯“铁路记忆”时产生的困惑与无助进行清理。她将回顾游行时的压力与疑虑转化为叙述动力,将抗战救亡呼吁引起的反思推及日常生活层面,并把思考推进至更深刻的对战争中弱势群体的关照上。故事铺开的过程可视作萧红书写被抗战呼声屏蔽了的个体经验的过程,也是萧红在文学中疏解个人生活被战争挤占而产生的压力的过程。类似关怀在萧红以北上临汾的经历为素材创作的《黄河》中也有体现,小说以八路军与摆渡人的对谈为主体内容,二人对话时反复出现“死人了还打仗”的声音,涵括着以生老病死为代表的日常生活与战争对立的逻辑。可以看到萧红试图从日常生活的正当性出发,谴责战争时期的暴力因素。
在同时期的书评《〈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中,萧红记录了颇有意味的生活片段:因书中逃难经历与女性处境书写颇受触动,萧红引起了男性作家的嘲笑,遂决定外出买菜逃离言语刺激,回家的路上她看见了一个衣不蔽体躺在草堆中的老人。面对赤裸裸的贫困惨象,萧红虽然以“抗战”大环境为立足点进行了理性分析,对自己憎恶战争与流血的感性情绪予以否定,却仍在语调中流露出伤感。“我憎恶打仗,我憎恶断腿断臂,等我看到了人和猪似的睡在墙根上,我就什么都不憎恶了,打吧!流血吧,不然这样猪似的,不是活遭罪吗?”流血的痛苦与战乱的现实使萧红看到了被战争屏蔽的日常生活和更加悲惨的“偏僻人生”,战时环境下的实际生活场景与对其深入的思考共同构成萧红战争感觉的主体部分[4]。
可以认为,萧红强调战争的异质性,她理解的战争是一种对个人生活的强硬介入的战争,也是一种将弱势群体拉入更危险境地的战争。萧红是在民族情绪、日常经验与人道主义的多重立场完成对于战争的批判。从这个层面上说,《一条铁路的完成》具有超越了《七月》以“救亡运动特写”为其命名时所期待的阐释空间。
二、抗战背景下的“旷野”更迭
作为短暂地出现于萧红三十年代后期写作中的意象,“旷野”在不同文本中的意指有所区别。将“旷野”的更迭视作切口梳理此意象在各时期文本中的具体内涵,有助于进一步把握萧红如何将个人化的战争感觉诉诸文学写作中。
《牛车上》是萧红于1936年8月完成的短篇,在这篇以儿童视角创作结构的小说中,“旷野”跟随主人公悲惨命运的展开变换出不同面貌。小说开篇的“旷野”宽广自由,生机勃勃,行走在“旷野”中的人也充满活力。通过与萧红回忆“后花园”时颇为近似的诗性描写可以发现,此时的“旷野”意象关联着作者对自然的向往,对童年的追怀以及对无拘无束、自由生活的热爱[4]。但伴随五云嫂一家经历的揭开,“旷野”很快就暴露出荒芜的真实形态。遭受苦难命运的五云嫂朦朦胧胧地追问人生意义时,车夫无言地望向旷野,旷野也只是“昏昏黄黄的一片”。“旷野”之上的无常命运劫掠着生命,个体在“旷野”衬托下显得格外渺小。小说结尾一行三人在沉重氛围下走入人生的灰暗中,甚至这灰暗人生也无比漫长,“连道路也看不到尽头”。“偏僻人生”究竟会走向何方?经历多次冷眼、背叛和抛弃的萧红借“旷野”意象表达了自己对生命本相的洞察。萧红指出美好生活只是命运的面具,厄运到来之时,个体是如此脆弱的存在以至于无法改变命运的捉弄,只能选择在苦难中接受自己的宿命[5]。
萧红常以诗作形式表达自己对爱情的感受,“旷野”意象也出现于其稍晚发表的诗作里,在1937年1月完成的《沙粒》中,萧红不止一次地发出“我心中所想望着的只是旷野”的感叹,如其“海洋之大/天地之广/却恨各自的胸中狭小”,又如“世界那么广大/而我却把自己天地布置得这样狭小”。对于习惯了东京生活,渐渐远离感情苦恼的萧红而言,“旷野”是与围困着她的小天地形成对照的另一重人生态度,此时的萧红已经不满足于狭小的情感世界,她有意去以一种更广袤的方式思考人生[6]。
通过梳理可以看到,“旷野”意象所指内容与萧红的个人经验密切相关。写作《牛车上》时萧红刚到东京,远离熟悉的生活与社交空间本就使她常常感到寂寞,加之身体与精神状态并不好,萧红形容自己“孤独的和一张草叶似的”。充满苍凉之味的“旷野”也就成为作者独居异国、无所凭依、充满寂寥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创作《沙粒》时萧红克服了东京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在异国环境下逐渐成长为摆脱依附状态的主体。1937年底,在和萧军及友人的去信中,萧红对自己的生活和写作提出诸多积极的计划。[7]东京寓所的狭小也激发了她关于辽阔天地的想象,《沙粒》中广袤的“旷野”象征着萧红在逼仄空间里外溢的主体建设欲望。因此,东京时期的“旷野”说明作者正剥离掉写作中非个人化的部分,并试图从贴近自我需求的立场出发作有关人生、命运的思考。
两年过去,萧红于1939年初完成了《旷野的呼喊》的写作。将《牛车上》对“旷野”的理解与此文串联起来,就能发现陈公公在旷野中的呼号与车夫面向旷野的沉默有着近似之处:在命运的“旷野”上,人的质询得不到回答,呼喊除了导致受伤流血外不会引起任何变化。两篇小说中的“旷野”都指向底层人的心理状态与生存环境。通过对陈公公、院落和村庄四周空旷环境的反复描述,萧红展示了抗争者亲属迷茫而无所凭依的感觉,以及人无处躲藏、生存权利被剥夺、人生彻底陷入无解的极端境况。
与东京时期相比,萧红创作《旷野的呼喊》时的外部时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对日抗战开始。思考个人与时代命运的萧红必须在文学中承接这一变动,《旷野的呼喊》中的“旷野”自然呈现出不同于此前的特点。首先可以发现小说中“风”的意象十分突出,开篇就写风以野蛮的姿态席卷着一切。不只是旷野本身的荒蛮,无目的攻击着人与生存资源的风沙也在考验着陈公公一家。将视线放远又能看到村头庙堂前日本兵的大旗杆并不受风沙干扰,象征压迫与奴役的旗杆挺直在让陈公公颇为恼火的大风中,风沙与侵略战争共谋的本质由此揭示。“旷野”与“风”的双重威胁表明了在侵略战争的炮火中,本就艰难维生的那部分人不得不面临更加恶劣的生存环境。还需要注意“旷野”此时被“风”纠缠着,“而现在西方和东方一样,南方和北方也都一样,混混溶溶的,黄的色素遮迷过眼睛所能看到的旷野,除非有山或者有海会把这大风遮住,不然它就永远要没有止境地刮过去似的”[8]。旷野在风的席卷下变得模糊不清,旷野上的一切要素都被风沙遮蔽。这一自然环境描写旨在表现“旷野”代表的无常命运在威胁人类生存的同时也是备受威胁的,说明萧红已经将对个体的关怀扩大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进而在写作中做到了对全民族命运的整体性把握。“旷野”既指向作者对单个人的不幸之怜悯,也暗含着萧红对抗战前途的忧虑。从东京进入到战时中国,“旷野”包含的范围从个人孤立无援处境增扩至更宏大的战时困境,此时的“旷野”不只是追问生命价值,揭示人生悲苦时的背景,还是萧红借以思考民族国家问题的核心意象,囊括着对个人、世界、侵略、抗争、死亡等诸多问题的考量。
前面提及萧红的战争感觉本就源于日常生发出的敏锐感受。伴随着战事推进,萧红不断深化对战争的理解,并自觉将充满生活细节的个人感受纳入《旷野的呼喊》写作中。儿时记忆、留日经验、战时体验均被调动起来组成“旷野”意象,成为衔接虚构文本与历史现实的中间环节。萧红用“旷野”书写陈公公、陈姑妈的恐惧与愚昧、贫穷与孤苦,书写抗争者家破人亡的凄凉命运,同时也思考着个体生命在战争环境下如何保存的问题。在调用凝聚着个人经验的“旷野”的基础上,作者对战争进行了抹去个体生命价值的批判,这一批判伴随着全民族在战争大环境下应当何为的理性思考。“旷野”意象实现了从“展示底层人与悲惨命运的较量”到“思考个人与世界关系”再到“承接抗战时期民族国家情感”的功能迭代。
“旷野”的更迭变换有迹可循。1938年1月,在《七月》社“抗战以后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座谈会中,萧红回应作家在书写战时生活的困境时指出“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躲警报,这也就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9]。萧红认为不必亲自去往前线,只要生活在战争的大环境中,作家就拥有抗战文学的素材,把握抗战文艺的关键不在于紧贴战事,而在于抓住战时生活本身,并由此指出抗战文艺存在“抓不住”战时生活的问题。那么作家应该如何抓住战时素材?同年4月“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中萧红的一段发言可视作对此问题的解答:“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那么为什么在抗战之前写了很多文章的人现在不写呢?我的理解是: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悉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但这多少是需要一点事件才能够把握住的。”[10]萧红认为抗战文学发挥动员功能的前提在于写作的素材需要和作家的情感熟悉起来,写作的内容不能是抽象的,而须是具体事件。也就是说,作家对自己要表现的内容应当具备熟悉的情感体验与具体的个人经验。
《旷野的呼喊》正是在这一文艺观点下进行的写作尝试。在进入民族国家叙事时,萧红混入自身的历史经验,在行文中调用熟悉的“北中国”背景、“铁路”记忆以及“旷野”意象。小说整合了作者的个人经验与战争感觉,既有对于底层人民生活与精神困境的熟悉;亦有对战争时代中的日常生活被打乱的观察;还注入了作家漂泊流浪无所依靠时的生命思索。这种贴近作家实际经历的写作使得陈公公在旷野上的呼喊具有可被阐释的多重面向,萧红的战争文学展示出触及灵魂的力量。
三、“胜利之问”与“从灵魂出发”的写作
1938年年初,萧红与《七月》的一众同伴响应建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的号召去往临汾,以此次北上经历为素材写成的散文《无题》中,萧红记录下自己在同行人们讴歌北方风沙时产生的困惑。萧红不解于“他们”对野蛮风沙的盲目赞美,并发现“他们”无视具体的四季物候和侵略现实,指出有关北方风沙的感慨实际源自生疏引起的恐惧[11]。困惑与萧红认为文学表现内容须与作家情感经历足够熟悉的文艺主张相关。萧红期望在宏大战争里纳入偏僻人生和日常细节。尽管《旷野的呼喊》存在个体与国家双重关怀,但作者对两者的理解有着层级关系,正是对个体的敏锐感受使得作者具备了把握民族国家命运的能力。所以萧红无法附和将具体经验屏蔽的讴歌,并指出不足够贴近表现对象的艺术倾向会导致作家无法分辨“力”与“野蛮”,进而在写作时误将残忍的风沙指认为“伟大”。“他们”指一同北上的《七月》同人,双方的分歧说明充满细腻生活感觉的战时文学观念难以被整合进抽象的抗战热情和主流的文学表达。
带着此种理解就能发现,《旷野的呼喊》开头冗长的风物描写有着萧红与《七月》作家群的对话意图。形容庭院破败时冷静的叙述语调显然不来自陈公公一家,而独属于以展示风沙对日常生活的具体摧残来回应盲目“讴歌”的萧红。葛浩文认为《旷野的呼喊》是同名小说集中最差的一篇,他指出萧红常有妙笔的景物描写与杂感笔法在这篇小说中成了“硬填、凑篇幅、拖泥带水式的长篇大论”,这般足以称作严厉批评的判断正指向小说开篇的铺陈[12]。从阅读者立场看来,在主人公出场前大量的环境描写确实引不起读者的兴趣。但如果将这段文字归入萧红战争文学写作的脉络就能发现,堪称琐碎的风沙临摹传递出作者与《七月》作者群在文学观念层面存在分歧的信息,进而具有与文艺主流偏离的对话价值。
风沙描写背后的对话意识于《旷野的呼喊》集收录的其他文本中也存在着。《黄河》结尾,面对阎胡子“是不是中国这回打胜仗,老百姓就得日子过啦?”的困惑,萧红安排士兵给出必胜的答案,可随后又着意刻画的阎胡子被河滩沙粒淹没的双脚,暗示严峻自然环境并不受胜利预期的影响,将长久地威胁着人的生存[13]。《朦胧的期待》中写李妈得知心上人去前方打仗后的一系列心理活动,担忧又不知所措的李妈只有在进入“胜利”的梦中才能暂时获得精神放松,而“梦”的形式又隐喻着“胜利”的飘忽不定。借小说人物之口,萧红集中表达自己对“胜利”叙事的质疑。早在东京求学时,萧红写给萧军的信就提到过“人尽靠着远的和大的来生活是不行的,虽然生活是为着将来而不是为着现在”[14]。彼时萧红已经发现了“远”和“大”的“将来”与“现在”人之间的矛盾。战时环境下这一矛盾具体为“胜利”与真实生活的冲突。阎胡子和李妈的“胜利之问”正脱胎于此种冲突带给萧红的危机感:洞悉人间悲苦的萧红明白战争不是导致小人物痛苦的唯一原因,战争的胜利也不会完完全全地化解他们人生的苦楚。可现实是,当抽象的胜利口号无可避免地进入了具体生活,萧红发现周边存在着没能被叙事主流覆盖的角落,大环境对抗战热情强烈的认同将使这些角落中弱小生命在盲目歌颂野蛮的洪流中彻底迷失。接受新知识的知识分子何南生尚且会发出“抗战胜利之后什么不都有了吗!”的麻木感叹,更何况阎胡子、李妈这般普通人[15]。
“胜利”叙事与战争热情到底能多大程度上解决于人的具体困境?此种质疑进入到萧红的战时书写,推动着她偏离《七月》社文学中心。《无题》中的风沙引起萧红对于视“力”之强弱为评价好坏的文艺标准的思索,并由此展开对屠格涅夫的辩护。端木蕻良在刊登于1937年12月《七月》杂志上的《文学的宽度、广度和深度》中对屠格涅夫作出“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面可以找到类似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那样整部的形式和内容来,可是你在屠氏的散文诗里绝对找不到《战争与和平》的整部的形式和内容来”的论断,端木蕻良以此表达自己对精深宏大的文学主旨的追求,这一观点也代表着《七月》作家群以及抗战文艺整体较主流的看法[16]。《无题》中,常被指出创作“没有中心”的萧红以无不惋惜的口吻回忆起自己被上述观念裹挟时感到的失落时刻,进而指出对文学表现“力”的过分追求会带来远离作家灵魂的偏至,一味地鼓吹将使抗战文学与现实隔膜而无法发出贴近人群的声音,成为孤独的写作[17]。意识到萧红与战时历史环境和抗战文坛中心的紧张关系,就能穿透“胜利之问”,看见萧红面对逐渐空洞化的抗战文艺话语时,努力避免自己被卷入其中的焦虑。
在《旷野的呼喊》这一文学实践下,萧红的焦虑被战时个人化的经验写作化解,“胜利之问”从萧红的写作中退场,弱势群体在命运旷野上的呼喊声代替了抽象口号。《莲花池》中萧红不掩藏对为生存而不得已投靠日本人的祖孙二人的同情;《山下》作为叙述主体的林姑娘的悲剧也并非由战争直接导致。确立个人化写作立场之后,萧红从自己熟悉的儿童视野和独特体验出发,关注小人物的生活日常和无法把握的命运,尽管这些故事也放置在战争背景里,但人们在阅读时获得的大多是对于普遍且永久的亲情、人性与生命的感悟。
从抗战文学整体来看,《旷野的呼喊》集将偏僻人生的战时体验带进了抗战文艺视野;从萧红个人创作道路来看,小说集中收录的文章展示出作者写作时从焦虑走向沉静和谐的过程。接下来的两年间,萧红将在这种和谐状态下创作出《呼兰河传》《马伯乐》等动人作品,进入文学的又一高峰期。
四、结语
通过对萧红战争感觉与战争书写的梳理可以看到,震颤心灵的动荡促使萧红理解战争时纳入个人经验,并在对战争与抗战文艺的反复辨认中渐渐偏离主流抗战文艺话语,将炮火之下边缘人生的进一步失落作为文学表现的主要目标。萧红在写作时调动凝聚个人颠簸流浪体验的“旷野”,以此意象表现战时生活细节和穷苦群体的精神世界,将《旷野的呼喊》作为小说集名或许也隐含着作者的上述文学主张。
《旷野的呼喊》于1940年3月作为郑伯奇主编的《每月文库》丛书之一出版。郑伯奇在总序言中感叹自己未能上前线,希望收集的这些抗战初期优秀作品能起到承担精神动员的责任的作用。略带遗憾的表述透露出《每月文库》在出版过程中对战争以前线为中心,后方为补充的差序理解。在出版环节,看到了个体遮蔽困境并致力通过个人化写作摆脱困境的萧红再一次面临着被裹挟的命运。裹挟的再现,也更说明了萧红文艺观点与战争书写的独特价值。
参考文献
[1] 萧红.一条铁路的诞生[J].七月,1937(4).
[2] 萧红.一九二九年底愚昧[J].七月,1937(5).
[3] 萧红著 林贤治编著.萧红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4] 萧红著 林贤治编著.萧红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5] 萧红著 林贤治编著.萧红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6] 萧红著 林贤治编著.萧红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7] 萧红著 萧军编著.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8] 萧红著 林贤治编著.萧红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9] 抗战以后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座谈会纪录[J].七月,1938(7).
[10] 现时文艺活动与——座谈会记录[J].七月,1938(15).
[11] 萧红著 林贤治编著.萧红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12] 葛浩文.萧红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3] 萧红著 林贤治编著.萧红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14] 萧红著 萧军编著.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5] 萧红著 林贤治编著.萧红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16] 端木蕻良:《文学的宽度、广度和深度》《七月》,1937年12月第五期.
[17] 萧红著 林贤治编著.萧红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特约编辑 杨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