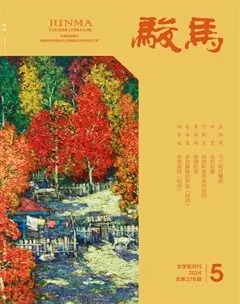鼓浪屿是用来怀旧的
有没有一个地方,冥冥之中和你有缘,每当听到它的名字,心中便是一颤,充满了自以为是的牵挂,仿佛和它前世有约。
鼓浪屿与我,便是这样一份感情。
——题记
林语堂的“婚房”
一
樟树街44号,是当地富贾廖家老宅,1919年,林语堂先生就是在这里娶了廖家的二小姐廖翠凤。
第一次去那里,我在樟树街38至50号之间来来回回寻找,并没有44号。一位当地人见我找得辛苦,问清了缘由,往胡同里一指说,前面那个大铁门就是。原来廖家隐藏在半截胡同的最里面。胡同安静干净,虽邻闹市却仿佛过滤掉了车水马龙的喧嚣。大铁门上虚挂着一把铁锁,我从门缝间大声呼道:“有人吗?我能进去吗?”里面传来一个女人懒洋洋的声音:“谁拦着你啦?”
我小心翼翼地把锁拿下来,轻轻推开门。啊,好深的院子,眼前的院子几棵老树虬干苍劲,枝叶参天,似有百十来岁的树龄。左侧是一堵红墙。右侧则是一栋老旧的两层英式建筑风格的别墅。别墅像一位垂暮的老人,幽幽地散发着一股腐朽的气息,外墙皮的很多地方都剥落了,不过这座别墅的造型别致,拱券回廊,两层坡顶,空间宽阔优美,使得整座别墅看起来古朴典雅,能想象出当年的富丽堂皇。
院落尽头,有一幢破旧的二层房舍,显然是后来建的,房子前面晾着几件衣物。一个衣着随意的中年女人拿着盆,正在头也不抬地捡着贝壳。
我注意到这栋英式别墅被一根绳子拦着,赫然写着“危楼”,问那个女人:“能进去看看吗?”她冷冷地回一句,“你不认字啊?”便不再言语了。
零零散散进来几个游客,一会儿院落里又静了下来,那个女人还在心无旁骛地干着活。我悄悄地从绳子底下“钻”了进去,回头看,那个女人似乎是装作没看见,或许根本没在意我。上了台阶,一股久置的尘埃味道迎面袭来。哦,该是多年没有人居住了。
没有门板和窗玻璃的房间几乎都是相通的,房间的地面有水泥的,有木板的,也有瓷砖铺成的,显然是出自不同年份的装修,不过依然可以看出厨房、卧室、卫生间、书房的模样。高大的廊柱残留着往日的尊贵,走廊的墙壁好多砖块缺失,斑驳的墙面露出岁月的痕迹,有的房间的墙壁出现了裂痕,为了防止倒塌,用粗粗的木头横竖支撑着。在一个房间里我发现了废弃的壁炉,炉膛里塞满了破碎的砖头,岁月的沧桑,人世的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宽敞的走廊沐浴着懒洋洋的阳光,让人感到了些许的暖意。在老先生结婚的洞房里,正好阳光照了进来,让屋子里多了一层明亮。
这座老宅见证了林语堂一生最重要的时刻。林语堂先生在这栋楼里待了三天,认定廖小姐是他可以托付一生的妻子。廖小姐出身富贵人家,一辈子跟着林语堂先生颠沛流离,没有丝毫怨言,上了厅堂,下了厨房,并为他生下三个漂亮的女儿,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称心。
而今人去楼空,廖家老宅却因为林语堂而知名。
关于这座老宅的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卖给“七匹狼”当家的了,将来要改造成酒店。还有人说要建林语堂纪念馆。不管怎么说,希望不要拆了它。
走了出来,铁门在我的背后又轻轻虚掩上。恋恋不舍地回望,一簇簇挂在墙头的凄美的曼陀罗炫了双目,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心想,若是再来,只寻“曼陀罗”便是。
二
又有了机会去鼓浪屿,第一个想拜访的就是廖家别墅。
顶着炎炎的烈日,汗流浃背地找到樟树街44号,却发现先前那些曼陀罗没了踪影,只有光秃秃的墙。大铁门实实在在地锁上了,显然谢绝参观。有些零散的游客站在门外观望,我正暗自庆幸多亏上次得以进去,就听身后有人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钟南山先生的外婆家。”咦,我心中疑惑,不由地转过身,DzzFhpoJTcm6j3yAaiRkcg==见一导游模样的年轻小伙子,手里举着小红旗,正汗淋淋地和他的客人们介绍呢,“钟南山先生从小就在这里玩耍,他的妈妈就出生在这里……”我第一次听说这栋老宅和钟南山先生有关。
回到宾馆赶紧查资料。原来还真是如此。
钟南山的外公是林语堂妻子的表弟,也是林语堂的同学,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嫁给了著名的儿科专家,教育家,病毒学专家钟世藩,算起来,林语堂先生还是钟南山的堂姑祖父。
现如今“钟南山”三个字如雷贯耳。再来寻廖家别墅,或许打听钟南山的外婆家更好找一些。
三
回到家后,我好奇地百度了一下廖家的家谱,竟然又发现了一个名人——殷承宗。这位著名钢琴家的妈妈廖翠娥也是廖家人,林语堂是他的表姨父,他是钟南山的表舅。
说起来殷家在鼓浪屿也是名门。殷承宗的父亲是新加坡华侨,曾组建“厦门劝业银行”。殷家所在的鸡山路16号建筑已成为鼓浪屿重点历史风貌建筑。
再查,从廖家老宅走出来的还有医学家廖月琴(钟南山的母亲,广东肿瘤医院的创始人之一),厦门医学界的翘楚廖永廉(钟南山的舅舅),著名肺科专家戴天佑(钟南山的姨父),声乐家林俊卿(钟南山的表舅),骨科生物力学专家、工程院院士戴尅戎(钟南山的表哥)等等。
不怪有人说,廖家是“神仙家族”,亲友团强大,人才辈出。
音乐世家的骄子——殷承宗
在鼓浪屿繁华的商业街上,你会发现地上有着歪歪扭扭的音符“?”,好信儿地跟着走,到了音符的尽头,抬头,“鼓浪屿音乐厅”出现在眼前。
这可是鼓浪屿最热闹的地方,几乎每天晚上都上演着各种名目的音乐会、演唱会。
据说20世纪的鼓浪屿几乎家家都有钢琴,随便你站在哪家的门口,一准儿会听到音乐,就在这曼妙的乐曲声中,走出了无数位知名的钢琴家,殷承宗便是其一。
我曾见过殷先生一面。那是2014年10月24日,我在哈尔滨音乐厅聆听了老先生演奏的《黄河》协奏曲和由他改编的《春江花月夜》。
这张小小的音乐会入场券记录了我对老人家的敬仰和尊重,我保留至今。那年殷先生73岁,是我当时唯一接触过的鼓浪屿的名人。
来到鼓浪屿,当然期待看看先生出生成长的地方了。当地人说殷宅在鸡山路16号,现在住在里面的是他的哥哥,殷承宗每年只在夏日里回来一趟。一位当地的女子把我带到一条小路上,指着前面说,顺着小路走到头就是了。此时是正午,阳光温暖,小路尽头有个缓台,两个年轻女子在阳伞下安静地喝着咖啡,我找了个阴凉的石阶席地而坐。
这是一座法式的乡间别墅,在鼓浪屿上千别墅中也堪称上品,别墅是由留美的殷承宗大哥殷祖泽设计的,称为“殷宅”或者“圃庵”。1941年,殷承宗就出生在这里。
老宅外表看起来有些颓败,院子里的花草凌乱地长着,摇曳的树枝伴着海风,似在呼唤。花岩墙上镶嵌着欧式的窗棂,于陈旧中透着高贵。
殷家不似廖家,廖家是医学世家,殷家是音乐世家。
殷家九个儿女,几乎都和音乐有缘。殷祖泽,就是别墅的设计者,不仅是建筑学家,还是颇有名气的男低音;殷祖澜,工科生,男高音歌手;殷承典,钢琴演奏家,厦门(鼓浪屿)音乐学校校长;殷彩恋,女高音歌唱家;殷秀茂,著名音乐教授;殷承基,钢琴演奏家兼男中音……
殷宅绝对是一座神奇的、浸没音乐旋律的别墅。据说,上世纪60年代殷承宗在苏联获得钢琴大赛的冠军后,苏联有一位著名的教授不远万里来到鼓浪屿考察。他住进了殷家别墅,感受到了殷家的音乐气氛以后,动情地说:“我现在明白了,殷承宗的演奏为什么总让人有强烈的画面感,那种如诗如梦的音乐之魂,来自这栋小楼,来自鼓浪屿。”
德高望重的生命天使林巧稚医生
林巧稚医生是我的老师们的偶像,当然,也是我的偶像。
记得在妇产科实习的时候,老师总是和我们讲述林医生精湛的技术和高尚的品德。林巧稚医生去世的时候我正念大三,早会上科主任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这是我国妇产界的巨大损失。
1901年12月23日,林巧稚出生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在这里,她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到了鼓浪屿,去拜访一下林家老宅也是我的初衷之一。
颇费了一番波折我才找到。网上说在晃岩街47号,但岛上的地图根本就没有标识,几经询问,终于在日光岩的对面看到了一个蓝底白字的牌子——晃岩街47号。
初见它,我惊呆了,这就是她出生的小八卦楼?眼前这座面朝大海的楼和廖家别墅建筑风格相像,同样墙皮剥落,门窗油漆老化脱落,几盆白色塑料盆里的花萎残成一团摆放在廊厅上。
我试探地走向它,突然楼里走出来一个穿着迷彩服的中年男人,对我一边摆手一边喊:“别往前走了。”我犹豫地问道:“这,不是林巧稚医生的故居吗?”那人带着嘲笑的口吻回道:“林巧稚怎么能生活在这么破的地方,你也不想想?”可是,我看着手机里的“百度”,分明是晃岩路47号!“百度”还说,诗人舒婷曾经建议在这里建“厦门文学院”呢。我迎着对方不太友好的目光,把疑问生生咽了下去,望着这不堪入目的危楼,我倒宁愿相信他的话。我远远地拍了几张照片。
林巧稚说:“我是鼓浪屿的孩子,我的童年和少女时代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鼓浪屿还是没有忘记她的,专门为她修了毓园。
通向毓园的是一条柏油路,很幽静,很雅致。一侧是墙,另一侧种着柏树和灌木,树木间穿插着石头做成的“书”页,每一页都用中英文镌刻着她曾说过的话和人生感悟。一路走一路慢慢品味,一个热爱和平mrDF3gBF8aKNF6/kOq4ZsNQCf4PXwMmzXoa/w1Z9MEU=、热爱生活、充满智慧、不畏苦难的医学工作者的形象跃然“纸”上。
毓园的入口处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雕像,像是在欢迎人们的到来,又像是守护着林巧稚医生的小精灵。
毓园两侧是花坛,种植着洁净的星菊,石阶两旁则是色彩缤纷的米兰、扶桑、大理、一串红等花卉。一块醒目的石头上刻着林巧稚的遗言:“我是鼓浪屿的女儿,我常常在梦中回到故乡的海边,那海面真辽阔,那海水真蓝、真美……”
林医生的雕像由汉白玉雕成,通体纯白,她梳着短发,显得精干利落。她微笑地目视远方,双手交叉地放在胸前,这双手承接过五万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她曾说:“我愿意做一辈子值班医生。”她做到了,她就是天使,守候在生命之门。
雕像下面埋着她的一半骨灰,另一半骨灰遵她的遗嘱,洒向了大海。
大爱者永生。
毓园里有林巧稚医生的纪念堂,里面很详细地介绍了她的生平,有许多珍贵的相片和她曾经用过的物品。望着这些,我心中有些宽慰,之前看到的那栋破旧楼房引起的不愉快渐渐消失。
那天,我在毓园坐了许久,心中想着陪陪孤独的她,又想着为什么叫“毓园”呢?“毓”有生养、养育的意思,甲骨文字象形母亲生育分娩的情形。用于名字时,有博爱、慈祥、无私、善良、大爱之义。我们的林巧稚医生太担当得起这些优秀的品质了。这个“毓”字用在这里很妙,很贴切。
写这篇文章时再查百度,无意中看到,钟南山母亲廖月琴的堂姐妹廖雪琴嫁给了林巧稚的侄儿林嘉泽,林巧稚竟然是钟南山的姑婆。
这世界真小,绕来绕去又绕到钟南山那儿了。
拼音之父——卢戆章
寻找“拼音小道”是个夏日的午后,气温高达42度,天似乎在下火。我顾不上汗水顺着脸往下淌,急切寻觅着,明天就要返程了,若是不去看看,定然心中遗憾。
这次带我们的导游竟然是教导游课的历史文化老师。“金牌”导游对鼓浪屿了如指掌,当听他介绍鼓浪屿有个“拼音小道”和“拼音之父”卢戆章时,我格外留意。之前我研究过鼓浪屿的名人,可是对卢戆章不了解。导游说,这个人可了不得,他的一生在汉字的进化中占了七个第一:第一个发明拼音字母,第一个发明标点符号,第一个提倡白话文,第一个提倡国语,第一个提倡简化行字,第一个提倡横排横字,第一个提倡拼音识字。听到导游如此介绍,我顿时怦然心动,立刻决定这次无论如何要去寻踪。如果说之前对那些名人故居的拜访充满了敬意,那么对“拼音之父”的拜访除了崇敬还有寻根之意。
记得我上小学的第一堂课,老师点着黑板上的字母领着我们读拼音:b、p、m、f……那是所有孩子学习汉字的起点。学会了拼音,就学会了查字典,学会了读生涩的书,比如充满繁体字的《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等,没有拼音就没有往后的阅读。我终于在这里知道了发明拼音的先辈,能不激动吗?还有,我现在在电脑上写文章,在微信聊天,使用的都是拼音法、横排横字形式、标准的标点符号等等,这些都拜他老人家所赐,感恩之心油然而生,这种心情之迫切远远超过对酷暑的畏惧。
我请导游发过来拼音小道和卢戆章雕像的位置。导游说了一句,大姐,从拼音小路到雕像,要经过一大片基督教徒的墓地,您最好别单独行动,特别是不要晚上一个人走啊。看到导游的话我乐了,想起有人说过,这个世界上可怕的不是死人是活人。况且,我还真想一个人去寻找,静静地和心中的大师“对接”,来一次“饮水思源”之旅。
按照导游发的“鼓声路10号”方向走。鼓声路在鸡山路尽头,我先去鸡山路16号殷承宗先生的老宅外面看看,一切如常。然后继续按照导航前行,导航在鼓声路和鸡山路交口犯“混”了,一会儿告诉我朝东行,一会儿又说走过了,朝西走,反反复复如此来回不已。此时四周寂静,没有一丝风,连个人影都没有,老天这是考验我的耐心呢?还是在嘲笑我的执着?就在我快绝望的时候,从旁边一条岔道上晃晃悠悠走上来一位戴着草帽,挑着扁担,打着赤脚的当地男人,我急忙向前询问,他一指身后,“喏,从这条路走下去,到头就是沙滩,那儿有座雕像。”说完,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继续前行。原来这条小道在鸡山路和鼓声路之间夹着,难怪导航反复纠正我的方向,可是,我望着眼前这条看不到尽头的小道有点儿茫然了,冲那男人背后喊道:“老哥,这条路多长?”“也就一里地,很短的。”男人头也没回。
总算找到方向了,小道绵延而下,我迈开脚步,开始留意足下花岗岩石上面的刻字,我走在这条小路上,和“拼音”在一起。
顺着石阶一点点往下走,路两侧种着榕树、梧桐树、椰子树和许多绿色的植被,有风吹来,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不一会儿,看到左侧花园里散落着大小不一的墓碑,这就是导游说的基督教徒的墓地吧。听说卢戆章的墓地也在那里,为了表示对先人的尊重,我路过时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又鞠了一躬(礼数还是要到的),默默地道,“安息吧,这一路谢谢你们的陪伴。”
不知不觉就到了尽头,眼前是一片沙滩,海浪拍打着岸边。有块很大的石头,上面刻着:拼音道是为纪念现代汉语拼音文字之父卢戆章,修筑的一条特色路。卢戆章(1854—1928年),汉语拼音文字首倡者,字雪樵,福建同安人,居鼓浪屿,清末学者,1892年自造民族字母的拼音文字方案《切音新客》,开中国拼音字母先河,是中国语文现代文化运动的先驱。
拼音小路是2004年为纪念卢戆章诞辰150周年修建的。想来也20年了,这条拼音小路和另外一条音符小路(通向音乐厅)成了鼓浪屿很有特色的两条道路,可惜离中心地带远了一些,知道这里的人不是很多,不过,在我观望石头的时候,身边不断有家长领着孩子从沙滩走上小路,边走边“唱”着拼音。
离石头不远处的沙滩上矗立着一尊卢戆章的半身雕像,这尊铜像高2.4米,雕像中的卢戆章老先生表情凝重,目光深邃,似乎还在琢磨“切音”的应用。
我恭恭敬敬地站在老先生面前,三鞠躬,为他的伟大发明创造,为他福泽后人之恩。
下次来,争取去老人家的坟墓祭拜。
他的故居在厦门同安,与鼓浪屿一海之隔。
鼓浪屿是个令人怀旧的地方,这里的名人很多,这里的故事很长……他(她)们是一个个时代的标志,陈列在岁月的风尘中,让我们对逝去的人与事物充满了怀想和怅惘,读他(她)的故事,动人、感人、暖人。
【作者简介】于秋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哈尔滨市作家协会散文专业委员会主任。曾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长城》《天津文学》《北方文学》《人民日报海外版》《作家文摘报》等多个报刊发表小说、散文等百余篇。著有散文集《远行物语》《城里的人们》。
责任编辑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