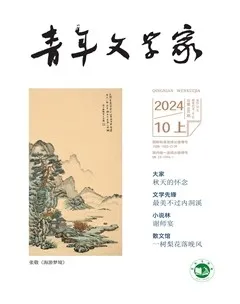一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秀珍微信发来一张照片,仔细一看,竟是我俩刚进银行学校时的合影。看着那青涩的脸庞和清澈的眼眸,一下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像回放的电影一样,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年前,回到我的母校—山东银行学校。
1983年9月,我踏进了位于济南市的山东银行学校。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爸爸和哥哥一起送我到学校。宿舍里都是上下两层的铁架子床,我在上铺,哥哥帮我铺被褥。爸爸环顾了一下四周,又用背包带围着栏杆绕了两圈,说睡觉的时候不要像在家里一样不管不顾,翻身要小心一点儿,不要摔着。我答应着。安顿好一切,他们又嘱咐我要和同宿舍的同学好好相处。我说知道了,催着他们快点走。可是,看到他们踏出宿舍的背影,不知不觉就流出了眼泪,心里彷徨又无助,一片茫然。宿舍的其他同学看见我掉了眼泪都围过来,结果七个女生都哭了,我们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互相劝慰着、鼓励着。刚刚相见还互相叫不上名字的七个女生一下亲近起来,就像久别重逢的姐妹。
开学不久,班委决定在国庆节前搞个文艺汇演,一来可以消除同学们之间的陌生感,更重要的是能够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把班里的气氛活跃起来。
同宿舍的七个姐妹决定以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为背景音乐,编排一段简单的舞蹈。不过,只有活泼洋气的秀珍有点儿经验,于是就让她在中间带我们跳并进行指导。我是最怯场的那个,不是走错位置,就是手脚跟不上。秀珍一遍遍耐心地教我、鼓励我,说没事的,只是在自己班里自娱自乐,不要紧张。没想到演出那天我更紧张了,脑子一片空白,转圈的时候我踩了秀珍的脚,她没站稳趔趄了一下,同学们边哈哈大笑边对着秀珍指指点点,我更慌乱了,也不知怎么下的台。这可惹恼了秀珍,她走到我面前立着眉毛低吼:“你是不是故意让我出丑?”我连声道着歉:“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太紧张了。”她对我使劲“哼”了一声就走开了。
演出结束后,我到处找秀珍也没找着,回到宿舍她也不在。我很不安,一直盯着屋门。等她回来的时候,马上就要熄灯了。我本想和她说话,她却一声不吭,端着脸盆去盥洗室了,回来的时候正好熄灯铃响了,我在黑暗里对她说对不起,但没听到她的声音。
我辗转难眠,不知不觉泪水打湿了枕头。过了一会儿,她轻敲了一下床板,我抬头一看,她已经打开了门,示意我出去。我悄悄地下了床,跟在她的后面。我俩轻手轻脚地走着,到了卫生间门口,她走了进去,我也跟了进去。她站在那儿没有说话,我看了她一眼,低着头小声说对不起,眼泪又不争气地掉了下来。她走近我,往我嘴里塞了什么东西,我一愣,发觉是我爱吃的胶东地瓜干。这才听她压着声音说:“你是林妹妹吗?怎么这么多眼泪?”说着,又伸手抹了一把我脸上的泪水,我知道她原谅我了,就破涕为笑,刚想说什么,她却把两根手指放在嘴上做了一个不许说话的手势,然后自己也往嘴巴里塞了一块地瓜干,我俩互望着,做着鬼脸嚼起地瓜干来。
过了一会儿,她悄声说:“今天我们一起睡吧。”我说:“好。”我俩悄悄地又溜了回去。
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她们五个都站在床边看着我俩。见到我们醒了,玉儿大声问:“快点儿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嗯?”我连忙说:“没什么呀。”“没什么?”玉儿瞪着眼睛看着我又问:“没什么,怎么睡到一张床上了?”其他姐妹也七嘴八舌地说道:“是啊,快点儿交代。”她们随声附和着,一边说一边掀开我们的被子,挠我俩的痒痒。顿时,七个女生在一张小床上扭作一团,笑作一团。
从那天起,我和秀珍就一起去教室,一起去餐厅,一起回宿舍,形影不离。又到周末了,我对她说,我们去大观园吧,就我俩。她说,好啊。就这样,我俩没同其他姐妹打招呼便悄悄溜了出去。到了大观园,我们把每个店铺都逛了一遍,我还请她吃了狗不理包子。路过中国照相馆,我们进去拍了张合影,也就是她微信发来的那张。
一切恍如昨日,却已是四十年光阴阻隔。如今,我们均已退休,相约再见面时,再拍一张合影存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