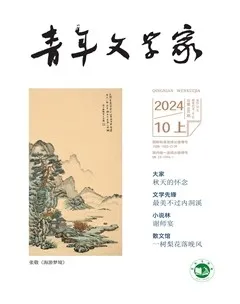原乡

上午我正在看自己绣好的十字绣,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一个陌生号码,不知来历,我看了又看,最终凭借直觉按了接听键。原来是北京的一个姐姐,好多年没有她的消息了。
2003年,我因一段情谊,冒着危险也要去见那个人。然而,怕横生枝节,且一向追求完美主义的我,还没有见到他的面,冲动已慢慢退却。多年后,那样的喜欢质变成了一种经久笃厚的友谊,在生活以外,在山水之间,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以另一种形式存在,高远疏散,天地寥廓。尽管我很轻易地找到了一份出版公司的工作,但得来容易,亦并不在心。
就在我一个人似舍犹眷、漫无目的地逡巡于沙尘漠漠的京城之时,姐姐的出现,似被隔绝很久的亲情从那街道的斑驳枝杈间席卷而来,我多日的固执在她古铜色的笑容里瞬间融化。马家堡的亲切,夏家胡同的逼仄,上地的熙熙攘攘,西单的繁华……107电车在连接了一个城市的南北秩序之后疾然而去,姐姐的一通电话让我和我当年的梦想再次浮现于脑海,那年,北海的静谧、天坛的庄严,在或寂寞,或冷漠的人群中来回游荡。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姐姐比我大十四岁,而姐姐一家五口是在老家的乡下居住的。那里有浅浅的河滩,硌着脚板的石子,傍晚时分有淡淡的炊烟,交织着田园里的草木清香,纯朴而自然地留驻在我的记忆深处。夜晚的天幕上,一万零一颗星星和一千零一个故事在和我满脑子的童年幻想对视对语,还有被蚊虫、虱子叮咬的红肿奇痒久不消退。我告诉她,我想回家了。姐姐说,先到她那里去待几日。她让姐夫把我的行李搬去,在她租住的房子里,我无比安然地度过了一个冰天雪地的寒冬。姐姐是那种很坚强的女人,自己有难处的时候绝不找人诉苦,解决完了才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整个冬天最寒冷的时候,我和姐姐一家围坐在姐夫自己制作的羊肉串铁板烧旁自己动手烤制羊肉串,那个场景,遥远而明媚,温暖而动人。
回来之后,我和姐姐几乎没有联系,倒是偶然接到姐夫的电话,说她在京被车撞到了,腿部受伤,不过疗养了一段时间,没什么问题了。我询问到赔偿的问题,姐夫说已经尽力了,语气里是那种不愿麻烦别人的善意。我亦无语,亲情的联络和补缺都需要机会,而简单的一个电话也不足以道明心底积淀的真情。前些时日,和姨家表姐通电话问她知不知道姐姐的电话,表姐告诉我,姐姐昨天还在她这里问起我,并询问我的电话。我很意外,也很开心,这世间终有一种思念是相通的。她从北京回来了吗?原来是她想家,想回来看看,顺便重新盖房子。
姐姐就在电话里,一通又一通地和我絮叨着,我的手机发热,两只耳朵发热。她竟然说她早两年因为一个手术从北京回来,在南阳的南石医院住过两个月,而她为了不让我们全家担心,竟然守口如瓶。她笑着说,她那时化疗了,一家人都瞒着她,现在她从鬼门关闯过来了,她比那时还好,过两天就来南阳见我。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掉泪了,昔日的岁月一点一滴浮现在眼前,这个叫“姐姐”的女人,她以她全部的好,收容了那时离家一千多公里的我的孤单和荒凉……多年之后,我沉淀着行走途中的种种况味和沧桑,不让坎坷打倒自己,不让脆弱蚕食自己。
而伪饰的社会里,这是多么轻飘的矫情。她自己真正历经生命的磨难时,离我只是咫尺,却一声不吭地掩藏。或远或近,我只能被动地接受她这样近乎残忍的方式,只有在我的想念里,能经常看到她纯朴的面容和爽朗的笑颜。在突然接通的世界里,听到她质朴、坚强的声音,感受永远美丽而亲切的原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