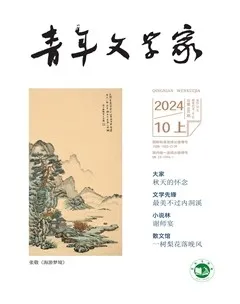离别
2002年7月13日,那一天像一条黄金分割线将桑晓菊的前半生清晰地划开。后来,只要桑晓菊一开始回想人生,首先袭来的肯定是那个下午。
微风吹在脸上,天气意外的凉爽。有那么一刻,桑晓菊觉得秋天已经来了。她背着一个牛仔蓝的大包,里面是从家里搬过来的这一年上学要用的书,沉甸甸的,压得她瘦小的身体好像随时可以收缩起来。右手拉着一个泥巴色的行李箱,褶皱里的凹槽处积满了灰尘,边缘处脱了皮,大概是多次使用的缘故—这是父亲留在家里的,曾随他跑遍大小城市去务工。
空气里有一丝适合告别的秋意。不过,要离开的不是桑晓菊,而是对面的曾琴和桑晓竹,他们分别是桑晓菊的母亲和弟弟。他们倒是一身轻松,曾琴一手拉着四岁的桑晓竹,一手提了一个小包。桑晓菊嗅得出曾琴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渴望,一种希望赶快离开的兴奋气息。
“你要听舅舅他们的话,表现勤快点儿,多帮忙做事。”曾琴说,“我会给你打电话。”
桑晓菊不知道母亲八年前是不是也这么兴奋,那时自己才六岁,被留在大伯家。大伯好像带着她和堂姐上山挖菜去了,这看起来像是故意安排的,她没有亲眼看到母亲离开。但是此刻,她也只是低头“哦”了一声来回应离心似箭的母亲。一旁的舅妈不合时宜地对曾琴说:“你放心,娃儿我给你带着,少不了一块肉。”然后转过头对着桑晓菊说,“好了,快跟你妈保证你会听话,等会儿她们赶不上车了。”
桑晓菊的心里还置着气。就在昨晚,她生命里的第一次例假来了。虽然知道女孩的生命里总会有这么一件事,但是当它真正到来时,还是有点儿措手不及。内裤上黑中带红的一块颜色,又不完全是血,甚至有点儿硬。她跑去告诉曾琴,渴望得到帮助和安慰。曾琴却马上撇着嘴角,撇得不能再撇,皱着眉,一脸嫌弃。曾琴说:“倒霉死了,脏死了,你自己拿卫生纸先处理一下。”桑晓菊像个犯了极大罪恶后深深忏悔的人,背负着羞耻,一时不知道该做什么,愣在那里。曾琴进去堂屋,出来的时候嘴里骂骂咧咧的,手里拿着一片卫生巾扔给桑晓菊。
“拿去,赶紧处理干净。”曾琴嘴里不停地骂道,“倒霉死了,脏死了!”桑晓菊好像看到了母亲在和奶奶或村里的妇女吵架时爆发出来的那种愤怒和嫌弃。
“倒霉死了,脏死了!”这是桑晓菊来例假第一天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从那天起,在她的整个生命岁月里,都觉得一月一次的生命经历是脏的,是极其倒霉的一件事。
为了生二孩,曾琴已经在家逗留了五年的时光。丈夫桑川在她生产后赶回家,据说为了接报喜生儿子的电话,桑川心急得摔了一跤,摔破了膝盖。当确认生了一个儿子时,桑川在电话那端大哭了一场。然后,桑川赶紧定了时间最近的火车票赶回老家,那是一趟最贵的火车。桑川在家足足待了半年才恋恋不舍地赶回了务工的城市。在曾琴心里,这比生桑晓菊强很多,那时他连月子期都不在家。留下刚生产的她独自面对一贫如洗的家和婆婆的刁难,以及产后波动的情绪。曾琴不知道生完桑晓菊后的暴躁、哭泣、压抑、忽喜忽悲,就是产后抑郁。但是,天生的要强和匮乏的物质条件足以打败一切抑郁,所有的情绪在她为缺衣少食和想办法对抗公婆的日子中被一点点分解。情绪爆发的一个个暗夜像不为人知的过去,无法启齿。然而,坏情绪并不是被她独自消化的,被她忽视的,还有她不经意间或习以为常吼叫的襁褓里的桑晓菊。这种习以为常的吼叫和谩骂延续到了以后她和女儿的每一次见面里。这个小人儿就像著名实验里天天被骂而枯萎的花,消极、悲观早已深种,为多年以后的人生埋下祸根。但是,曾琴直到多年后悲剧发生,甚至至死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师傅脚踩一下油门,摩托车发出一阵轰鸣,灰烟弥漫在空气里,摩托车带走了桑晓菊的夏天和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