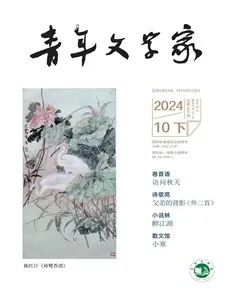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当代意识

马伯庸的小说创作巧妙地融合了历史真实性和艺术主观性,虽然是对历史故事的叙述,但其在创作中对于作品结构的把握更具有主动权,规避了在宏大历史背景下流水账式的史料铺陈。小说通过截取历史片段的表达方式,使整体内容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透视感,将史料文化从表象、内涵、结构三个层面进行拆解与重构,并与形象的故事叙述、生动的人物塑造以及细腻的历史场景刻画相结合,进行艺术的再次创作。他将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的关注与历史上那些不留名的小人物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变化结合起来,在历史小说的范畴之下融入了当代现实人生观照,由此实现文化历史小说多元的深层审美表达。
《长安的荔枝》作为新时代的历史小说,其主题思想中透露的大国思想与中国气派无意间与笔下的历史时代相呼应。马伯庸正是用现代的手法、当代的意识,在今时今日讲述历史,用天马行空的幻想和扎实的历史基础构造历史时空里的故事。它选取独特的视角,从小人物的视角来看历史,更能够引起当代读者的共鸣与认同,尤其是透过小人物与大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折射出大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与命运变迁。马伯庸的历史小说在历史背景之下,拓展出了一个同时具备现代感与古典美双重结构性张力的空间,呼应了时代主题,挖掘了深埋在历史土壤中的精神本源。目前,已经公开发表的关于马伯庸历史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历史重构与守正创新并存的审美价值进行探讨,以及对人物形象的分析等方面,并没有对其创作中融入的当代意识进行系统研究与说明,具有明显的单一性。本文通过文献分析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对马伯庸的小说进行论析,并从他的创作模式和叙事手法入手,通过研究马伯庸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对比与融合,对跨界创作模式的探索与开拓,对历史事实的考据与重现来阐述他作品的文化影响和文学价值,探究其在现当代文学中对于现代化进程的贡献以及在当代现实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而探讨熔铸于其作品中的时代精神。
一、真实与艺术并臻的内容组织
(一)视觉切入的史实性与主观性融合
马伯庸用自己独特的思想主题切入点展开这种小写的历史叙述,将历史的事实与文学的幻想结合起来,打破了人们惯性思维中小人物生活的琐碎平淡与乏味,努力寻找史实背景中古人与今人相同的精神联结,将人们在历史滚滚车轮碾过时的渺小无力与奋起支撑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实现了读者与主人公情感的广泛共鸣。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历史小说不再执着于书写大人物的历史,而是将历史看作每个个体经历的多元、复杂的过去,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新历史主义的许多书写以对历史中个人命运的叙述代替纯粹的阶级斗争的叙述,作家们不再仅仅局限于从所谓的历史进步和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来叙述历史,他们开始摒弃传统线性叙事中过分强调的唯物史观,转而追求更为主观化的叙事方式,从历史参与者的精神层面、人性深度以及复杂心理等难以量化的角度深入探索历史的丰富内涵。这种小写的历史,背后隐含的一种价值立场是“写作立场的人性化”。正如马伯庸的历史书写中不存在“刀枪”,也不存在“兵戎相见”。这样的融入让他的历史小说有了独特的风格。马伯庸于历史长河中舍弃了对历史的宏阔叙述,把目光投向了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从而使其小说在“真实”和“虚构”两个层面上实现了“弹性”的“游移”。在马伯庸的历史写作中,经常能看到一些小人物的窘迫和无助,他对这些小人物的关心,实质上也是一种对现实世界中平民百姓生存困境的反思。从《长安的荔枝》中我们可以看到,马伯庸很久以前就已经看到了人类的宿命在时代的大潮中变幻不定的无常。然而,在明白了宿命的残酷和变幻之后,他仍以一颗平静的心去直面它,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去记录这段历史。
(二)典型人物塑造的群体共鸣
《长安的荔枝》之所以能够蝉联豆瓣、微信读书榜首,并且在各大APP上被读者们狂热推荐的主要原因,便是这部小说在“人的回归”基础之上实现了小人物与“小人物”的共鸣。有时读者并不需要探究小说的情节和文笔如何,只要小说中的主人公能够与读者产生精神上的共鸣,这往往就成为读者喜欢这部小说的理由。《长安的荔枝》中几乎无处不映射着现实。主人公李善德在首都买房,还房贷,甚至一买完就得赶紧赶回去上班,因为只请了半天假;还有后面李善德列表格、各部门“踢皮球”、给资方讲演示文稿以获得投资,皆是当今人们职场生活的写实,他的故事引发了无数“小人物”与这位小人物的共鸣。
另一方面,从职场上升到社会层面来看。在小说中,主人公因贵妃随口一句想吃荔枝引发的风波而陷入了殚精竭虑的苦恼中。然而,在跟随主人公紧锣密鼓筹备的同时,读者也能够充分感受书中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在主人公一次次实验时,纵使读者对数字不太敏感,但这一笔一笔的收支摆在眼前,的确让人为之一惊。上位者们毫不在意要将荔枝送到贵妃面前需要多少人为此殚精竭虑,需要多少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与损失,他们也不懂得种树人用无数心血栽培起来的荔枝树被砍掉时心中的悲痛与无奈。他们不在乎这一切,他们只知道从百姓身上可以榨取的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马伯庸用轻描淡写的笔触讲述故事,“苛政猛于虎”的残酷史实极尽勾勒在读者面前,引发“小人物”的唏嘘慨叹与共鸣。
二、非历史化叙述的结构搭建
书写“历史文化真实”可以称作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多数历史小说家的自觉行动和普遍追求,反映了作家文化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主体精神的弘扬,从文学接受论角度来看是对受众群体需求的发现。读者在文本接受中更易于展开对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勾勒。此外,在历史空间中的特定文化表达里,受众往往会潜意识地进行自我映射的深层精神活动,从而追求文学作品在审美文化表达上与传统相悖的独特性。在这种受众需求下应运而生的是作家们为增加作品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将史料文化从表象、内涵、结构三个层面进行拆解重构,并与形象的故事叙述、生动的人物塑造以及细腻的历史场景刻画相结合,进行艺术的再次创作,由此实现文化历史小说多元的深层审美表达。
(一)视角的转移:历史背景中的配角
当代作家在进行历史叙事时,并不热衷于将他们的故事严格框定在实际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中。作家们只是简单地描述、创作和想象他们的人物在历史中的活动。尽管新历史主义者的小说也写人性,但其小说创作并不仅仅是以写人性为目的。而马伯庸通过视角的转移,展开了对历史中配角的描写,把注意力放在对历史中人性的分析上,叙述历史中人性的复杂性。人类本性的变化与历史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马伯庸不但展示了历史中的人性,同时也通过对小人物总体人性的描写和分析反映了历史的起伏。历史小说作为小说的一类重要主题,它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具有多种形式,或讲述权谋之争,或讲述战火纷飞,或讲述国家兴亡。而马伯庸创作的《长安的荔枝》则没有将重要的历史事件或史实当作写作中心,而是借助唐朝这个特殊历史背景来演绎具有历史永久性的职场故事。无论是宏大的时代背景,抑或广为人知的人物形象,都是围绕展现小人物生存困境的恒久主题发散。而正是因为《长安的荔枝》的视角的独特性,使得它在文本写作中被植入了一种特有标识,排除了历史设定的束缚后,这些小人物的“可能”反而更加多彩,这也为我们理解相关类型的历史小说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二)叙事的易变:时间与空间的灵活运动
马伯庸在对历史事实详细研究的基础之上,又在叙事方面做了一些灵活的变动。首先关于杨贵妃所吃的荔枝从何处而来这一问题,大致可以归类为三种说法:岭南、福建,以及四川涪州。关于这三者的辨析,很多学者甚至已经研究并发表了专业文章。根据作者调查所示,晚唐时候有一个叫袁郊的人,其所撰写的《甘泽谣》中讲了个故事:“天宝十四载六月一日,贵妃诞辰,驾幸骊山,命小部音声,奏乐长生殿。进新曲,未有名。会南海献荔枝,因名《荔枝香》。”(《长安的荔枝·文后说明》)在所有的唐代荔枝史料中,这是最具画面感的一条。由于小说所具有的灵活性和较大的自由发挥空间,作者便直接采用了这个说法,并且将“天宝十四载六月一日”这个设定也运用进小说当中去了。“关于岭南荔枝道的路线,我是用鲍防的《杂感》和清代吴应逵《岭南荔枝谱》里提供的路线为参考,综合卫星地图研判而成。至于文中所提及的诸多保鲜方式,皆取自从宋代到清代的各种记载,如瓮装蜡封、隔水隔冰、竹箨固藏、截枝入土、小株移植等。考虑到中国古代科技差异不大,唐朝纵无记载,也并非不可能实现。”(《长安的荔枝·文后说明》)在其他方面,诸如由于作者对骊山并不感兴趣,所以文中的设定是直接让贵妃在城里过生日。峒人边唱歌边摘荔枝这一设定源于林嗣环在《荔枝话》中提到的福建一带的风俗:“荔熟时,赁惯手登采,恐其恣啖,与之约曰:‘歌勿辍,辍则弗给值。’”(《长安的荔枝·文后说明》)其意便是,为了防止工人摘果时偷吃荔枝,雇主会要求他们一边唱歌一边采摘。作者便是直接将这一设定安插到了小说中的峒人身上,实现了时间与空间的灵活运动。
马伯庸的历史小说通常只选取历史中的某个事件或某个阶段,通过这种点状和短线状的截取,在方寸之间结合史料,发挥作者的想象力,重构一个细节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在这种叙事手段下,马伯庸对于小说的创作贯穿个人主观性,虽然是对于历史故事的叙述,但在创作中对于作品结构的把握更具有主动权,完全规避了在宏大历史背景下流水账式的史料铺陈,通过截取历史片段的表达方式,使整体内容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透视感,增强了叙事背景的深度。
三、当代现实观照对传统历史观念的重构
在传统的历史观念中,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不可更改的现实,史书记载的都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但是新历史主义诸家反对这种观点,依据他们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重要的是制作历史的年代,而不是历史发生的年代”,历史不再是纯粹客观的现实,而是可以以人的意志发生转移的一种文本,即历史可能因为历史写作者的立场而呈现不同风貌。传统历史小说中的历史是以国家发展为中心展开叙述的,普遍都带有着关于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属性。但历史并不仅仅是由“大人物”来书写创造的,建构历史的重要基层是往往被史传忽略的“小人物”。特别是在读者厌倦了帝王将相的普遍描述之后,他们开始渴望拓宽和提升自己的阅读视野,由此关注“小人物”的历史小说就变得具有越发强烈的可塑性和建设性,当代历史小说逐渐由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变为对人性的书写。马伯庸《长安的荔枝》这部小说紧紧跟随了这一潮流,作者对宏大的历史进行碎片化的解构,选用历史中无名小人物的视角进行叙事,不仅能够“借古讽今”,抒发当代人类生存困境,并且实现了与读者距离的拉近以及对读者阅读兴趣的满足。
马伯庸并不注重客观冷静的全景式历史事件描写,也不热衷于研究所谓的历史规律,而是将他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的关注与历史上那些不留名的小人物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变化结合起来,从而使他的作品与读者的心灵产生共鸣。马伯庸将笔触落在历史人物之上极尽刻画,读者却往往能在字里行间窥到对自身的映射,《长安的荔枝》便是将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马伯庸的独创性和对现实的关怀、刻骨铭心的幽默感,以及对历史材料和细节的孜孜以求,是他的历史小说受到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
马伯庸作为当代历史小说新编的典型代表,他的历史书写并不遵循宏大历史叙事创作传统,他选取任意时段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进行描写,运用自己的独特风格,幽默随意又立意深刻,引人入胜。他用宏大时代背景中的小人物的职场经历演绎了一段人们熟视无睹的有关人性和生存的故事。马伯庸没有解构或者颠覆历史,而是注重历史自身的史实性,围绕主题作出自己的灵活变动。马伯庸的历史小说穿过了厚重的历史来实现对当下的观照,找到了一个贴近读者的视角来去探索恒久的生存困境问题。马伯庸《长安的荔枝》这部作品就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时代要求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为当代历史小说的再创作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