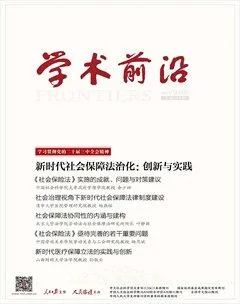社会保障法协同性的内涵与建构
【摘要】在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社会保障法的协同性需要引起关注。社会保障法的协同性有形式协同性和实质协同性两重内涵。从法律实施情况来看,形式协同性既表现为社会保障法与财税法、金融法、慈善法等存在的法间协同需求,也表现为社会保障法的实施需要多部门共同协作的部门协同需求。长期以来,学术界主要围绕生存权保障来界定社会保障法的实质协同性,这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实质协同性更为准确的表达应为生存权兜底与发展权促进之间的协同。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保障法实质协同性的具体内涵。建构社会保障法的协同性,首先要处理好社会保障立法中“促进”与“限禁”的选择问题,明晰社会保障法形式协同性与实质协同性的法律基础;其次,要深化《社会保障法典》立法进程与实质协同性的交互关系;最后,要明晰形式协同性在三次分配中的不同体现,重点关注共享理念指导下的协同路径。
【关键词】社会保障法 协同性 社会保障法典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8.003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能否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地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社会保障体系能否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保障法理论与实践的生命力蕴含于其协同融贯的属性之中。全面深化改革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对社会保障立法提出了新要求,这可以从不同维度进行解读。从社会法体系协同与机制构建的基本原理来看,社会保障法规范在宏观维度存在与民法、经济法规范进行概念融贯与制度衔接的空间,最终在促进共享发展的层面达到整体均衡。从中观维度看,社会保障法体系与劳动法律体系能够在新业态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协调发展,在坚守“风险防范”底层逻辑的同时,促使社会法体系内部实现有序分工、系统协同,推动发展质量的有效提升。从微观维度看,社会保障法各子系统已经拥有较为成熟甚至庞大的规范群,有条件从现有规范的“存量”中提炼出社会保障法理论的融贯性,在回应社会保障领域现实问题的同时,促成中国特色劳动法理论的本土构造与有机更新。[1]本文将从形式协同性与实质协同性两个方面,对社会保障法的协同性加以阐释与凝练,并提出进一步建构社会保障法协同性的路径。
社会保障法的形式协同性:基于法律实施的视角
作为社会保障法司法适用的核心领域,以2023年为例,全年度社会保险法领域的司法实践保持活跃,作出司法裁判案例共计2930件,主要聚焦社会保险责任承担主体、责任承担范围、工伤认定标准以及社会保险的程序等问题。[2]观察其案由即可发现,社会保险领域的纠纷解决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紧密相连,在纠纷解决的表层即涉及如何与民事程序法与行政程序法协同的问题。如果将视野扩展至整个社会保障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其协同需求不只存在于如何与既有程序法规范实现融贯的问题上,还表现在其他方面。
一方面,社会保障法与财税法、金融法、慈善法等有着较强的法间协同需求。社会保障法较强的法间协同需求,与其本身较强的交叉属性密不可分。截至2023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66亿人、2.44亿人、3.02亿人,同比增加1336万人、566万人、1054万人,其中,工伤保险参保人数首次突破3亿人。全年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7.92万亿元,支出7.09万亿元,年底累计结余8.24万亿元。[3]社会保障法与财政关系密切。正如有学者指出,“社会保障在今日已然脱离运动论之层次,而优为现实的权利论课题,因而其支出往往具有义务性,而非仅止于任意性或裁量性的政策层面……社会保障受给权或给付请求权所保障之权利或给付,如无适当之财源支应,往往沦于纸上谈兵”。[4]在社会保险法领域,社会保险兼具保险性与社会性,在保持财务独立的基础上,还有赖于财政支持,所以社会保障法与财税法有着较强的协同需求,其重点在于区分社会保障与财政介入的区别,确立财政补助社会保险责任的规范路径,唯此才能在精算平衡下划定财政补助责任、在预算平衡下消解财政过度依赖,[5]最终实现社会保障法与财税法的协同融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增强社会保障可持续性,夯实稳健运行的制度基础,积极发展第二、三支柱养老保险,其中全面推开个人养老金制度是重中之重。[6]2022年4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2〕7号,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推动发展适合中国国情、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个人养老金”,并就参加范围、制度模式、缴费水平、税收政策等十方面提出意见,这是全国首次就“第三支柱”作出的统一制度安排,意味着各方关注已久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出炉”。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与社会保障法能否与财税法实现协同密切相关,同时对社会保障法与金融法的协同提出了新要求。在与财税法的协同方面,2018年4月印发的《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财税〔2018〕22号)首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第三支柱”的概念,并在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含厦门市)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标志着我国开始探索运用税收优惠引导个人开展养老金积累。截至2021年10月底,累计实现保费收入近6亿元,参保人数超过5万人。[7]虽然政策层面不断通过社会保险法与财税法协同的方式推进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但是商业养老保险的规模仍比较有限,参保人数和保费收入远未达到支撑起第三支柱发展的作用。由此,在推广商业保险的基础上,第三支柱调整制度思路,提出了以“个人养老金”为基础,建立“个人账户”,投资商业养老保险、养老目标基金、养老理财产品等多样化养老金融产品的制度体系,社会保险法与金融法的协同需求在个人养老金的推行背景下愈发重要。2021年8月,《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1〕95号)发布,选择“四地四家机构”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2022年2月,《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扩大养老理财产品试点范围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2〕19号)发布,养老理财产品试点范围由“四地四机构”扩展为“十地十机构”。截至2022年7月30日,已有23.1万投资者累计认购养老理财产品超过600亿元,虽然覆盖范围较为有限,但是扩大试点后表现出较大发展潜力。[8]2022年6月24日,证监会发布《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主要包含产品准入、机构准入、显式账户和独立机制四大核心要点,提出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募基金产品的规范细则。虽然目前养老目标基金还存在机构准入门槛较高、政策细则亟待落地等问题,但是基金市场的积极反应也从侧面反映出个人养老金投资养老目标基金的市场潜力,表现出社会保险法与金融法协同的持续性需求。
在社会救助领域的法律实施过程中,社会保障法与慈善法的协同需求愈加凸显。随着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逐步完善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在政府救助层面,“扩围增效”是基本工作基调,中央与地方合力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推动政府社会救助范围的有序拓展。关于如何“扩围增效”,社会保障法与慈善法协同的路径呈现出愈发明显的优势,尤其在凝聚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这一方面。社会保障法与慈善法的协同,关键体现在建立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衔接机制上。为低收入人口提供多样化的救助帮扶,是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形成综合救助格局的重要内容。2023年9月,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有效衔接的指导意见》,从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加强信息互通共享、创新参与途径方法、落实激励支持举措等方面,对引导动员公益慈善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救助工作作出部署。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机制协同的制度化也是促进慈善力量参与救助帮扶监管规范化、推动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项目融合多元化的重要举措。[9]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有着较强的部门协同性需求。以社会组织法的实施为例,聚焦社会组织领域的行政监管,社会组织领域的执法实践重点关注社会组织外部登记管理、检查监督、内部运营管理等方面,除行政处罚外,执法部门必要时还会采取列入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等信用惩戒手段,并根据需要引入司法实施机制,通过部门协同的方式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惩戒力度。例如,在民政部公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天津市某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叶某某利用职务便利,操纵基金会,以借款名义私自将基金会165万元慈善资金转移至自己名下某公司账户,被发现后仍拒不执行改正要求;同时,该慈善基金会还存在慈善活动年度支出比例不符合规定等违法行为。天津市民政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有关规定,对该基金会作出了吊销登记证书的行政处罚,并将案件相关材料移送天津市公安机关,对叶某某涉嫌挪用基金会资金的行为立案侦查。本案中,登记管理机关依托社会组织联合执法机制,根据有关规定将叶某某涉嫌挪用慈善资金的证据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有利于震慑侵害慈善财产的不法行为,加大追回公益慈善资金的力度,有力保障了慈善财产安全,同时也是社会组织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实践,是社会保障法实施领域跨部门协同的现实彰显。[10]
由于社会保障法综合性强、涉及多方主体、领域广泛、事务繁杂,在法治实施环节往往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以提升法治实施的质量和效果,因此跨部门协同有其必要性与现实需求。例如,社会保障领域相关资金的发放涉及与财政部门的统筹合作与协调。基于社会保障领域行政主导的法治实施特征,行政部门的依法履职对社会保障法的实施至关重要。而现阶段对行政机关执法的监督机制相对薄弱,行政执法的法律责任WHhE23MrBencjys/vsbl/w==追究机制、绩效评价机制不够完善,难以通过单一化的方式对行政执法形成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因此,为有效发挥司法在社会保障法治实施和权利救济方面的重要作用,应持续提升社会保障领域的法治化、权利化程度,通过赋予社会保障制度必要的强制效力,保证司法实践有法可依,补齐社会保障法治实施体系的“司法短板”,[11]满足社会保障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对部门协同性的现实需求。
社会保障法的实质协同性:生存权兜底与发展权促进的协同
社会保障法的形式协同性与实质协同性属于一体两面的关系,形式协同性更多是基于法律实施现状的实然层面提炼的现实需求,而实质协同性则是蕴含于社会保障法发展脉络和规制逻辑中的本质属性。回溯发展历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历史上存在着一定不足,包括法律规范长期缺位,长时间依赖政策支撑运转,“人们还没有习惯于运用法律制度进行实践操作”。[12]然而,社会保障立法先行又具有必要性,因为与民权、民生息息相关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体系的建立必须通过法律规范才能落实,社会法治的规范化、体系化和科学化也要求社会保障领域的制度必须在法律的规范下运行,“从政治制度走向法律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民主法治建设、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民愿望的必然结果”。[13]各类社会保障的发展原则需要在法律中确认,具体运行细则、政策优惠和责任机制也需要在法律规范中明确,唯此才能确保其能够通过国家权力真正实现。而通过立法规定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论证其正当性,明确权利基础,为制度构建提供正当性来源。
随着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推进、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涌现,仅以生存权兜底作为社会保障法实质协同性的内涵已经有所不足。社会保障的相关立法要解决的是权利基础的问题,在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仅以生存权兜底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已经有所不足,仅围绕生存权保障来提炼社会保障法的实质协同性内涵亦失于精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规定了国家的社会保障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社会保险的权利内容和国家义务,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这就以根本法的形式将“社会保险”等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使得国家负有相应义务,即国家应为公民享有这种权利提供相应的条件。[14]进一步追溯权利来源,社会保险权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保障权的子权利,[15]而社会保障权意指“社会成员(或公民)在面临威胁其生存的社会风险时,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保障和社会服务,使之维持生存并达到相当水准的生活的权利”。[16]“维持生存并达到相当水准的生活”这一标准,意味着社会保障权实际上是对生存权的保障。生存权是一项具体的权利,权利内容是健康且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生活。[17]“社会保障是生存权的救济方式”,“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受社会保障权就是社会弱者的生存权。这种形式的生存权对于社会强者只是在他是强者时才不需要,而一旦他沦为弱者,受社会保障就是他原来生存权的自然延伸”。[18]为了生存不受到威胁,个人有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国家和政府也有提供社会保障的义务。由此,“社会保险权作为劳动者基本人权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劳动者生存权的保障上”,以社会保险权为代表的诸多权利,作为社会保障权的子权利,从根本上讲也源自生存权。[19]
从生存权的本质考察社会保障的诸制度,会发现基于生存权的社会保障权建立在“生存标准”上,是“底线”性的权利约束,义务主体是国家。[20]例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条、第三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国家建立,保障对象是全体公民,坚持“保基本”的原则方针,目的是保障公民在年老时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这与生存权的内在逻辑相契合。
然而,随着社会保障改革进入深水区,以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为代表的诸多新制度不断涌现,更多新制度在设计之初并没有将生存权作为其核心内容,即没有将“保障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制度的出发点,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也与生存权的内涵不相符合,而将生存权保障作为社会保障法实质协同的基点已经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如《意见》指出,推动个人养老金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养老保险需要”,其具备“养老保险补充功能”。在个人养老金的制度建设中,国家和政府发挥“引导作用”,提供“政策支持”,个人参与遵循“自愿参加”原则,缴费也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承担。由此可以看出,以个人养老金制度为代表的诸多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其出发点更趋向于一种“既有制度的补充”、“多层次选择”和“质量提高”。虽然有评论指出,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发展迅速,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较低,第三支柱养老金等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尽可能覆盖非正规就业群体。[21]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在这部分群体中替代了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承担了保障生存权的作用。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理论研究,都认为平台劳动者的生存保障应当由基本养老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号)指出,要“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相关政策”,“做到应保尽保”。相关研究也认为现行法赋予了平台劳动者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资格,需要通过规范建构实现平台劳动者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权益。[22]同时,生存权的保障应当覆盖全体公民的基本保障,国家具有主动保障的积极义务,[23]这与个人养老金“补充”的定位和国家“引导”的角色存在一定出入。
因此,如果仅仅以生存权的内涵进行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可能过度放大国家责任,过度要求固定的保障标准,从而难以平衡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目标的实现和市场活力的发挥。无论是从制度目标还是权利义务主体角度,社会保障法的实质协同性应当具备更为丰富的内涵。
推动社会保障体系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生存权兜底与发展权促进的协同,这也是社会保障法在新时代应当具备的实质协同性内涵。发展权作为一项人权观念,首先在国际层面被提出。198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在第1条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24]中国作为发展权的倡导者、践行者和推动者,也明确将发展权视为首要的基本人权。由此,发展权作为人权,是指“每个人和所有人民为实现其各方面人权而全面参与发展进程、公平享受发展成果,不断改善其生存和发展状态的权利”。[25]从中可以看出,“发展权是一种综合权利”,[26]可以从权利形式上划分为经济发展权、政治发展权、社会发展权、文化发展权和生态发展权,[27]也可以从内涵维度划分为平等参与发展的权利、促进发展的权利、平等享有发展成果的权利和人自身得到发展的权利。[28]新时代诸多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基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保障需要的定位,实际上解决的是人民群众追求高于基本社会保障标准的需要和缺乏相应的市场化补充制度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扩大基金市场化投资运营规模、健全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制度体系的现实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29]以个人养老金为例,这种制度正是发展权的体现:[30]以终生收入为基础,养老保险制度会对同一代人不同生命周期或者不同代人之间的终生收入进行长期再分配,即发生代内和代际的收入再分配效应。[31]个人养老金制度就是让个人充分参与终生收入的分配过程,保障个人的发展权利,并且协调代际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促进每个人平等享有发展成果。
因此,社会保障法的实质协同性指向了生存权兜底与发展权保障的协同,其背后暗含了政府兜底和个人提升如何在社会保障法的框架下实现协同的问题。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指向不同,生存权指向的是生命的维持和延续,发展权指向的是人生活的方式和目的。尽管如此,生存权和发展权之间也存在良性循环,生存权的实现对发展权的实现具有支撑作用,生存权保障水平的提升,为实现参与、促进和享受发展权利提供更充分的现实条件。[32]例如,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保障了个人基本的养老需要,而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的养老保障、更丰富的老年生活的向往。[33]由此,在当前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实现广泛覆盖的前提下,[34]下一步的制度目标转到了解决更高的养老保障需求上,个人养老金制度应运而生。可以说,从建设完善基本养老金制度,到发展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尤其是加速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是具备生存权保障的基础,进而追求发展权实现的生动例证,同时也表明社会保障法实质协同性的实现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个人养老金制度与基本养老金制度的协同,是社会保障法生存权兜底与发展权提升的协同性在养老保障领域的具体表达。
社会保障法的协同路径
处理好社会保障立法中“促进”与“限禁”的选择问题,明晰社会保障法形式协同性与实质协同性的法律基础。现代性法律能够把积极的鼓励促进与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从而具有突出的规制性,规制性涉及对不同对象的发展选择和手段上的宽严取舍。[35]其中,经济法与社会法中能够直接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以法定的鼓励性与促进性为手段的规范类型的集合,可称为“促进型法”;而通过法定的限制性和禁止性手段、间接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规范类型,则可称为“限禁型法”。[36]社会保障法作为典型的社会立法,具有突出的现代性,也面临在“促进”和“限禁”之间的选择。诚然,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必将同时包括“促进”与“限禁”的具体规范,处理好社会保障法的法间协同问题,如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个人使用个人养老金账户、服务商提供养老金融产品,通过市场准入等门槛限制市场的无序发展,保障个人账户的资金安全等。然而,社会保障立法必须坚持“促进型法”的原则,充分发挥促进型法律规范的作用,这一方面是由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质协同性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现状决定的。“促进型法”通常针对那些社会关系尚未得到良好发育、市场规模并未形成而急需鼓励形成市场规模的领域,因而主要解决供给问题,对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引导意义。[37]以个人养老金为代表的社会保障领域新制度,仍处在“试点”发展的初期,尚未在全国推广。在“供给”问题尚未解决、覆盖率亟待提升的发展背景下,具体规范应当坚持“促进型法”的主要导向,更多地设置优惠政策和鼓励发展的制度机制,尽可能避免过多的限禁规范。
深化《社会保障法典》立法进程与实质协同性提炼过程的交互关系。当前,社会保障规范仍存在体系不完善、内容缺失、覆盖面窄、可持续性差等缺陷,以“一法驭多法”的模式制定《社会保障法典》是重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的最优选择。[38]前述问题也可以考虑通过编纂《社会法典》的方式解决,通过“社会法总则”以及最终的法典具体实现。[39]法典化是实现社会保障法协同性的极佳路径,但需注意“对特定完备价值表达尊重和坚持,就是法典化的核心意义之所在”,而“特定完备价值”意味着“一方面它毋需向外援引其他更高阶价值作为根据,另一方面它使得本部门法的多数规范凝结为价值上的统一体”。[40]因此,基于法典化背景下实现的协同性是一种坚守社会保障法本位的协同,更多解决的是实质协同性的问题,即生存权兜底与发展权促进的协同。生存权兜底与发展权促进不仅是社会法体系协同的重要一环,更是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属性之一,应当作为社会保障法的“特定完备价值”之一,与政府责任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和普遍保障原则一起,一方面成为社会保障法可以法典化的有力证成,另一方面在社会保障法典化的过程中不断得以完善。
明晰形式协同性在三次分配中的不同体现,重点关注共享理念指导下的协同路径。我国社会法在兼顾公平和效率、调节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皆将“倾斜保护”作为其制度构建的逻辑脉络。具体而言,在初次分配环节,最低工资制度等劳动基准制度以及工资支付保障制度,能够确保劳动者收入的全面实现,并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稳步增长机制,通过社会法的介入确保劳动者不受任意剥削。在第二次分配环节,社会法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资源分配,即通过对社会保障资金和公共财政资金的统筹安排与转移支付,弥合不同收入群体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促进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在第三次分配环节,社会法通过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以自愿转移个人收入和志愿服务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分配社会财富,在精准纾解特定社会成员困难、推动共同富裕进程的同时,提高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可以说,就社会保障法的形式协同性而言,在法间协同的层面,社会保障法与慈善法的协同更多体现在第三次分配的过程中,致力于社会力量的凝聚;而其与劳动法、财税法、金融法的协同则更为关键,这在前两次分配的过程中皆有所体现,需要通过对共享发展理念的贯彻实现其融贯性的落实。共享发展的理念不仅要注重各类主体的基本权利保障,更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充分保障各类主体的发展权,[41]不断提升其发展能力。这样才能使各类主体共享改革开放成果,[42]实现共同富裕,推动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43]在共享理念的指导下,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财税法和金融法的协同需处理好“兜底保护”“价值创造”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构建层次清晰、功能齐全、协调联动的社会法体系,实现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协同增效。例如,在第二次分配中,诸如《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及各地方的保障性住房条例等社会法通过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实现国民收入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转移支付,在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以缩小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确保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结论
社会保障法是规范社会保障活动、明确公民权利义务和国家责任的法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的重要内容,具有兼容公法和私法、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复合法律属性。协同性既是其基本属性,又是其在法律实施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需求。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之后,社会保障法治工作始终围绕着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更有效地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展开,体现了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社会保障法作为共享型社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形式协同性与实质协同性能否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真正落实,关涉共同富裕制度保障的构建是否成功、是否高效。需要在形式协同性与实质协同性的指导下,实现社会保障法的法外系统与法内子系统的高效配合,筑牢我国民生保障领域的法治根基,形成福利中国的有效制度支撑。
注释
[1]参见叶静漪等:《新时代劳动法的体系协同与机制构建》,见朱晓喆主编:《中外法商评论》第3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6~30页。
[2]参见叶静漪:《202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实施报告》,见江必新主编:《中国法治实施报告(2024)》,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5~298页。
[3]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2023年四季度新闻发布会》,2024年8月8日,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xhd/zaixianzhibo/202401/t20240124_512668.html。
[4]蔡茂寅:《社会保障的财政法思考》,《交大法学》,2014年第1期。
[5]参见胡明:《财政补助社会保险责任的规范类型与限度修正》,《法学评论》,2024年第3期。
[6]《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晓萍》,2024年8月8日,https://www.peopleapp.com/column/30046108531-500005640061。
[7]银保监会办公厅:《保险保障功能充分发挥 人民群众获得感大幅提升》,2024年8月8日,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26139&itemId=915&generaltype=0。
[8]《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研究适时再扩大养老理财产品试点范围》,2024年8月8日,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22-07-31/2385004.html。
[9]参见《广东省民政厅办公室关于公布2023年度社会救助领域创新实践活动情况的通知》,2024年8月8日,http://smzt.gd.gov.cn/gkmlpt/content/4/4298/mpost_4298576.html#1668。
[10]参见《社会组织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典型案例》,2023年1月30日,https://www.mca.gov.cn/n152/n164/c36675/content.html。
[11]参见杨思斌:《我国社会保障法治建设四十年:回顾、评估与前瞻》,《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12][13]郑尚元:《公开、规范与定型——养老保险制度从政策到法律——中国社会保险立法的进路分析》,《法学》,2005年第9期。
[14]史博学:《“社会保险权”在我国立法中的确立与完善》,《法学论坛》,2019年第4期。
[15]吴德帅:《消解与重构:制度演进视阈下的社会保障权研究》,《社会保障研究》,2017年第5期。
[16]郭曰君等:《论社会保障权》,《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7]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台北:元照出版社,2001年,第119~129页。
[18]徐显明:《生存权论》,《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19]常凯:《论社会保险权》,《工会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3期。
[20]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年,第298~301页。
[21]郑秉文:《养老金三支柱理论嬗变与第三支柱模式选择》,《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22]汤闳淼:《平台劳动者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规范建构》,《法学》,2021年第9期。
[23]赵新龙:《权利递嬗的历史逻辑——生存权保障机制的法哲学史考察》,《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4期。
[2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人权》,2017年第1期。
[25]叶传星:《发展权概念辨析:在政治与法律之间》,《东岳论丛》,2019年第12期。
[26]艾君·森古布达:《作为人权的发展》,王燕燕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1期。
[27]汪习根等:《论中国对“发展权”的创新发展及其世界意义——以中国推动和优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为例》,《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28][32]马原等:《生存权与发展权之间良性循环研究》,《人权》,2021年第3期。
[29]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求是》,2022年第12期。
[30]郭晔:《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人权之道——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权理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31]P. A. Diamond, "A Framework for Social Security Analysi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7, 275-298(8);王亚柯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效应:收入与财产》,《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33]据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金融分会、清华大学银色经济与健康财富发展指数课题组、大家保险集团在京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养老服务需求报告(2021)》显示,养老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未来人均养老消费预期超百万元。老年人养老观念更加积极,除了稳定的退休金,60岁及以上群体还有相当数量额外的养老金需求。
[34]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超过十亿人。报告参见:http://www.gov.cn/xinwen/2022-06/07/content_5694419.htm。
[35]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36][37]叶姗:《促进稳定发展的法律类型》,《现代法学》,2009年第2期。
[38]参见金锦萍:《论法典化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障法的体系和基本原则》,《法治研究》,2023年第3期。
[39]叶静漪等:《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法的转型与重点立法任务》,《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1期。
[40]陈景辉:《法典化与法体系的内部构成》,《中外法学》,2022年第5期。
[41]参见程信和:《经济法基本权利范畴论纲》,《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张守文:《经济发展权的经济法思考》,《现代法学》,2012年第2期。
[42]参见张彦、洪佳智:《论发展伦理在共享发展成果问题上的“出场”》,《哲学研究》,2016年第4期。
[43]参见张守文:《新发展理念与“发展型法治”的构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7月上。
责 编∕张 贝 美 编∕梁丽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