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如何开展舆论监督
中央苏区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红军部队,都办有报纸和刊物。当中,既有《斗争》、《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苏区工人》等最具代表性、发行量大、影响深远的刊物,也有图文并茂和通俗易懂的油印或传单式小报。运用这些报刊广泛开展舆论监督,是中央苏区提高党员干部素质和改进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苏区报刊普遍设立了“突击队”、“轻骑队”、“铁锤”、“铁棍”、“铁锥”、“铁帚”、“红板”、“黑板”、“反贪污浪费”、“自我批评”、“苏维埃建设”、“党的生活”等舆论监督专栏、专题、专版,对腐败现象“给予最无情的揭发与打击”,“使他们不能在苏维埃政权下继续生存下去,这样来改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来教育广大群众”,打造“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注重舆论监督的政治性
苏区报刊“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喉舌”,“是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报纸”。因此,必须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宣传政治思想主张、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舆论阵地。苏区报刊的反腐倡廉舆论监督,服从服务于革命战争,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服从服务于苏维埃运动需要,服从服务于人民群众需求,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革命性、时代性和鼓动性。比如,《红色中华》的发刊词说:“组织苏区广大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尽到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指导各级苏维埃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始终观点鲜明、毫不含糊。 苏区报刊紧紧围绕中央的部署和安排,着力聚焦反贪腐浪费、反官僚腐化、反消极怠工等从严治党主题,大力宣传训令法令,深入剖析大案要案,及时报道反腐成果,以主题舆论提升监督实效,扩大舆论监督影响。例如,为配合中央政府开展的“节省运动”,苏区报刊推出了一系列社论、评论、消息、通讯、杂文、漫画等,提出了“节省每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每月节省三十万来帮助革命战争”、“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等响亮口号,推出了一大批开展节省运动的先进典型模范,曝光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席卷苏区的节省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红色中华》报道:1933年11月中央苏区经费预算总计为3303145元,12月份就降至2415057元,节省了888088元;1933年11月,中央政府各部门预算总额为12032元,1934年3月增设了粮食部,预算总额反而减少到2831元,节省了9201元;中央审计委员会,仅1933年12月就节省了20万元以上。
注重舆论监督的群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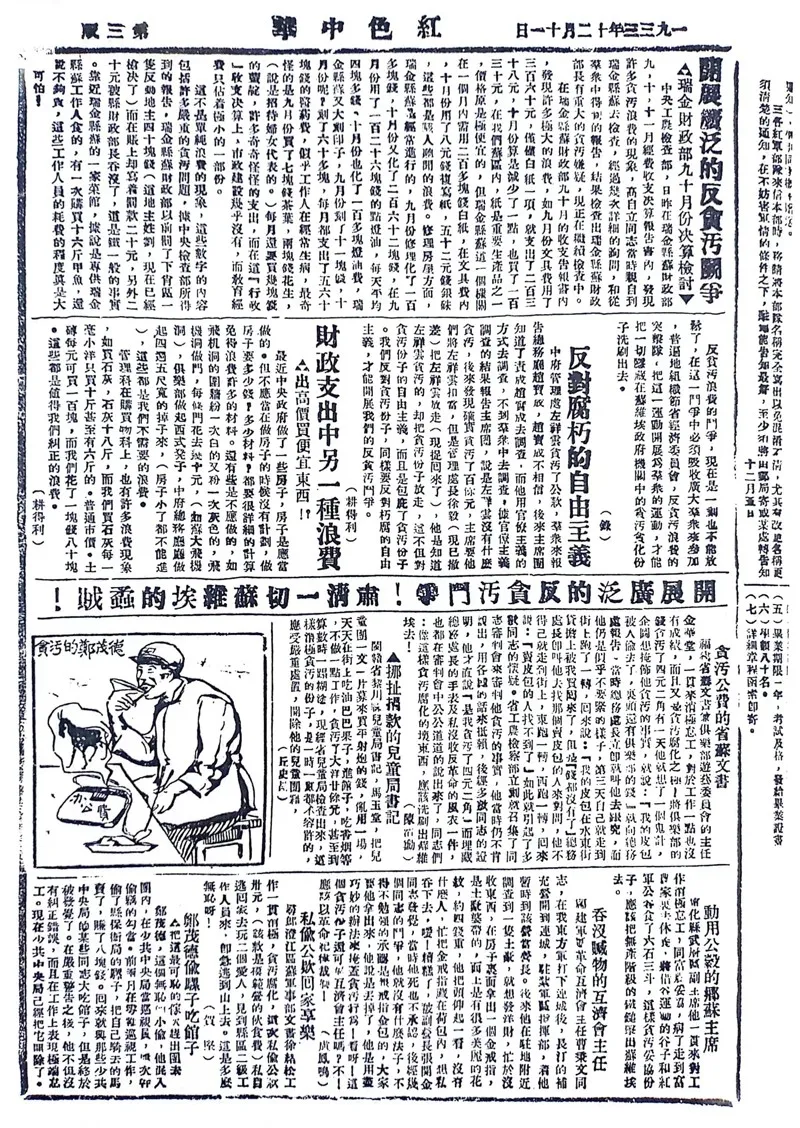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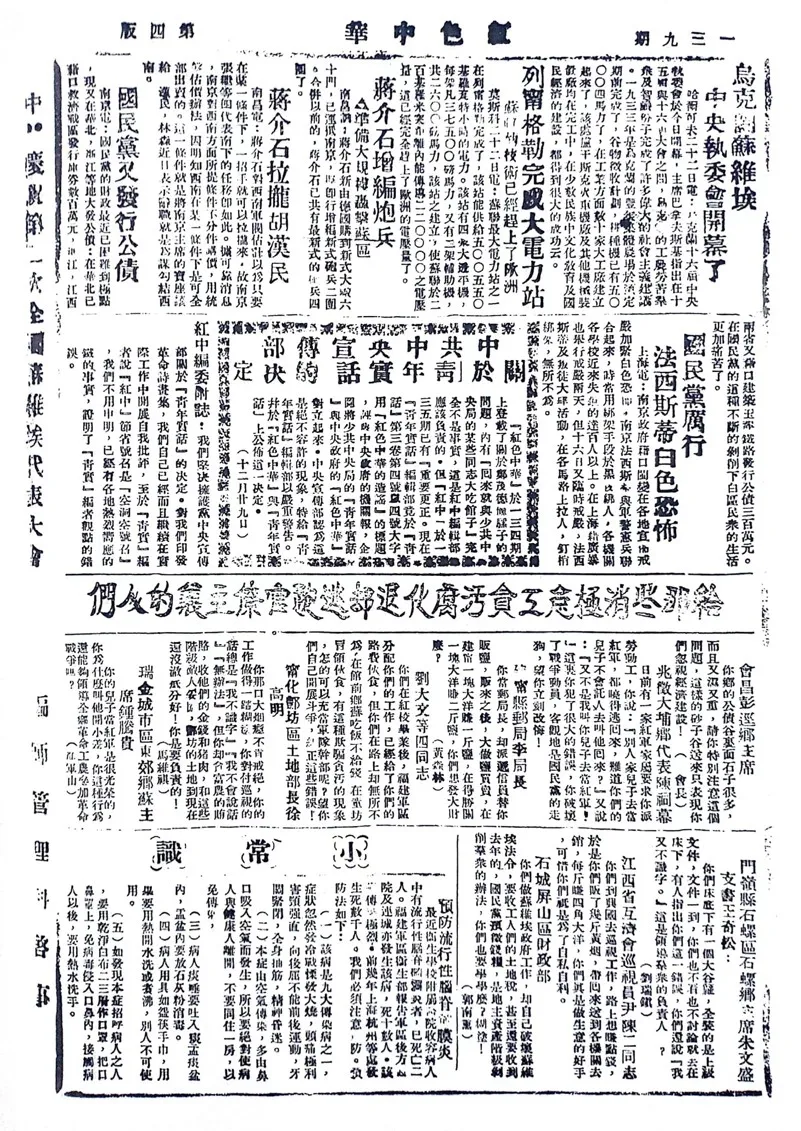
苏维埃规定:“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和缺点之权”。为深入开展群众检举运动,1932年初,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开展检举运动的训令。建立各级控告局和临时检举委员会,专门受理群众举报。要求“每个乡,每个村,每个屋子,每个机关,每个企业中都应该有它的通讯员”,并且各机关、群众团体、圩场、村庄以及城市中各街道,都要找素质好的群众来担任通讯员 。《红色中华》、《斗争》、《青年实话》等苏区报刊与群众监督组织联动互动,专门开辟了“突击队”、“轻骑队”等群众性舆论监督专栏,大量刊登工农通讯员、突击队员、普通群众的来信来稿,从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群众性舆论监督网络,使腐败分子时时处在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有力地打击震慑了腐化堕落分子。既发动群众开展检举运动,又发动群众撰写批评稿件,紧紧依靠群众进行舆论监督,是中央苏区舆论监督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苏区各级报刊普遍没有专职记者,基本全靠通讯员投稿。例如,《红色中华》通讯员有400多人,《红星》仅专职通讯员就有500多人。通讯员中,有党政军的各级领导干部,更多的是基层工农兵群众。为便于及时反映群众呼声,许多苏区报刊还专门设立了“读者言论”、“读者来信”等栏目,用于刊登读者的批评建议、时事言论和表扬稿等。依托无处不在的群众性舆论监督,使一个个大案要案得以及时查处,一个个蛀虫害虫被清除出革命队伍。“特别是各级机关的工农通讯员,他们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多数的贪污案件是由于通讯员的通讯而检举,更由于群众的参加与揭发”。
注重舆论监督的典型性
在开展舆论监督中,苏区报刊选择那些最具代表性、紧迫性、严重性的问题与错误,选择那些具有典型性、现实性、针对性的文章与案例,予以公开曝光和无情抨击。例如,《红色中华》刊发的《贪污与腐化》、《奇妙的罚款》、《合伙瓜分公款》,《青年实话》刊发的《不良青年的标本》、《劳动部长未免太劳动了》等众多新闻监督稿件,其内容都兼具“最标本”的特点,发挥了很好的监督作用。在舆论监督中,苏区报刊对于大案、要案的曝光,重要社论、评论的发表,重要训令、法令的发布等,大都由苏区中央局、中央军委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亲自撰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为《红色中华》、《斗争》等中央苏区报刊撰写过社论和文章。领导同志和权威机构在报刊上的铿锵发声,不仅体现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对舆论监督的重视与支持,也体现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的信心与决心,使舆论监督更有号召力和震慑力,更有严肃性和权威性。在舆论监督中,苏区报刊切实把各种监督紧密结合起来,大大增强了舆论监督报道的真实性、本源性。有时,苏区报刊还通过发布公告等形式,直接公布惩治贪污腐化判决书,以最直观的反腐成果教育党员干部。
注重舆论监督的深入性
为营造从严治党、反腐倡廉的强大舆论,苏区报刊在版次编排和版面使用上,或安排头版头条,或开设通栏、专栏,或动用多个版面,大量推出反腐倡廉舆论监督稿件,持续保持了舆论监督高压态势。整版或几版都刊登揭露揭发批评贪污腐化问题文章,造成强烈的视角冲击和心灵震撼。为揭发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中的第一大窝案——“于都事件”,《红色中华》在1934年3月8日、10日、13日,连续刊载了系列追踪报道,深入揭发了于都检举的情形和经过,及时报道了案情的审查及处理结果,深刻剖析了腐败产生的原因及教训,起到了强烈的警示、震慑和教育效果。
注重舆论监督的实效性
坚持问题意识,保持建设心态,力促问题解决,是中央苏区舆论监督与斗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一是既谈问题,又谈举措。如《红色中华》第5期第6版,刊发了《奇怪的河田乡分田》一文,批评长汀河田乡分田工作滞后,分了3个月还没分完,作者张鼎丞分析了问题原因,并针对分田问题提出了“七项措施”,其中包括“确定分田观念,发动农民参与分田斗争,严厉打击妨碍分田的土豪流氓,组织雇农工会等”。二是追踪监督,督促整改。比如,针对临时中央政府建立初期不少机构存在的各自为政、自由散漫现象,《红色中华》于1932年2月10日有针对性地发表了《反对忽视上级命令和敷衍塞责的恶习》批评文章,指出:“就政权的隶属上说,下级政府应绝对服从上级政府。”2月24日,又推出专题社论《实行工作检查》,再次批评这种不良现象,指出:“在将近三个月以来,各地对于中央政府一切训令、通令、决议等的执行,那是非常令人不满。”这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症结所在,并一追到底,引导相关部门正视问题、克服错误,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声势,推动了工作的改进。三是坦诚批评,有错必纠。苏区报刊积极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既强调要不留情面指名道姓开展批评,又指出批评时要“废止讥诮的口吻”,这充分体现了苏区报刊冷静、理性、坦诚的批评态度。一方面,苏区报刊专门设立“自我批评”等栏目,拿出版面供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做自我批评。另一方面,倘若批评与事实有出入,允许当事人辩解,并予以澄清事实。四是平等对话,均衡表达。给予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以同等的话语权,是苏区报刊开展舆论监督的又一创举。
注重舆论监督的通俗性
针对苏区干部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特点,注重语言的通俗化、形式的多样化和内容的简明化,是苏区舆论监督的一大特色。从体裁来看,苏区报刊通过消息、社论、漫画、杂文等众多形式,多层次多角度对腐败现象开展尖锐的批评和无情的斗争,采取不同形式的报道,取得了良好的教育警示效果。从文风来看,苏区报刊的批评文章简洁明快、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常常运用描写、议论、夸张、比喻、设问等多种修辞方法,或在文章末尾加上少许评论,促使监督批评非常清晰到位,使人一看就留下很深的印象。从方法来看,苏维埃的报刊不仅要无情揭发苏区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还必须从正面大量宣传和表扬先进典型、先进模范,要介绍他们的生动事迹,树立学习的榜样。苏区报刊特别注重报道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在褒扬与批评中形成浓厚的反腐倡廉舆论氛围。从手段来看,苏区报刊还特别注意广采博闻,尤其注意由小见大,“注意查察,有一点小的表现就要跟着去查,常常能从小问题中查出大问题,瑞金的大贪污案就是从他们灯油费一件小事着手查出来的”。
(本文作者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党组成员、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