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合规高效管理地方政府债务还需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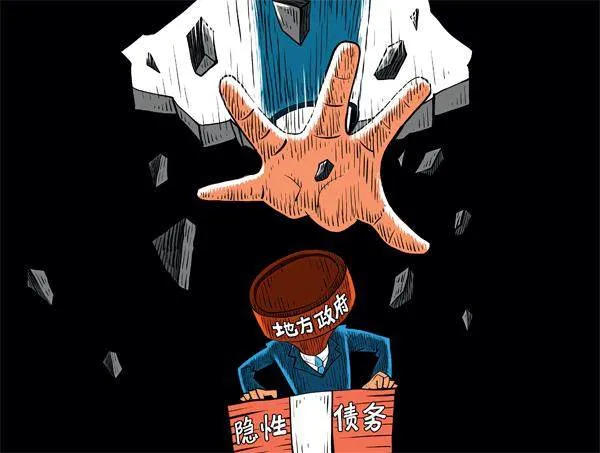
9月19日,财政部网站发布8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以下简称“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的通报。该通报涉及8个省份的相关部门违规举债,分别是:天津市天津港保税区、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湖南省属公办职业学校、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吉林省通化市梅河口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海南省临高县、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从金额看,此次通报新增隐性债务116.41亿元,化债不实0.68亿元,合计117.09亿元。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指地方政府在法定预算之外,直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以及违法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
自2022年实施新一轮隐性债务化解工作以来,财政部共发布4次涉32起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此次通报的这8起与以往有何不同?背后透露出哪些信息?
通过国企新增隐性债务金额超八成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发现,此次财政部披露的8起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涉及天津、辽宁、湖南、江西、吉林、内蒙古、海南、宁夏8个省份。这8起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中,7起是新增隐性债务,1起是化债不实。
2022年以来,财政部共发布4次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通报。从此次通报的8起典型案例看,相比以往,新增隐性债务的投向有所变化。
2022年,财政部分别于5月、7月各披露8起典型案例;2023年11月披露8起。总体来看,在2022至2023年发布的3次通报中,新增隐性债务使用投向大多为水利、公路、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此次通报的隐性债务典型案例,发生在2018—2023年期间,在7起新增隐性债务投向中,3起是向地方国企借款偿还存量债务、将借款纳入城建专户统筹使用等,违规举债金额为97.33亿元,占此次披露总金额的83%。
超八成的违规举债资金,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
天津市天津港保税区颇具代表性。根据财政部通报,2018年6月至2023年5月,天津市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向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天津天保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借款147.32亿元,并全部转借给天津临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用于偿还其存量债务。
截至2023年5月,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已归还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天津天保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27.57亿元,借款余额为119.75亿元。扣除用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统计监测系统中存量债务“借新还旧”的45.78亿元后,剩余部分形成新增隐性债务73.97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国家对保税区、开发区等实施了一系列特殊制度安排和优惠政策,而且借款是以天津港保税区党委常委会决议的方式通过的,属集体决议,看上去‘合规’,因此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事实上,越是这样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地区或机构,越应当成为财政部门监管的重要对象。”
另外两起向地方国企借款的案例是: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向地方国有企业借款新增隐性债务19.96亿元;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通过地方国有企业借款新增隐性债务3.4亿元。
“通过向国企借款形成债务,看起来是企业的债务,实际上是政府的债务。”许光建指出,国有企业由政府出资或控股,与地方政府存在天然的联系。这种产权关系使得地方政府在与国有企业沟通和协调时具有便利性,双方更容易达成合作意向。“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少数地方政府没有划清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把国企当作政府‘融资’的工具了。”
近年来,财政部多次强调严禁地方政府通过国有企事业单位违规举债。《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提出,督促地方政府严肃财经纪律、强化预算约束、划清政企权责,严禁地方政府通过国有企事业单位违规举债建设政府投资项目,严禁举债建设楼堂馆所、形象工程。
更早之前,国务院在2021年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提出“严禁地方政府以企业债务形式增加隐性债务”。
监管信号已足够强烈,为何仍有个别地方政府铤而走险?
“事实上,地方隐性债务与地方国有企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杨志勇在2023年撰文《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势、成因与应对》,道出了隐性债务形成的根源:如果政企关系界定不明确,企业管理层听命于地方政府,执行政府指令,包括为地方政府举债或企业债务融资后执行地方政府的某些职能,这些都会带来地方隐性债务问题。
少数基层政府财政压力大,隐性债务形态呈现多样化
近年来少数基层政府财政运行遇到麻烦,是导致隐性债务增加的原因之一。
比如,2020年9月4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关于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拖欠教师工资补贴挤占挪用教育经费等问题的督查情况通报》,指出了当地拖欠教师工资和挪用教育经费的问题。

大方县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及上一年发展不足时称,财政收入偏低,财政增收乏力,历史欠账较大,税收收入持续低位运行。地方政府性债务、民生欠账等风险点仍然存在,还本付息压力较大,财政“收不抵支”,资金短缺与发展需要的矛盾十分突出。
还有个别地方基层“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也在经受挑战。
“受此前疫情影响、房地产市场冲击,有些地方‘三保’困难,于是通过融资平台变相举债,以弥补财力不足。从总体上看,财政为基层‘三保’提供了有力的财力保障,但部分地方刚性支出不减、化债任务重、收入端又受到冲击,必然对‘三保’产生负面冲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吉富星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说。
“财政部连续披露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主要是起警示作用。相比而言,市县级政府隐性债务问责比例相对较高,可能的原因是市县级政府财政收入有限、法定范围内的政府发债配比受限,同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较高,导致举借隐性债务的动机更为强烈。”许光建说。
2014年新预算法取消了地方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并且开始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实行限额管理和存量债务置换。
“在新预算法实施后,地方政府唯一举债途径就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而且不得违规担保。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债务认定实现清晰化、法定化,监管对象从政府性债务过渡到地方政府债券。”吉富星表示。
但是,政府显性债务以外的担保、举债行为仍然十分普遍。“尤其是在新预算法实施以后,地方政府通过企事业单位、社会资本等主体进行变相举债,其中,政府隐性债务的主要载体是融资平台。”吉富星说。
2017年隐性债务整改以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普遍通过融资平台、社会资本等去融资,以文件(政府承诺函、决议)、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形式,或明或暗将项目付费责任纳入财政预算,或通过融资平台来变相列支预算。
地方融资平台的设立,始于东部发达城市,是这些城市的创新融资工具,支撑了当地交通、水电气热等设施建设。但是,遍地开花的融资平台,意味着举债规模迅速膨胀,地方违规担保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此次财政部披露的8起典型案例中,还曝光了其他违规举债的隐蔽手法。
2018年11月,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自行确定与岳阳湘女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合作,采取以租代建的方式建设新校区,通过每年支付租金1233万元和以三产委托经营(包含新、老校区)的方式进行回购,期限30年,总金额4.5亿元,形成新增隐性债务4.5亿元。
此外,财政部曝光的其他地方还有:海南省临高县要求代理银行垫款支付且长期未清算新增隐性债务8.4亿元。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国有企业以农村人饮及农业灌溉特许经营权质押融资新增隐性债务3.2亿元。吉林省通化市梅河口市以公立医院等为主体贷款新增隐性债务2.98亿元。
近年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形态呈现多样化,如何识别?吉富星认为,很多隐性债务隐蔽性强,看似企业债务、金融债务,实则替政府融资。他提出,认定隐性债务要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和“穿透”两大原则,从还款资金或财政偿付责任来界定。
“实质重于形式”,重在强调按照其业务实质、本源来揭示政府本应该承担的风险。“穿透”原则更侧重于操作层面,即要识别底层资产是否属于非市场化运营的公益性项目、最终还款方是否政府。
“不管项目如何包装、模式如何‘创新’、交易链条有多长,从‘借、用、还’几个环节联动看,重点放在‘还’这个环节,关键看是否由财政资金偿还,或主要靠财政补贴来还本付息或回收投资成本,形成事实上政府‘兜底’,但这并不代表有财政补贴的债务就一定是隐性债务,需要视情况而定。”吉富星表示。
政绩观偏差是违规举债重要动因
在财政部先后4次发布的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通报中,至少有177人被问责。
“违规举债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有客观层面的财力不足、‘三保’困难、防风险所需等因素,也存在政绩观偏差以及可能的腐败等问题。问责也会根据举债的后果、危害等进行分类处理,并不限于简单的行政性处分,未来还是要强化并落实‘终身问责和倒查责任’机制。”吉富星分析说。
从公开的信息看,近年来,不少有关落马官员的通报都出现过盲目举债、违规举债等表述。
比如江西省吉水县委原书记袁守旺,罔顾该县财政年收入仅10亿元的现实,狠砸6.8亿元建设中国进士文化园,使当地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陕西省西乡县委原书记演晓刚未经科学论证,频频上马多个不切实际的“大工程”;贵州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再勇在六盘水任职期间,推动兴建23个旅游项目,其中16个项目被贵州省列入低效闲置项目,3年多时间就给当地新增1500亿元债务……
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许光建一语道破:“那些违规举债被问责甚至因违法违纪而落马的少数领导干部,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贪大求洋,急于求成。本来一个地方有多少资金能办多少事都应进行科学论证,如果想上新项目,也要通过正规的合法途径筹集资金。之所以敢冒险,估计在他们看来这样能够很快出‘政绩’,于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隐性债务方式绕开国家的相关规定。”
财政部此次通报称“以上八起典型案例,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干部政绩观存在偏差,纪律观念不严,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搞变通,严重影响了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成效”。
不仅如此,财政部通报称,对新增隐性债务和化债不实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持续强化隐性债务查处问责力度,有效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
“开前门”“堵后门”化解隐性债务风险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事关发展安全、事关民生福祉、事关财政可持续运行的重大问题。
近年来,我国积极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健全完善地方政府法定债务管理,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2018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办法》落地后,2021年《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推出。《意见》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地方政府及其部门、金融机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均有提及,同时再度强调严格落实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
2023年以来,按照关于“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的决策部署,各有关部门、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采取更多更实举措,取得了积极成效。
针对少数地方依然违规举债,今年以来,中央进一步加大隐性债务化解力度。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加快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
9月14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对地方债务管理强调了“着力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的要求,提出下一步财政重点工作安排包括统筹好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进一步落实好一揽子化债方案,全省负总责、市县尽全力化债,逐步降低债务风险水平等。

“经过持续多年的隐性债务化解,我国的地方隐性债务规模增速总体在放缓。但是部分地方债务压力依然不小,县市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许光建表示。
针对隐性债务治理难度大,吉富星认为,债务化解应加快构建疏堵结合、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
“化解隐性债务的核心,还是要进行系统的体制机制改革,尤其是深入推动财政体制的事权改革、纠正不正确的政绩观。就当下的情况而言,应积极推动、实施更大力度的一揽子化债政策,助力防风险措施落地见效。其中,进一步加大中央杠杆,将部分市县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要上移到中央或省一级承担,并减少基层配套支出压力,这样可以大大减轻县市一级的财政压力。”吉富星说。
在事权改革的同时,吉富星建议,要坚持“开前门”和“堵后门”并举。
“可以把‘前门’开得大一些,适度加大中央债务杠杆,把地方债务显性化、适当提高一般债比例,用显性来替代隐性。在此基础上,采取更大力度来稳妥化解债务存量。同时,加强债务合并、穿透监管,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加强监督问责,形成遏制隐性债务的长效机制。”吉富星说。
接受采访的专家一致认为,有效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必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加强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检查工作,根据新的情况变化,不断优化监督检查的方式方法,确保各级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依法合规高效。
责编:姚坤 yaokun@ceweekly.cn 美编:孟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