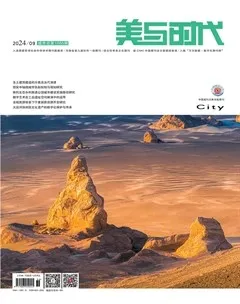博里农民画在乡村公共艺术中的再生产研究

摘 要:中国传统民间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珍贵的艺术瑰宝。以江苏省淮安市博里农民画为研究对象,对其自创生以来的境遇进行梳理,分析其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不同样貌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从再生产的价值与目的、风格与内容、措施与路径等角度出发,探索如何在不断发生变迁的文化语境中实现有效的当代转换。同时,强调乡村公共艺术模式下的农民画再生产是其对中国乡村“空间-地方”的再生产,其最终目标指向重新定义中国农民的文化身份,进而以艺术的方式重构中国乡村生活空间。
关键词:博里农民画;乡村公共艺术;艺术乡建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文旅融合视野下江苏乡村公共艺术的发生机制研究”(23SYB-144)、2022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旅融合下江苏传统村落景观符号演化与认同建构研究”(22YSB016)、2023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社会-生态系统下的云南景迈山农业文化景观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研究”(2023J1228)研究成果。
农民画,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民间美术辞典》中,张道一将农民画定义为:“通俗画的一种,指由农民自己制作和为农民生活服务的绘画、印画形式。”[1]以1958年关于邳县农民画的公开讨论为起点,中国农民画已经历了60余年的发展历程。作为我国“四大农民画”之一,博里农民画兴起于江苏省淮安市博里镇,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博里农民画立足于反映博里农民自身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本文试图从博里农民画的境遇变迁出发,探讨农民画这一中国特殊绘画类型在当代乡村公共艺术的语境中如何进行转换并实现物质与精神两种层面的再生产问题。
一、作为乡村公共艺术的中国农民画
乡村公共艺术的名称是相对于发生在城市中的公共艺术而言的。A. Goddin曾在《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中对城市中的“公共艺术”下了两个定义:第一,公共艺术诉诸广泛的观众,常系由它的规模与设置状况来决定;第二,它处理的是具有认知可能性的社会意义的主题。而参与美国公共艺术早期发展的弗利曼(D. Freedman)在其《公共雕塑》(Public Sculpture)一文中认为,公共艺术拥有三条硬性标准:具有高度的审美水准、规模与公众的关系。依此来看,乡村公共艺术除了在实施空间上有异于城市公共艺术外,其具体的表现与城市公共艺术并无本质区别。但是公共艺术实施空间的差异并非简单的位移,其蕴含了不同类型空间所能释放公共性的无数可能性。“乡村”与“城市”并不是两个物理空间,而是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1982年,中国美协提交的《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支持,认为公共艺术以“城市雕塑”的名义出现是合理的[2]。此时,公共艺术的主要发生场域集中于城市。2018年,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倡“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并强调使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公共艺术的发生场域“回到”了乡村,并在乡村振兴的语境中寻求再生产的可能性。
在乡村公共艺术的内部表现上,其与城市还存在着巨大差异。以中国农民画为例,城市公共艺术中以(职业)艺术家为创作主体的模式,在这里被农民主体取代。除此之外,中国农民画还有一特殊性,即中国农民画从中国革命的语境中发展而来,并与农业集体化的现实相遇,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乡村发展息息相关[3]。这也决定了诸如博里农民画这样的绘画作为一种乡村公共艺术的特殊意义。如何再生产,是这种特殊性的衍生问题。
二、博里农民画发展的境遇变迁(1981年至今)
(一)发端期(1981—1991年)
博里农民画是一种自发的、以博里地区农民为主体的民间艺术类型。我们将博里农民画的第一个时期称为发端期。1980年初,淮安博里原文化站站长朱震国带领当地农民中的美术爱好者创办兴趣小组,他们以自学、互学为主,同时聘请专业教师进行短期培训,在此基础上成立创作组,并建立“农民画苑”。由此,博里农民画的早期创作骨干队伍逐渐形成。例如,1983年,博里农民画的代表人物潘宇参加了当年的全国农民画大赛,并以作品《农民小世界》获得嘉奖。到1985年前后,中国农民画的定义被进一步明确:第一,创作者的职业必须是农民;第二,画面构图必须饱满;第三,色彩对比必须强烈;第四,绘画题材必须与乡村相关。在此基础上,博里农民画得到了迅速而成体系的发展。1991年,博里镇被原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
(二)成熟期与发展期(1992—2006年)
20世纪90年代,潘宇等博里镇文化站工作人员将博里镇各村喜爱美术、五十岁以下的农民组织在一起培训,培训时间最少三年、最长五年,随后让这些学员回到各自村落进行传授、培训,使得博里农民画的创作队伍不断扩大。然而,这一时期的博里农民画的发展也存在许多问题。潘宇表示,对于农民画的扶持发展资金严重不足,再加上因乡镇机构改革,乡镇文化站与广电站合并,文化站的地位急转直下,这种情况导致农民画创作骨干纷纷外出打工谋生路,农民画创作逐渐萎缩。
在这里,我们要将博里农民画的发展置于1992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在发端期能够以“自学、互助”的形态发展起来的农民画,实际上植根于彼时的农村集体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在发生变革的同时,农民画的创作主体——农民的身份实际上也发生了变化,“进城务工”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选择,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初期“阵痛”的体现——乡村与城市空间的一体化、农民与城镇居民的一体化,以及乡村生产模式与城市生产模式的一体化。这不仅重塑了博里农民画的生产空间,还促使博里农民画根据新的语境进行调整。
(三)再生产期(2007年至今)
2007年,江苏省委宣传部将博里农民画列入全省重点发展的特色文化项目。2008年,博里镇又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引进企业资金500万,兴建了中国博里农民画院和中国博里现代民间画艺馆,与投资企业签约,有偿引进农民画师作品,并合作开发博里农民画系列美术工艺品、装饰和服饰类产品。这一时期,文化政策引导与市场化运作的介入,为博里农民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近些年,在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农民画苑”项目开始了新一轮的教学培训,仍由潘宇牵头,一年开办了农民画免费培训班6期,每期培养30人左右。同时,中国博里农民画院进一步拓展博里农民画的衍生产业,如在本地传统刺绣工艺的基础上开发农民画与刺绣相结合的农民画刺绣等。这一时期,博里农民画才真正进入当代意义上的乡村公共艺术的发展领域,其再生产的空间场域与文化语境在此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博里农民画的公共特点是积极参与农民生活,而不是仅仅将农民生活当成创作对象,这是博里农民画再生产调动本地农民画创作群体积极性的关键所在。正因如此,博里农民画再生产的本质是对其自身的超越,具体来说,是将其从平面延伸到空间中,从架上渗透到物质空间中。这是博里农民画走向更普遍公共性的必由之路。与此同时,从平面到空间不仅仅是物理上的位移和拓展,还蕴藏着这种空间转换后不同农村社会生产形式及其本质的变化,这种物质性空间与精神性空间辩证统一的形式寓于再生产的过程之中。
三、博里农民画在乡村公共艺术中的再生产
(一)再生产的目的与价值
近年来,在一系列的复杂国际形势之下,“去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共识。这也为我们重新理解“在地性”提供了多维度的参照,也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以开挖“在地性”的方式来丰富文化内涵成为此种复杂局面下的必然策略之一。
当代博里农民画是否还能体现出其发端之初自发、互助的公共性?追溯1958年中国农民画肇始之时,与农民画运动共同发生的还有中国民歌运动,同样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民间艺术运动,它们都基于彼时的社会主义建设语境。博里农民画在经历早期的自主创作后,后期的创作时常围绕奖项展开,甚至逐渐以奖项为目标进行功利性的创作,其表现力、题材和观念都被框定,无法形成自由生长的状态,这实际上与其早期的先锋性相悖。真正有生命力的艺术都是自主发展和主动引导相结合产生的。
除了将农民画置于世界民间艺术的横轴(空间)上进行审视外,我们还需要在纵轴(时间)上对博里农民画进行划分:就传统博里农民画而言,其再生产意味着对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且其是与其他民间艺术类型互相配合的总体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就当代博里农民画而言,其再生产的目的与价值在于融入了适合当前农村经济及文化发展语境的模式,它可以在秉持经济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与传统博里农民画并行发展。通过这两种方式,博里农民画作为公共艺术参与乡村振兴的优势便得以彰显,从而参与重构地方、重构中国乡村生活。
(二)再生产的风格与内容
博里农民画的面貌区别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民画。有研究者曾对博里农民画的艺术风格进行研究,提出了“饱满性构图”这一特征[4]。此外,跨时间线的叙事属性、特殊性的绘画视点,以及现实或超现实景观的叠加,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以潘宇的作品为例,在《农民小世界》中,他采用了并置的手法,使共时性融入了画面之中;在《送宝下乡》中,他综合了俯视、鸟瞰、散点透视和焦点透视等多种视角方式展开画面,恣意烂漫;在《冬季农运会》中,他在博里乡村景观的基础上,完全创作出了一种超越“再现”的想象空间[5]。同时,淮安本地传统文化对于博里农民画的影响,也可以从“在地性”的角度进行理解。例如,在博里农民画家戚海彬、鲍殿顺、沈仕清以及韦志兰等人的创作中,车桥剪纸中的装饰性及负形因素被吸纳。同时,部分作品中撕纸画自由、粗犷的边缘线,也在博里农民画的创作中得到了体现。
当然,上述风格是穿插在不同农民画创作主体的实践中的。我们在对博里农民画进行再生产的过程中,需要继续总结农民画的传统实践方法,同时也需要根据空间变化带来的不同观看、体验方式进行转换。譬如在建筑立面上创作的壁画,需要考虑它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无论是从构图还是颜色的选择上,都需要互相配合。在此基础上,再生产的内容必须与再生产的形式相统一。以潘宇的《春天的歌》(图1)、王德海的《端午赛龙舟》和管建菊的《春耕耙——家乡的回忆》为例,他们所描绘的内容都与博里镇的“在地性”息息相关,强调的是一种传播效果上的直接性与稳定性。与特定的时事相结合的作品在这里反而不如更加普世的议题更能成立。这种内容上的精确选择不仅方便外来者的快速进入,还可以加强创作者群体自身的凝聚力,提升村民对于本地文化的认同感。
(三)再生产的措施与路径
2023年,笔者对博里镇进行了实地考察,看到了博里农民画在乡村公共艺术中的再生产。这可以从博里农民画在乡村物理空间中的参与程度看出。
博里农民画对于乡村整体景观的重新塑造,体现在乡村建筑立面上的农民画壁画创作。例如戚海彬的《中秋明月照水乡》、陈必富的《槽头兴旺》以及沈仕清的《如今度假到农家》等壁画,都将农民画拓展到乡村生活的立面空间中,并与建筑使用者(本地农民)做到了文化属性上的一致性。农民画图像在博里镇生活空间中的介入,其意义不仅是乡村景观表象的变化,景观中的视觉意象还在潜移默化中调动了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农民画以壁画的形态出现,与其在平面画框中的意义大相径庭。壁画实际上成了公共空间本身,其所能产生的影响力自然是不可小觑的。
博里农民画家还利用农民画元素,以雕塑、装置以及建筑小品的形态在各种重要空间节点中实现“点穴”,重新梳理了空间走向,为本地人提供了更多可以进行社交的公共空间,增强了他们的归属感。实际上,在中国传统农村空间中,在不同空间的起承转合处设置景观节点,既可以将不同的血脉聚落连接在一起,又能对不同功能区域进行区分。当然,空间中的农民画因素的点状分布也给外来者提供了良好的导视功能,是外来者快速建立博里镇空间意识的有效方式之一。
博里农民画也直接参与了乡村公共设施的建设,农民画图像在其中反复出现,例如便民设施的亮化(施工围挡的美化)、博里色彩意象的参与(供村民与游客休憩的户外彩色长凳、“彩虹桥”长廊等),以及垃圾桶外壳图像等。这种有用性在生活中被反复测试、反复评价。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一结果对于生产博里农民画相关衍生产品及配套服务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前述农民画再生产的举措也给农民画家提供了一个流动性的展示空间。这些作品在公共空间中的展示加速了这种流动性带来的更新与迭代,从而推动了博里农民画持续不断地自然生长。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农民画的艺术乡建思考
露西·利帕德(Lucy Lippard)曾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地方是一种人类文本,是“自然、文化、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交汇点”,人们站在一个局内人的立场来理解这种地方。她还认为,地方是“从内部看到的土地或城镇或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是对已知和熟悉的特定地方的共鸣……经由人的主观经验所中介的外部世界”[6]。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艺术乡建与其他形式的乡建比起来有什么优势?笔者认为,其最大优势在于其“间接性”可以在“传统-当代”“个人-公共”这些过往被认为是二元对立的概念之间制造缓冲地带,将博里农民画的再生产置于整体的文化语境中审视。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空间生产理论中提出了“差异性空间”理论,认为重构一个空间的关键在于激活其与日益同质化的“抽象空间”之间的对抗[7]。博里农民画再生产的实质就是对“空间-地方”的再生产。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农民画已经不再孤悬于乡村场景。以近些年开始兴起的“大地艺术节”模式为例,其本质是“以文化为主导的系统工程”。我们需要展现的不仅仅是“原汁原味”的乡村空间,而是将乡村置于与城f7a28c9a99d0b457ba85fb8787b9894adbc76d7c06422b727a62903a70ad6ca2市相同的、平行的位置上思考,这也是新时代下城乡融合的必然趋势。
艺术乡建除了追求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外,最重要的诉求是以“软治理”的手段实现乡村的和谐安定,这正符合乡村振兴背景下建设“和美乡村”的新要求。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民间信仰作为中国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含着激励村落意识、激发村落道德实践、整合村落空间秩序和生成村落生活方式的强大力量,在总体上与村落社会的结构特征和村落发展的使命相契合,并在生活实践中互嵌互构,二者构成内在的关联机理”[8]。而在当代,乡村公共艺术将有可能成为替代这一传统乡村文化的文化空间。潘宇曾说:“农民画作品就是感染人,给人以启发,给人以教育意义。过去的农村生活中,打麻将、抽烟、喝酒是很普遍的,很少有人关注当地的文化。这正是乡俗教育缺失的结果。”在潘宇看来,农民画的普及能够起到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在如今的博里镇中,我们能够看到博里农民画家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例如“扫黑除恶农民画”“反腐倡廉农民画”等主题创作层出不穷。这种乡俗教育与蔡元培试图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宗旨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博里农民画为代表的乡村公共艺术,其作用亦是如此:艺术乡建的目的不在于艺术本身,而在于以公共的名义重新定义中国农民的96ae51b189a8e1ef815566d876dd298344ba769c9b2704136f5a6b2d19e16d0e文化身份,以艺术为中介重构中国乡村生活空间。
参考文献:
[1]张道一.中国民间美术辞典[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312.
[2]武定宇.演变与建构:1949年以来的中国公共艺术发展历程研究[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17.
[3]胡绍宗.另类的现代性贡献:中国农民画的文化叙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130-136.
[4]吕艳.淮安博里农民画饱满性构图特征分析[J].装饰,2015(8):107-109.
[5]朱震国.博里农民画集[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8:39.
[6]全美媛.接连不断:特定场域艺术与地方身份[M].张钟葡,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21:130.
[7]刘怀玉.现代性的抽象空间、矛盾空间和差异空间的生产:以黑格尔、马克思、尼采为研究视角[J].国外理论动态,2023(1):58-68.
[8]张祝平.论民间信仰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机理和机制创新[J].学术界,2022(3):73-83.
作者简介:
曾莉,博士,淮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乡建、传统村落。
郭文静,硕士,石家庄市植物园中级工程师。研究方向:风景园林规划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