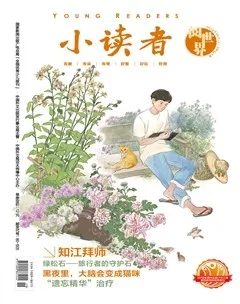知江拜师

越朝城郊走越荒僻,只闻狗吠,越显得人声阒(qù)寂。
深秋的凌晨很有寒意,但知江穿得挺单薄,穿得多了就不方便练功了。
知江走的不是日常脚步,是戏里的“趟马”,剧中人物骑马前行时就用到这种身段。
是探江让女儿这样走路的。这时卖菜的马车还没进城呢,假马不怕被真马撞了。探江是拿科班里的一套训练女儿。
当望江已不能指望自己成为名角跨入响堂时,他将这指望寄托到两个儿子身上。
探江眉清目秀,集中了爹娘相貌的优点。而蘸江相反,把爹娘的缺点加到一起,长成了歪瓜裂枣。
儿子们两三岁时,望江就把他们带来戏班里玩耍。
探江喜欢“扒台帘”,从台帘缝里往台上窥望。
蘸江则对戏箱里的各种行头感兴趣。戏班新排《十八罗汉斗悟空》时,蘸江简直如孙猴子般抓耳挠腮。因为是新戏,许多行头都要班里自己设计制作。要给伏虎罗汉做个圈儿,得拿彩色布条缠上。大家各忙各的,停下来时,没想到六岁的蘸江已把伏虎圈缠好,缠得匀匀称称、像模像样的。
望江就将小儿子送进科班,那个所谓的“六年大狱”。
老师见探江长得唇红齿白,就让他学了旦角。
探江教女儿在街上趟马时,告诉她:“在科班早上练功时,老师会让孩子们每批七个人趟马跑圆场。为什么是七个人,不是六个人,也不是八个人呢?”
知江不吭声,等答案。
“这七个人是梁山七弟兄:晁盖、林冲、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扈三娘。”
知江说:“扈三娘是女的,不能算弟兄。”
“别抬杠,”探江笑道,“那你说该怎么叫,叫‘七姐妹’吗?或者叫‘梁山六弟兄加一个姐妹’,那多别扭!”
知江没词儿了。
探江说:“不管叫什么,科班这样安排是有道理的。七个人分七个行当,七种个性:晁盖是大花脸,要有梁山首领的气概;林冲是武老生,要武中有文;刘唐呢,是架子花脸,要演出暴躁的劲头;阮小二是短打武生,勇中带秀;阮小五是风趣又机灵的武丑;阮小七是勇猛的武二花;扈三娘是柔中有刚的武旦。七个人先按自己的行当跑趟马,跑着跑着,老师一敲锣,立刻大花脸变武老生,武老生变架子花脸,架子花脸变短打武生……这样跑七趟后,各种行当都学到了,以后就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啦。”
知江忽然眼珠一转:“爹。”
“怎么?”
“我忽然想到,如果我是学老旦的,要不要也这样跑趟马?爹,我这可不是抬杠。”
探江承认:“确实,这不算抬杠,学老旦的也得这样。”
知江说:“老旦是演老婆婆的,没有老旦演的武戏吧?”
“不是没有,是你没见过。佘太君你知道吧?”
“知道,杨老令公的夫人,她有武戏吗?”
“有哇,有一出《太君辞朝》,佘太君要扎靠开打。《战太平》里有大将花云,花云的老母亲在《游宫射雕》里也有武打。还有一出《乳母教枪》。你知道梁山一百零八将里有个双枪将吧?”
“双枪将董平。”
“对。《八大锤》里被仇敌金兀术抱走养大的双枪陆文龙,他的双枪就是奶妈教的,那奶妈就是董平的姐姐……”
就这样一边练着,一边聊着,练一会儿,歇一会儿。
知江忽然停步:“爹,你说过,爷爷曾经想知道自己有没有演戏的天分,你看我有吗?天分?”
探江有些沉重地说:“你爷爷没有,我也不像有。我学旦角,年轻时没红起来,现在发胖了就更惨了,但我希望你不一样。天分这个东西很难说。现在最红的旦角梅兰芳,小时候学戏,老师最后都不愿教他了,说:‘祖师爷没赏你饭吃。’老师说他的眼睛不灵活,没法演旦角。梅兰芳后来靠养鸽子,眼睛盯着鸽群转,不是练出一双滴溜溜的比女人还像女人的眼睛?”
忽然传来女子的高叫声,听来似乎有些凄厉:“咦——!啊——!”
探江判断了一下:“是在窑台那边。”
吓得知江不敢往前走了。
探江往叫声传来的方向看,看见一团小小的火光。
“爹?”知江贴着父亲。
那叫声一阵一阵地传来。
探江说:“不是女人的声音……是男人的。跟我一样,是个男旦在喊嗓子。”
“不会吧?”知江不信,“我们来窑台多少次了,没见有别人来这里喊嗓呀。”
探江就将手里的灯笼向那小小火光晃了几下,口中也“咦”“啊”了两声。
叫声停止了。看来小小火光也是一个灯笼,那灯笼也朝着这边晃了几下。
于是父女俩向火光走过去。
果然他们看见一个穿大褂的中年男人。
走近了,探江招呼道:“原来是魏老板。”此人是春霖社的魏少霖,亦是旦行中的翘楚,在演合作戏时探江见过他,不过探江是在台下。应邀演出合作戏的都是名角,所以魏少霖不认识井探江,但魏少霖还是向这位同行点了点头。探江说:“我是云华社的,姓井。魏老板很少来这里吧?”
“第一次来。”魏少霖说,“我一直在中山公园五色土喊嗓,近来那边太闹腾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就躲到这里来了。”
探江问:“五色土怎么闹腾了?”
魏少霖说:“养百灵的人越来越多了,听说最近他们也要选百灵四大名旦,要比个我高你低的,您说我受得了受不了?”
知江这时也不怕陌生了,问魏少霖:“比什么?比叫唤吗?”
“哦,那叫唤的名堂可多了,什么‘家雀闹林’‘群鸡争食’,还有学猫叫,学老鹰叫,一共有十三套,我也记不全。最厉害的叫‘水车子轧狗’,吱吱扭扭的,送水的独轮车来了,很容易轧到躺在路当中的狗。据说要当选百灵四大名旦,百灵不仅要学车和狗的声音,还要学到水车由远到近和由近到远的声音,也算真不容易。”
魏少霖朝附近的坟头扫一眼:“这窑台啊,除了僻静,还有点……怎么说呢,有点亲近的感觉。”
“啊?”知江不明白,“我只觉得挺瘆人呢。刚才远远望见您那灯笼,我还以为是——”
“以为是鬼火吧?”魏少霖笑了,“我师父就葬在这儿。他没儿没女,教戏这点积蓄还不够买一块巴掌大的墓地。后来还是我们这些梨园行的热心肠朋友,集资买下窑台的这块地。前面有座牌坊,刻了四个字,现在看不清,写的是‘梨园义地’。从此以后,没钱买坟的那些孤寡同行,再也不愁死无葬身之地了。对了,小姑娘,刚才那两嗓子,是你喊的吗?”
知江说:“是我爹喊的。”
“你是陪你爹来的吗?”
“不,我爹陪我来的。”
“哦,明白了,”魏少霖点着头,“等我的琴师来了,你能唱一段吗?”
看知江忸怩着不好意思回答,探江赶紧接过话去:“知江,难得能让魏老板指点一下,咱们求之不得呀。”
说完这话,探江转向魏少霖:“魏老板,听您刚才的话,我有几句不中听的言语,不知——”
魏少霖忙道:“请讲请讲。”
探江便说:“我学艺不精,自己的玩意儿是马尾拴豆腐——提不起来的,但我喜欢听人白话(huo)名角们的那些事儿。我听说金少山金三爷在家里养了一些鸟,有蓝靛、红靛、红子什么的,他唱《锁五龙》那段‘见罗成把我牙咬坏’的翻高唱,就是从红子的高音里悟到的。”

魏少霖是何等冰雪聪明,立刻“嗯”了一声。
探江继续说:“程砚秋先生,看上去多么喜静的一个人,偏偏也爱泡电影院。听说有一次他在真光电影院看《凤求凰》,是美国电影呢,硬是把人家梦克唐娜的一首洋歌化到他的《锁麟囊》里,化得就像……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春水无痕。”魏少霖立刻恭敬起来,“请问井先生大名?”
“不敢,贱号探江。”
“那我要称您‘探江兄’。探江兄,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我不该挪地方,留在五色土挺好的。”
探江有些惶恐了:“魏老板,其实小女有幸跟您一起喊嗓是她的造化,可以常得您的指教不是?”
“那好办哪,”魏少霖笑道,“咱们可以一同搬回五色土啊。”
正说着,有个人带着胡琴来了。
魏少霖便向父女俩介绍:“这是我的琴师,名‘秋波’,偏偏他又姓宋。”
知江想起那句成语“暗送秋波”,对爹笑了。
魏少霖把探江的建议对宋秋波说了,宋秋波“啊”地拍了魏少霖一下:“昨天你说要搬来窑台,我没吱声,其实我正在琢磨着一个新腔。你猜这新腔从哪儿悟到的?”
“从百灵的叫唤里吗?”
“百灵十三套里不是有‘紫燕找窝’吗?我觉得可以化成一个新鲜好听的伴奏过门,但还没想好。”
“行,明儿个咱们再去找百灵,你可以接茬儿琢磨你的过门。小姑娘,”魏少霖转向知江,“你叫什么名字?”
“井知江。”
“这名字挺有志气啊,”魏少霖咂摸着,“以一井欲知一江,好。知江啊,你会的戏都是你爹教的?”
“是。”
“你会不会昆的?”
“昆的”指的是昆曲。
知江说:“我爹教过我《思凡》和《游园》。”
魏少霖说:“京戏各个行当都拿昆曲来打底子。京戏旦行中的青衣,以前被人戏称‘抱肚子旦’,一双水袖捂在肚子那儿,坐着可以一唱老半天。昆曲哪有这种事,那是一刻不停地载歌载舞,真正是演戏。知江,你就把《思凡》里那曲《山坡羊》唱给我听听。”
“就是那段‘小尼姑年方二八’?”
“没错。不光傻唱,把身段也带上。”
“成。”
知江便见宋秋波从他的琴袋里取出一支笛子。
魏少霖解释道:“我每天喊嗓都是京的昆的左右开弓。”
宋秋波吹出《山坡羊》,知江便活泼泼地边唱边做:“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父削去了头发……”
魏少霖朝宋秋波指了指,笛声立刻停下,知江也就不唱了。
探江担心地问:“怎么,有毛病?”
魏少霖毫不客气:“有毛病。不过——”
“还有‘不过’?”
“唱法,脸上和身上,都有欠缺,就像枝子有点歪,我知道怎样下剪子。这孩子吭儿不错,是块好材料。”吭儿就是嗓子。
井探江见魏少霖愿收知江于门下,顿时大喜过望:“这块材料在您手上能做成大褂,在我手上兴许就只能做成坎肩儿了。”
魏少霖虽是旦行,却极其豪爽:“接下来就是拜师宴的事了,在哪儿摆,请什么人。多少有出息的孩子,一拜上名师,借的这笔债就不知猴年马月能还清了。除了这顿饭,还得做几身漂亮行头,不能丢师父的人哪。放心吧,孩子,今儿个是师父看上了你,所有开销包在师父身上。要是掉个头,是你死乞白赖地缠着我——”
知江说:“那就该我们借债请客了。”
“那——”魏少霖一撇嘴,“我愿不愿收你还另说呢。”
众人大笑起来。
在这当儿,井知江还没忘了问这句话:“师父,您去响堂演过吧?”
这可是井家的心结呀。
魏少霖反手一枪,问:“你会写字不?”
井探江替女儿回答:“写不好,先生教的是柳体。”
“我是随便一问。请客撒帖子,当然是我来写,谁认识井知江啊?我要请的第一个人就是如今的响堂主人。”
集贤堂号称京城八大饭庄之首,在这里请客最有面子。
集贤堂有戏台,所以又能吃饭又能听戏,嘴巴、耳朵、眼睛都可以不闲着了。
不过一般来说,请客和唱戏的不会是同一伙人,可魏少霖从来喜欢自行其是。当客人们各自坐下,在寻觅主人的身影时,台上开始打通了。
锣鼓家伙热闹了一气,忽然停住,停到所有人都静下来。伙计也被吩咐,只能在打通时上菜,此时便不可走动了。
台上罩着桌围椅帔的一桌一椅本来就摆好的,现在它们浸在柔和的灯光里。
魏少霖扮的小姐和知江扮的丫鬟,在笛声中娉婷地出场,还没开口呢,台下的内行们便在心里嘀咕:《游园惊梦》。
来客在帖子上已经知晓,魏少霖要收的新徒弟叫井知江,但大家没想到的是师徒俩会在拜师宴上粉墨登场。显然魏少霖觉得这个徒弟“拿得出手”。
小姐持折扇,丫鬟持团扇,声声相和,步步相随,把每个瞬间拍摄下来都可以入画。
拜师的日子之所以迟迟未定,是因为魏少霖一定要等到已下不去剪子了才公之于众。
师徒俩只演了较短的《游园》,后面的《惊梦》还要加个小生柳梦梅,就掐掉不演了。他们卸了装,在掌声中回到主桌。知江看到主桌上已坐了一位客人。
魏少霖没跟这位客人打招呼,看来是因为互相很熟就随便一些了。魏少霖没坐下,他对知江说:“你跟我去见见客人们吧。”
知江说:“刚才不是见过了吗?”
魏少霖一愣,随即笑道:“你的意思是在台上已被大家见过了?行,咱梨园行讲究的是‘台上见’,那我去兜一圈。”
“台上见”原来的意思是,双方第一次合作前不用对词儿,不用走台,大家凭本事直接演出。
魏少霖走后,知江大胆地问主桌上的客人:“您就是那位响堂主人吗?”
那客人没来得及回答,旁边桌上另一位客人赶过来:“知江啊,演得不赖呀!”
知江忙叫“大爷”。
原来这就是井蘸江。他在鸾凤社当过管戏箱的箱倌,后来开了个行头铺,把名字改成很霸气的“井占江”,再后来又开起了绸缎庄。
“不过,”占江说,“大爷不是领你到绸缎庄,让你要什么料子随便挑,还给你买了水钻头面,怎么不见你穿戴出来?”
知江说:“师父不让,他说丫鬟穿戴成这样,比小姐还像小姐,这是搅戏。”
“你师父没说错。”旁边的客人插嘴道,“我还见过一个《三堂会审》里的苏三,跪在那儿,面前的小桌子上摆着各种化妆品。两个跟班各背一个茶壶,茶壶上还写了‘茶’和‘参’。她就唱两句扑一下粉,涂一下口红,喝口茶或者参汤。这到底是个判了死罪的犯人还是个阔少奶?第二天她被记者写成文章,这可出名了。”
魏少霖回来后,井占江干脆不走了,他想听些名角逸事好传播传播。
魏少霖给知江介绍主桌客人:“这就是当今的响堂主人,孟雨夕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