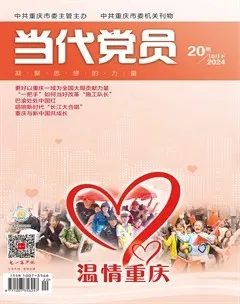名垂宇宙生无忝

我很惭愧,作为一个在四川内江工作过五年多时间的人,先前对张善子先生的认识,居然浅薄得像一张白纸。他出生在内江,虽然我曾附和他人的建议为征集先生的遗物做过一些努力,但终究没有做成一件事。一次集体参观,我才发现,那么多内江籍的名人雕塑居然没有一尊是先生的(连光绪二十一年的状元、进士都有),那么多纪念馆或陈列馆居然没有一座是先生的,那么多展示会、研讨会居然没有一个是先生的,在他的出生地居然没有一席之地是先生的。
我忽然怅然若失,痛上心头。
于是,我花了不小的力气到处找寻资料,从中梳理出先生的“足迹”。于是,我知道了,后人对他的评价居然如此之高:名垂宇宙生无忝。
1940年10月20日,重庆,铅云低垂,凄风寒雨,江水呜咽。
天妒英才,59岁的先生,在位于重庆歌乐山的宽仁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前身)安然作别、与世长辞。
噩耗,像歌乐山的风一样吹散开去、弥漫苍穹;像长江之水一样滚滚东流、流向海洋。一时间,从塞北大漠,到江沪沿海;从华夏大地,到欧美城市,扼腕叹息,哀声一片。
当天,重庆各界人士闻讯纷纷前来吊唁或举行祭奠。从第二天起,国内的报刊,境外的媒体,连续发表各界人士的多篇悼念文章,报道各地的纪念活动。《纽约时报》也在先生离世的第二天刊出长篇文章,报道先生去世的消息,介绍先生的生平业绩。接下来,美国芝加哥、费城、纽约等城市的华人华侨团体,纷纷举行追思会,悼念先生。
1940年11月16日,一场盛大的追悼会在歌乐山举行。各界社会名流或前来吊唁,或送来挽联。12月15日,上海举行追思先生的公祭活动,参加人数达四五百人。追思先生的公祭活动,规模大、规格高、地域广、时间长,仅重庆就超过了三万五千人。
“当代草圣”于右任送来挽联,上书:“名垂宇宙生无忝,气壮山河笔有神。”张治中的挽联几乎概括了先生的后半生:“载誉他邦,画苑千秋正气谱;宣劳为国,艺人一代大风堂。”表达痛切的仁人志士和朋友远不止这些,还有何香凝、郭沫若、田汉、徐悲鸿等等。先生生前和他们往来密切,相处友善。
死后哀荣极备,显然是生前为人不凡。
那就让我们粗略地看看先生的人生轨迹吧!
1898年,也就是先生即将步入成年的这一年,是中国社会的多事之年。这一年,清政府为了筹借第三期对日赔款,与英国、德国签订了《英德续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一千六百万英镑,折合白银一亿多两;这一年,中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德国租借胶州湾,租期九十九年;这一年,继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后,英国要求按照同样条件租借威海卫;这一年,英德订立瓜分天津至镇江等铁路的条约并要求清政府必须满足,之后清政府又与英国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华夏大地,任人宰割、遍体鳞伤。这一年,一些改革图强者发动变法,戊戌变法开始。随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戊戌变法结束。
走完这一年,经历了这些屈辱之事的先生,步入成年人的行列。
1899年,迎来新一年的中国,并没有迎来新的希望和曙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事情也并没有结束。刚刚成年的先生,因不满洋教肆虐,不满官教合流欺侮民众,不满洋货的渗透,参加了后来被史家称为“大足教案”的反洋教活动,踏上了不甘屈服、不愿受辱的抗争之路、斗争之路,拉开了其政治生涯的序幕。
清政府的无能、民众的孱弱、前途的无望,使许多仁人志士开始向海外寻找救国的道路、救国的良方。1905年,24岁的先生,东渡日本留学,入明治大学经济科先学经济,以图经济救国、实业救国,后改学美术,致力于从精神层面唤醒国民。他被“东亚病夫”的侮名压得快要窒息,决定以虎为题材进行艺术创作。虎崇拜是我国民间早有的习俗,可见传统文化对先生的影响。把猛虎入画,先生自有考量,那就是希望国人像虎一样习武强身、强健体魄,抵御外侮。他的正义与激情,很容易找到志同道合者。于是,先生加入了孙中山在日本建立的中国同盟会。1907年先生回国,被选为四川省咨议局议员。
1911年,先生参加四川爆发的保路运动和武装起义,反对昏庸的清政府出卖路权、损害国家和国民利益。辛亥革命后,先生去往南京,跟随黄兴做事,追随孙中山,支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因在辛亥革命中功绩突出,先生被委任为蜀军第一师第二旅少将旅长,也屡建战功,可谓能文能武之精英。
1913年,先生义无反顾率兵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的“二次革命”。遗憾的是,革命并没有成功。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悬赏万金通缉先生,要求捉拿后“就地正法”。
面对先生的奋不顾身,其母亲曾忧心忡忡地说,家中子弟,个个驯良,唯先生嫉恶如仇,又加入革命党,将来难免有抄家之祸。
翌年,为避追捕,先生再次前往日本,潜心钻研绘画艺术。
3年后,先生回国,专心画虎,以虎的威猛和气势,激励国人积极行动起来,增强自信、强健身体,甩掉“东亚病夫”的耻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救亡,先生不辱使命,以艺术家的担当,作巨幅国画《怒吼吧,中国》。画中28只猛虎一齐扑向一轮落日,表达全民抗战的激情和决心,引领艺术界发出发蒙振聩的时代强音。继而先生又作《飞虎图》《火牛破阵图》《正气歌像传》《弦高犒师》《卜式牧羊》等,马不停蹄到各地巡回展览,用自己手中的画笔作武器,满怀激情地参与抗战:以虎的威猛和气势,鼓舞中国人民抗战的斗志。
尤其是先生1937年8月创作的《正气歌像传》,以影响中国历史、气韵高古、能榜样后世的民族英烈作为像传的创作选题,取材之苦心,立意之高远,是发乎其心发乎其志、有其独特情怀的。像传共十四幅,分别是文天祥、齐太史、董狐、张良、苏武、严颜、嵇绍、张巡、颜杲卿、管宁、诸葛亮、祖逖、段秀实等在中华大地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民族圣贤、英雄豪杰。先生意在以此为镜,让中华儿女常“照一照”自己,既是对自己的镜鉴,也是对别人的希望;既是颂扬圣贤大德的传略,也是先生以他们为楷模与民族同呼吸共存亡的艺术表达。
《正气歌像传》当年出版后,在全国各大书店销售,并多次再版再印,发行到抗战前线,甚至传至欧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文学家、艺术家,一位诗书画印样样出众的文化人。他创作的诗词不少于两百首,多是以诗配画形式出现。比如,“落照虞渊惨不红,怒湍谁激大王风?山林尚有歼倭志,奋臂先张射日弓。”再比如,《汉家飞将图》下配诗,“汉家飞将雄,直插倭虏穴。恢复旧神州,四海歌英烈。”等等。
在先生等人的积极倡导下,1938年6月,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在湖北武昌成立,先生任协会主席并被选为首席常务理事。同为理事的有徐悲鸿、吴作人、叶浅予、刘开渠等,名誉理事有蔡元培、冯玉祥、郭沫若、田汉、何香凝等声名显赫的人物。先生提出:“我全国美术界一致联合组织起来,其唯一的目的是在发扬美术的力量,使民族抗战的精神磅礴充实,以打倒侵略中国、扰乱世界和平的日本强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的爱国激情喷薄而出。
同年12月,先生携带一批画作经云南取道越南,到法国、美国。在所到之处,他精心筹办画展进行义卖,为抗战募捐,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赢得各国政府人民的同情和支援。
1939年2月,先生在法国巴黎国家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时任法国总统勒布伦深受感染,亲自前往参观展览,给先生颁授勋章,称先生是“近代东方艺术之杰出代表”。4月,先生到达美国,在纽约、芝加哥、费城、旧金山、波士顿等地举行巡回画展,所得收入悉数寄回中国政府作为赈款。7月,美国宣布废除《美日友好通商条约》,先生挥笔作《虎图》二幅,分别赠送给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把自己这个“民间外交家”的智慧和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罗斯福总统夫人曾几次开车迎接先生到白宫欢宴致谢,《华盛顿邮报》对此做了详细报道。
在美期间,先生一有空就创作,然后将作品卖出,把钱寄回国内用于抗日。有人不理解,他却说,多卖出一张画,就多一颗射向敌人的子弹,对一份支援国家抗战的力量。
先生不辞劳苦,到欧美一些大学和华人团体进行演讲,宣传抗日。所到之处,常有人竖起大拇指,表示对先生的友善和尊重。
1940年9月初,先生动身回国,回国前将义卖、展览门票及募捐所得及时汇回国内作抗战经费,多达二十万美金。涓滴归公,不入私囊,而自己节衣缩食、节俭无比,食不求精、衣着朴素,扣子掉了都是自己缝。到达香港后,先生竟然囊中空空,无返渝资金。在朋友的帮助下,先生10月4日才抵达重庆。
一到重庆,先生就赢得整座城市的迎候,汇报、演讲、座谈、交流……先生十分繁忙,疲惫不堪。
旧疾未除,又添新劳。在家人和朋友的劝说下,先生住进了宽仁医院。不幸的是,10月20日,先生竟溘然长逝。
呜呼,先生何人?风云军政两界,驰骋海内海外,为国为民甘洒热血,是文坛艺坛一代圭表的“虎痴”张善子也!
1882年,先生生于四川内江的一个普通家庭,名正兰,字善子。父亲张忠发,通文识字,做过小生意,但终究未成大业,最终靠劳力谋生。母亲曾友贞,普通家庭妇女,喜读书爱画画,顶多算一个小知识分子。先生有十个兄弟、两个妹妹,自己排行老二,赫赫有名的张大千是其八弟。
我很早就知道,陈纳德将军组建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名为“飞虎队”。先生和陈纳德将军过从甚密,早在将军准备来华前,就以《飞虎图》相赠,画面是两只长有翅膀的老虎,祝愿将军的队伍如虎添翼、所向无敌。相传,因此画,将军将飞行队更名为“飞虎队”。
在整理和研究先生方面,学者汪毅功不可没。他认为先生拥有若干的“第一”,我认为这一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这是他严谨地总结提炼出来的。
在内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如果要找出作为榜样影响了当代、影响了后世的名人,一定少不了先生,且他应属首屈一指。
作为一名曾在内江工作过的人,我是惭愧的。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应该为此写一点东西,好让更多的人了解先生,也好让我的愧疚心稍稍有所解压。我认为,内江即使人口密度再大再拥挤,也应该给先生留出一席之地,以昭示敬仰之情。
由此,我想到曾工作居住过十多年的四川绵阳。那些年,我去富乐山时,经常要去富乐山酒店大门外的一个八角亭转一转,这是为了纪念宋哲元这位爱国将领而修建的,如今这里已是富乐山公园的一部分。宋哲元不是绵阳人,但病逝于绵阳,被绵阳人厚礼安葬在富乐山。后人在纪念瞻仰宋哲元的同时,也能感受绵阳人的深情厚谊、广阔胸襟。
我也在想,如果先生安于创作,或许不会英年早逝,先生的生活也会很滋润。但是,先生作出了另外的选择,走上了另外的道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能从他给弟弟张目寒的信中找到答案。
“丈夫值此时会应国而忘家。此次我来郎溪,生平收藏存苏州网师园皆弃之如土,以今日第一事为救国家于危亡。万一国家不保,则虽富拥百城又将何用?恨我非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今将以我之画笔写我忠愤,鼓荡志士,为海内艺苑同人倡。”
在这条不平坦又充满荆棘和艰辛的革命之路上,先生虽然生命短暂,但一生光辉灿烂,令人无比感动、无比敬佩,永远照耀后人。
还有一件事,我不能不提。
1926年3月,45岁的先生赴察哈尔省(现已划归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北京市),先后担任丰镇、兴和、凉城等地土地清丈局局长,察哈尔造币厂总务科科长,商都县县长。这些地方,至今都和我的老家同属乌兰察布市,离我的家很近很近。其实,这件事,我不是今天才知道。我在内江工作期间,商都的一位领导就和我说起过此事,并希望我能觅得一些先生的照片、遗物,包括仿制的作品之类的东西,拿回去以资纪念和缅怀先生的这段人生、这段经历。事实上,先生在商都任县长只有3个月时间,为此他创作了“三月商都令”印鉴以自嘲。但我同样什么也不曾做。今天想来,我家乡的官员实在是比我有情怀、有远见得多。以至于到今天我又多了一份额外的惭愧。
后人的回忆文章,多有这样的表述:“先生仪表从容,有谦谦君子之风;秉性豪侠,有大侠魂之风度。其民族正气之修养,洵足为现代国人之楷范”,“诚可谓中华民族之大侠魂”。这是先生留给后人的鲜明印记。
先生是中国抗战时期情感投入、表现出色、贡献伟大、影响广泛的画家。在先生的身上体现最充分的是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他影响力很大的作品《二十八忠孝故事图》,就是取材中国古代二十八位贤良忠孝人士的故事加工创作而成,意在宣扬中华民族的忠孝思想。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至今,他依然是艺苑钜子、圭表、楷模。
《正气歌》里有“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一句。在处境危难时,人的气节才能显现出来。《正气歌像传》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危难的考验的,先生亦复如是。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极其残暴,以惨绝人寰的手段对待中国人民,企图以屠杀和死亡让中国人民屈服。面对侵略者的屠刀,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人人抱定必死之心,成千上万的英雄们,在侵略者的炮火中奋勇前进,在侵略者的屠刀下英勇就义,彰显出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我想,在成千上万的英雄中,先生一定是闪亮的一员。
此外,先生在艺苑树起的“精神标高加艺术标高”,也是我们不能忘却、应予纪念的理由吧。
侯志明,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曾参与制作影视作品《天上的菊美》《邓小平遗物故事》《绝代芳华》等,出版有散文集《行走的达兰喀喇》《少点精致的俗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