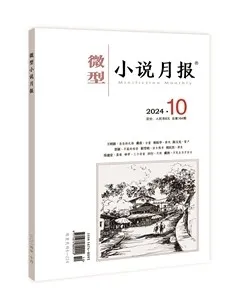二两肉
二两家有头骆驼,四喇叭沟方圆几里就他家有一头。
听二两说,这是一年前的事了,过年出门运货几天,回来就见家里趴着头骆驼,嘴角还有被咬断的门闩的木屑。他问了一圈,没人知道这骆驼是哪儿来的,没人会养,也养不起。
“俺爹娘走得早,只当留下骆驼来陪俺,有点念想不是。”旁人问起,二两总这样答。
骆驼耐旱,听话得很,给啥吃啥,让干啥就干啥,只是瘸了一条后腿,走路不利索。大西北天干物燥,除了沙子就是沙子,驼峰上的毛也不太光溜,二两就找了点别人不要的破木头盖了棚子,拿家里仅有的一点水给骆驼擦了擦身上。
这事被同村六伢子知道了,抓着二两后脖颈就是一顿骂:“人都没吃喝,给一个畜生洗毛!等你哪天渴死了,你看它谢谢你不!”六伢子的口水差点溅进二两眼睛里,二两没说啥,笑着躲开了。
二两真名李二顺,平时人好得跟没心眼似的,大家都说他“心里没二两数”,久而久之,这外号就叫开了。
一晃两三年过去,本就黄土漫天的大西北,迎来了三年旱灾,人人过着“嘴啃树皮,沙子当水喝”的日子。日光无情,大地被撕成残缺不全的碎片,只等老天爷赏点水。
六伢子动了吃骆驼的心思,跟村里几个有根基的人家一合计,天一亮,抄了家伙风风火火地往二两家赶。
“驼峰里全是水,拉两刀让大家解解渴!”
“咱把骆驼吃了吧,反正也不一定养活,早晚都得死!”
“你是要全村人的命,还是要骆驼的命!”
二两怒视着准备围剿骆驼的村民,两条黝黑细瘦的胳膊死死抱住骆驼的脖颈,眼底猩红,不退半步。
双拳难敌四手,村民们拉不开二两,便一哄而上对骆驼下手,硬是割掉了一个驼峰,好几双拿碗的手去接,等了半天,只有血水混合着黄色的脂肪汩汩地流,没有一滴水。
不知骆驼是哑了,还是认命了,一声不吭地任由众人推搡,骆驼血在本就狭小的小院里蜿蜒成河,身旁护得最紧的,还是二两。
有人一把夺过被割掉的驼峰,举起来说要煮熟这二两肉给大家分分,人群闹哄过后,就散了。
二两从骆驼身上爬起来,抬头望了望日头,日光依旧烫得无边无际。他扯了扯双唇,又落下,最终还是嗫嚅道:“爹、娘,这些年,咱这院里还是头一次这么热闹嘞……”
趁着夜深,二两用家里唯一的床单裹住骆驼背上的伤口,一人一驼走了十多里路。从伸手不见五指走到了天蒙蒙亮,也不知走到哪里,不知身在何处,直到二两再也走不动了。
“你走吧,俺对不住你,六伢子说得对,也不知你能活到啥时候,我较这劲干啥嘞,你莫回头,莫回头。”
胳膊上还有风干的骆驼血,混合着汗液,有点腥。二两擦了擦,抹不掉,又给骆驼擦了擦脸,指尖有一点湿湿的东西,借着月光细瞧,是眼泪。
想到这里,二两没再回头,旷野的风烈,饶是硬朗汉子,也一吹就干。他解开了骆驼的缰绳,看着骆驼消失在夜色里,一边掉头走,一边响亮地唱着爹教给自己的那首歌: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哦,
三盏盏的那个灯!
哎呀戴上的那个铃子哟,
噢哇哇的那个声!
从那以后,四喇叭沟再没人见过二两,只多了一个不知从哪儿来的瓜娃子,老穿一身露棉花的破袄,黑黝黝的脸看不清五官,总爱捡一些枯草插头发。逢人就说自己叫“骆驼”,模仿骆驼跑起来时驼峰摇摆的模样,嘴里嘟囔着“哪里都没水,骆驼更没有”,累了就痴痴地望着天上的日头。
当年分了“二两肉”的人,在几个月内都得热病死了,有人说得的是“骆驼病”,也不知真假。
选自《小小说月刊》
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