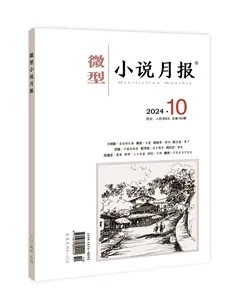请戏
梅山峡外的大晒场突然搭上了戏台。
闹台鼓响过第一回。大鼓小钹声声响,穿入百米外的梅山峡口,钻进峡内三开门三进又三重的梅山峡大屋。九岁的阿娇踮着小脚,听畈上传进来的闹台鼓响,心似猴爪挠过,边侧耳往外听,边蹬着脚尖往门隙的油坊里瞧。
阿娇是袁家抱来的童养媳。她的小丈夫叫平清,今年六岁。
门里的婆婆梅枝也踮着小脚,她在清点山茶桃。
霜降过后,袁家的长工短工都派去了茶园,十三个人忙活了大半个月,山茶桃断断续续塞满大屋里的榨油坊。
请戏是公公太钱临时决定的。婆婆梅枝为此埋怨了几句,太钱瞪着牛眼骂:“你个苕婆娘懂么子事?照办就是!”一旁的阿娇吓得连呼吸都缩了回去。
太钱昨日去了趟长滩街,回来后就一直阴着脸,见人骂人,见鸡撵鸡。
太钱幼时得了一种叫“走马干”的怪病,鼻黏膜发炎后,一直化脓不断,去汉口寻了大夫都没用。鼻子腐烂的地方直延伸到上嘴唇,病好后,鼻翼和上嘴唇虫噬般各缺了半块。他平素极少出门。每个月去长滩街兑票,总以一块青布遮着口鼻。
那日,刚从山上返回的太钱,琢磨着兑票的时日到了,想着从梅山峡去长滩街也不远,便衣服没换鞋没换,顺手扯了只旧竹篓背出了门。在找管账的大先生之前,他临时决定往长滩的东大街走走。
在袁家屠铺前,他停下来。刚刚忙完的屠夫,看着眼前瘦眉窄骨的老头,只见他脚趿一双破草鞋,凌乱的小辫歪盘在后脑上,眼下罩块青布,风一吹,便露出鼻子下的一大坨麻花豁口。屠夫怜悯心突起,随手拣了一块卖剩的下水肉扔给太钱:“喏,赏你块肉吃。”
太钱的脸当即涨成了猪肝色:“把你管事的请来!”
屠夫一听来了气:“你爱吃不吃,送你的,还嫌肥拣瘦。请管事?我呸!我家大先生在水楼听戏呢,岂是你说请就能请的?”屠夫一把将肉夺回。
太钱气得直跺脚,吼了一声:“没耳朵吗?是不是不想干了?马上把你们管事的叫来!”
屠夫一怔,嘴里仍喃喃:“你一要饭的臭老头,我好心赏你一块肉,还这么不识好歹。”
太钱一把就掀了肉案。
大先生听说有人在闹事,怒目从戏楼冲出来。他一见太钱,脸上立时堆起笑,扯了扯屠夫齐作揖:“大东家,不知者莫怪,您不常露脸,大家伙都不认识您哩。”
“好,好一个不常露脸。那我让大家伙认识认识。通知一声,明日让掌柜们来梅山峡听戏!”太钱背着他的竹篓,趿着草鞋,阴着脸回了梅山峡。
闹台鼓响过第二回,梅枝出来了。门口的轿已备好,四个长工临时充当轿夫,轿是竹制的,平顶黑油齐头轿,左右是青皮篾编成的牖,轿门处坠了一道红丝绒的帷帐。阿娇努努嘴:“娘,从峡内到畈上,两百米不到也坐轿?”
梅枝斜瞥了阿娇一眼:“不想看戏,就在屋里待着,看家。”阿娇吓得不敢吱声了。她缩着小脖,悄悄地跟在轿子后往大屋场走。
闹台鼓响过第三回,袁家大屋场密密麻麻挤满了人。梅枝的轿子刚落,账房大先生哈着腰凑上前搀着她去了上席。
花鼓戏三打闹台戏开场。三打闹之后,戏台却没有半点要开场的迹象,倒是一声接一声的锣声鼓响大钹声木鱼声响彻大屋场。戏台下摆满席面,桌上的茶水果品糕点没人去动,几十位掌柜分两列站着,一律的青衣长马褂。肉铺的屠夫后背冷汗直淌,他不安地望着上席正中那张空椅。来时大先生可是说了,大东家要是不原谅,肉铺的营生就得收回。
戏台静了,仍旧是草鞋声先响,一个瘦瘦的身影挑着山茶桃走来。放下扁担的太钱松开罩在脸上的青布,抖抖前襟的草屑,抬手压下几次欲言又止的大先生,也没看一脸惊恐的屠夫。他手执青布擦了擦额上的汗,对梅枝笑:“今日把后山又搜了一遍,算上我这担桃,今年的山茶几多?”
梅枝翻开账本答:“六百九十一担。”
太钱点了点头,转头问大先生:“竹坊呢?”
大先生手捧账簿上前,不料一脚踩空跌在地,话却没半点耽搁:“回东家,本月竹板十万块,竹席一万床……”
太钱点了点头,朝两旁茶庄米铺饭馆裁缝铺的掌柜们道了声:“我叫袁太钱,劳大家受累了。”又朝阿娇招招手:“丫头,去让班主开《合银牌》,大家等着哩——”
清光绪三年(1877)冬日。
原本热热闹闹的长滩东大街,十铺九关,近百家铺门统一置了块小牌,上书“大东家请戏,今日休市”。去而复返的人,空手等待的人,全拢在一处。人一多,闲话来了。知情人说:“这人哪,不能以貌取人。”“是呢,凡事还得有个规矩,越线就不好哩。”“可不是嘛!多少人的饭碗呢。”
可不是嘛,多少人家的生计哩!
选自《芒种》
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