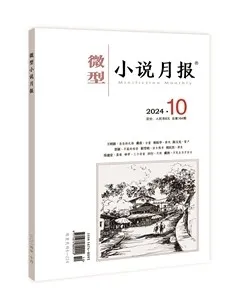伞
小时候我们家里穷,穷到什么样呢?这么说吧,翻遍祖宅连一把像样的伞都没有。
记得那时,每次下雨,父亲都用一条麻袋,把底上的两个角对着套进去,再一拉一拽,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雨披,虽然实用,样子却很难看,有点像东北扣酱缸用的酱帽子。给我的,则是用小一号的化肥袋子依样做成的。
那时上学放学,一般父亲是不接送我的,可是雨天不行,他也怕我有什么不测,所以就带上这样的装备,守在校门口。说句实在话,这让我很是难堪,我总是觉得我们更像是两只鹌鹑,一大一小,在狂风暴雨和雷电的恐吓声中瑟瑟发抖。
终于有一天,我发起脾气,对父亲说:“如果你不能真的带一把伞,就不要到学校来接我了。你知道同学们都在嘲笑我吗?笑我们丑陋,说我是秃尾巴老李。为什么别的家长都可以带一把好看的雨伞来学校,而你却不能?”
父亲沉默了。他没有向我解释家里因为我母亲的多病和祖上的贫穷而一无所有。其实这些我也是知道的,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体弱多病,常听说的就有冠心病、高血压、胃溃疡等,要经常去省城的医院做检查,这当然是要花钱的。至于祖上的事,据说当年因为我母亲和祖母不和,终日吵闹不休,致使在分家时,父亲和母亲只从祖父母家拿了两副碗筷,便算是祖传的了。
父亲从不和我谈起这些往事,对我的要求他只是沉默地点点头,算是答应了我。后来我们家就有了一把伞,这是一把旧伞,黑色的油纸面,磨得有些发秃的伞柄早就脱了色,上面的骨架也断了一两根,虽然父亲修理过,可撑起来时上面还是有些凹凸不平。我也不知道这伞是哪里来的,不过比起麻袋和化肥袋子强多了。
从那以后,一到下雨天,父亲就拿着那把褪了色的伞到学校门口接我。放学的铃声一响,同学们便叽叽喳喳地冲出去,我也高兴地冲到父亲身边,一路上和父亲有说有笑。父亲举着伞,我依在父亲腋下,雨水一点也进不来。也是从那天起,我特许了父亲不下雨的时候也可以来接我,并且还特意叮嘱他一定要带上伞,可以遮挡一下阳光。回家的路上,我撒着娇让父亲背着我,于是,父亲就背着我,我撑着伞,一高一矮,我们都在那伞的阴凉之下。那时,我觉得那伞好大好大,仿佛整个世界都装得下。
时光匆匆如流水,转眼已是多少年,父亲已故去,连我自己的孩子也上了小学。如今的生活条件早已非昔日可比,农村的孩子也同样要大人们每天接送,我自然也不能懈怠。
那天,放学时间来临之际,忽然飘过一片云,下起雨来。妻子偏此时不在家,我干着急也找不到伞。愤怒之余,我边翻边嘟囔:“成天到晚瞎收拾,用的时候找不到,不用的时候倒是在眼前晃,这会儿人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可是,我说什么也没有用。最后,我在堂屋的旧箱子里翻到了当年父亲接我时的那把旧纸伞,别无选择,带着伞匆匆忙忙去了学校。
一路无语,回来时,雨却越下越大,还夹杂着久违的东风,一阵强似一阵。我左挡右堵,弄得手忙脚乱,还是不行,索性效仿当年的父亲,把孩子扛上肩,让他打着伞,可是即便如此,还是顾不过来,我和孩子都被雨水淋湿了大半边。
此时此刻,我忽然想起父亲,不免心头一阵酸楚:这伞真的好小好小,容不下一点点感伤……
选自《红山晚报》
2024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