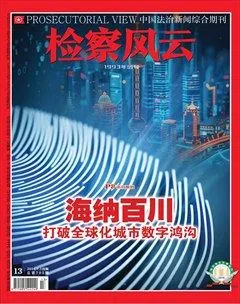投标失利引发的人情费官司

介绍工程项目但未中标
赵某与何某系朋友关系,何某常年经营废品回收企业,具有一定的废旧设备回收经验。2021年12月初,何某告知赵某,河北沧州某公司有淘汰设备要转让,但自己没能力接手,问赵某是否有兴趣。赵某提出,何某可带其到现场看看。
2021年12月9日,赵某在何某陪同下赶赴河北沧州现场察看后,决定以江苏华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公司”)名义参与投标。12日,华某公司授权委托赵某,以该公司名义参与该供电设施拆除转售项目(以下简称“案涉项目”)的投标,并处理一切事务。
赵某决定让何某负责案涉项目的前期接洽,并向何某转账30万元。双方在微信中约定:由何某负责以华某公司名义投标,由赵某负责提供资金及安排作业。
在后来对簿公堂时,双方对于赵某转给何某的这30万元的用途产生争议。赵某认为何某相当于中介,该款系交给何某的“诚意金”;何某则认为,这30万元系赵某基于他们之间的委托关系预付的“委托报酬”,其中包含了何某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可能支出的相关费用。
何某向案外人钱某转账20万元,关于其用途,何某称系“做人情”。何某接受赵某委托后,曾多次前往沧州参与项目的前期调研、磋商谈判和价格交涉等事宜。2022年1月6日,赵某和何某因该项目招标再次一同前往沧州,结果事与愿违——该批设备被广州某公司以更高的价格收购。
2022年1月13日,赵某要求何某返还30万元。何某对赵某表示,自己在参与投标过程中花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带助理多次前往沧州,不仅奔波劳累,还垫付了所有花销,累计已超过30万元。因此,他拒绝向赵某返还该款项。
2022年5月26日,赵某以何某为被告,向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令何某向其返还30万元,并按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支付相应的逾期还款违约金。
武进区法院经审理,认定原、被告之间系中介合同关系,被告向原告提供案涉项目的信息并积极推动投标。后因投标失利,被告的中介工作未达成预期目的。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返还已支付的案涉款项,但被告在此过程中实际支付的有关费用(酌定20982元)应予以扣除。
2022年10月17日,武进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何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赵某279018元。
预付款应否返还
一审宣判后,何某不服,于2023年1月4日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赵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在常州中院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围绕案涉30万元的性质及应否返还展开辩论。
何某认为,双方之间系委托关系,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中介关系。中介关系与委托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受托人对项目的介入程度,以及受托人是否享有一定的决策权。本案有关书证可以证明,不仅何某向赵某提供了订立合同的机会以及媒介服务,而且赵某在认可案涉项目的可行性后,将签约事宜全权交由何某负责。因此,双方之间已经超出了中介关系的界限,属于委托关系。
何某表示,即便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双方为中介关系,赵某也无权要求其将30万元全部返还。其中20万元项目启动金实为“请托费用”,已转至案外人账户,赵某对此是知情的,未提出异议,说明他默认了何某对该笔资金的使用权。
何某还指出,一审法院将其已实际支出的烟酒茶叶等认定为应酬开支,且未予扣除。应酬开支的目的是促进案涉项目谈判,属于必要费用,在商业风险范围内。若不予以扣除,就相当于将商业风险全部转嫁给了何某,这明显有违公平原则。
赵某辩称,双方之间为中介关系。是何某主动找其提供有关案涉项目的信息,并参与其中,试图促成交易。赵某与何某的微信交流中,并无明确的授权委托信息,也未将何某明确列为被授权人,对此何某是明知的。因此,双方之间并无委托关系的基础。
赵某认为,何某在本案中的行为特征与中介合同之“报告订立合同机会、提供订立合同媒介服务”一致。案涉款项是“诚意金”和预付款。何某提交的所谓支出费用凭证,显示都是其单方认定和擅自使用的,未经赵某同意,甚至未告知赵某,其用途也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
二审认定委托违法
常州中院将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归纳为:何某与赵某之间成立的合同关系的性质、效力及相应的法律后果。
关于何某与赵某之间成立的合同关系的性质。相关证据表明,案涉项目主要由何某出面洽谈及投标,何某在案涉合同中的义务,并不仅局限于向赵某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实质上,何某是接受赵某的委托处理其事务,该行为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故本案应为委托合同纠纷,而非中介合同纠纷。
关于案涉委托合同的效力。本案中,何某向赵某发送微信“我要到银行预约提取现金”。赵某在向何某转账30万元后,回复“谨慎做事,原则性问题把握好”,还表示“如何使用,与我无关”。何某则向赵某保证,“我在该项目上有关系,绝对可靠”。据此综合判断,赵某应当知道其委托事项以及给付款项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因相信何某在案涉项目上“有关系”,才向其转账30万元,以期中标案涉项目。赵某的这一转账行为属于“不法原因给付”,其委托行为及给付行为均违法,故赵某与何某之间基于该不法目的订立的委托合同无效。
关于案涉委托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本案中,赵某企图通过“走关系”的方式获得案涉项目,在投标失利后依据无效委托合同起诉。这一行为应认定为滥用民事权利,其并不享有合法债权。
综上,案涉30万元系不法的、无效的民事行为支出,赵某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2023年3月31日,常州中院作出二审判决:撤销一审民事判决;驳回赵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文中企业名及人名均为化名,本文谢绝转载)
编辑:姚志刚 winter-yao@163.com
法官点评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中介合同与委托合同的本质区别在于中介人与受托人的法律地位不同。中介合同中,中介人只能如实传达双方的意思表示,不介入委托人与第三人所签订的合同关系,处于中介服务的“中间人”地位;委托合同中的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务时,有权在委托权限范围内独立进行意思表示。
“不法原因给付”是指当事人基于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序良俗的原因而为之给付。《招标投标法》第5条规定:“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这一规定对招投标活动中通过“走关系”的方式中标的行为给予了否定性评价。本案中,赵某给付何某30万元的行为属于“不法原因给付”,应给予否定性评价。
一般情况下,合同被认定无效后,一方通过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另一方。但该法条中有“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内容,且《民法典》第132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本案中,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因违法而被认定为无效,且案涉给付30万元的行为被认定为“不法原因给付”。二审法院改判驳回赵某的诉讼请求,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