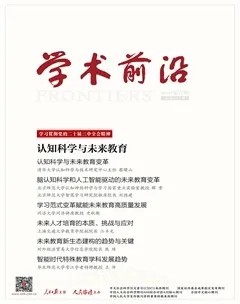认知科学与未来教育变革
【摘要】中国认知科学的三个发展阶段是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而认知科学时代的人才培养要通过教育变革来实现,为此要重新认识和定义教育。未来教育应坚持知识和能力并重,更加重视心智和认知能力的培养。通过建立人类认知五层级与教育发展各阶段的对应关系,可以重新制定教育发展各阶段的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提高学生和受教育者各个层级的心智和认知能力,这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在认知-教育的视域下,应围绕“6+1”的学科框架,聚焦综合认知能力的提升,深化高校育人模式改革,培养21世纪的“大师”和“杰出人才”。此即认知科学时代对 “钱学森之问”的回答。
【关键词】知识 能力 认知科学 未来教育 心智
【中图分类号】B842/TB1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6.020
导言:中国认知科学的三个发展阶段
以清华大学认知科学团队的建立为标志,20多年来中国的认知科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科学研究,明确认知科学的研究对象、科学结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其间,笔者创立了心智进化论和人类认知五层级理论,使认知科学从交叉学科转变为单一学科。[1]
第二阶段是学科建设,创立认知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2019年),创立语言与认知、逻辑与认知、民族文化与认知等研究生专业(2016年~2019年),设置相关课程、建立培养方案,学科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据统计,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有130多所高校开设了认知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为进一步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扩宽就业路径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第三阶段是实践应用,主要目标是人才培养,因为认知科学说到底是关于人的科学。21世纪是综合的时代,这个时代教育的使命是通过认知科学与教育变革,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综合性人才。[2]作为以人类心智和认知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认知科学所关注的是人类的命运,通过认知科学实现新世纪的教育变革是认知科学的使命。21世纪以来,教育学已经被纳入认知科学的来源学科,从而形成“6+1”的学科框架(如图1所示),并形成聚合科技(NBIC)这一更大的学科综合体。从综合到更大的综合,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方向。认知科学正在对未来教育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教育变革的时代正在到来!
本文从知识和能力这一对基本的教育范畴入手,深入分析认知科学对未来教育的影响以及可能引起的教育变革。在新的时代,应该用认知科学重新定义教育,重新认识教育的使命,从人类认知的五个层级来提高人的心智和认知能力,以期在认知科学时代培养出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并最终解答“钱学森之问”。
知识和能力
什么是知识。“知识”一词由“知”和“识”二字组成,这两个字本身也是汉字语词。《说文解字》对“知”的解释是:“知,词也,从口,从矢。”[3]这里,“矢”指“射箭”,“口”指“说话”。“知”是“矢”与“口”的结合,表示“说话要像射箭命中靶心”,即“一语中的”,表示话说得很准。例如,18世纪英国天文学家哈雷(E. Halley)声称掌握了一颗彗星的运行规律,并预测这颗彗星将于1759年重新出现。1759年1月21日,人们果然又一次看到这颗彗星,哈雷的预言得到证实,该彗星被命名为哈雷彗星。哈雷预测得很准,这就是“知”。“知”通“智”,“智”即“心智”,而“知”的行为需要通过心智。“知识”的“识”,繁体写作“識”,《说文解字》对“識”的解释是:“常也,一曰知也,从言,从戠。”对“戠”的解释则是:“从戈,从音。”[4]“戠”本指古代军队的方阵操练。“音”指教官口令声,“戈”指参加操演的军人的武器。随着教官指令,军阵会变换各种队形,观看者则会看到各种整齐的图形。因此,“戠”的本义是“规则图形及其变换”。凡从“戠”之字皆从此义,如“織”“幟”“職”都有“图形”“图案”之意。“識”的本义是用语言描述图形、图案的形状和细节,引申义为区别、辨别。总结起来,“知识(知識)”的意义是:“准确地说,认真地看和理解”。
距今2500多年前的孔子(前551年~前479年)时代,“知”和“识”是两个词,是分开使用的。儒家经典《论语》21000多字,“知”出现117次之多,“识”只有6次,“知识”无一次出现,说明那个时代并无“知识”一词。
《论语》中为人所熟知的有关“知”的表述包括: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第一》)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第二》)
以上“知”的语义是知道、了解、理解。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一句中,最后一个“知”通“智”。意思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智慧啊!”
《论语》中“识”仅出现6次,如: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第七》)子曰:“赐也,如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第十七》)
以上“识”的语义是认识、见识、识别,更接近于“知识”的“识”。
《论语》中,“知”和“识”同时出现,而且将二者加以对比的,仅有1处: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则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第七》)孔子说:“确有那种无知而行动之人,但我不是这种人。要增加自己的见闻,这样才能择其善者而从之,见多识广,求知是次要的。”
这段话充分表明了“知”和“识”的联系与区别。区别是这种见识是通过学习获得的还是通过实践获得的。通过学习获得的见解叫“知”,通过实践获得的见解叫“识”。如果将二者联系起来就会得到一个新词或一个新概念,这就是“知识”,彼时这一新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孔子对概念的辨析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是同时期的西方语言学家和哲学家都无法企及的。黑格尔(G. W. F. Hegel)认为孔子的思想并未体现出“思辨的哲学”,这在笔者看来是无知甚至愚蠢的。[5]
“知识”一词的正式使用,见于比孔子晚三代的另一位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前476年~前390年)的言论。《墨子·号令》曰:“其有知识兄弟欲见之,为召,勿令入里巷中。”这里的“知识”指相知相识的友人。汉代以后“知识”一词已经普遍使用了。孔融在《论盛孝章书》中写道:“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白居易在《感逝寄远》一诗中写道:“昨日闻甲死,今朝闻乙死。知识三分中,二分化为鬼。”孔融和白居易二人所言的“知识”也是指相知相识的友人。刘向《列女传·齐管妾婧》曰:“人已语君矣,君不知识邪?”薛用弱《集异记·汪凤》曰:“每面各有朱记七窠,文若谬篆,而又屈曲勾连,不可知识。”刘向、薛用弱二人所言的“知识”意为了解、辨识。焦竑《焦氏笔乘·读孟子》曰:“孩提之童,则知识生,混沌凿矣。”这里的“知识”是指一种认识能力,这已经和现代的知识意义基本相同了。
《现代汉语词典》中“知识”有两个义项:(1)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2)指学术、文化或学问。第一个义项比较接近《说文解字》和《论语》中“识”的意义,即通过实践获得的认识,但却缺少“知”的意义,即通过语言和学习所获得的认识。更进一步说,以上定义尚不能体现当代认知科学对知识的理解,更无法有效诠释知识和能力的联系。
人类的知识体系。知识是一种认识和理论体系,而不是个体的零散的认识。古希腊的“三科四艺”(three subjects and four arts)是人类最早的知识体系。如表1所示,人类最早的知识体系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学科(subjects),古希腊人认为人类最重要的知识体现为三个学科:语言、逻辑和修辞,这三个基础学科都是与人类语言相关的。语言学教我们如何说话,逻辑学教我们如何正确说话,修辞学教我们如何把话说好、说生动,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语言和思想的沟通。语言、逻辑和修辞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稍后的认知科学五层级理论中会看得更加清楚。第二部分是技艺(arts)即基本技能,古希腊人认为人类最重要的四种基本技能是算术、天文、几何和音乐。
在欧美(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教育传统中,“三科四艺”一直被当作完善人格的基本途径,是基本且重要的认知方法。公元9世纪末,欧洲开始出现第一批大学,如法国的巴黎第一大学(前身为巴黎索邦神学院)、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被誉为“大学之母”,开设语法学、逻辑学、修辞学和法学课程)、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到12世纪,西方著名大学已经达到18所之多,“三科四艺”被列为基本课程。
从这一分类可知,第一,人类知识是形成体系的学科知识和技能,知识被等同于学科知识;第二,大学的出现强化了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学习,现代大学则遵循了完全的分科教育。
20世纪是分析的时代。通过现代教育体制强化的学科教育,人类知识被切分成学科知识,形成“学科门类十几个,一级学科几十个,二级学科几百个,三级学科几千个”的学科体系,[6]掌握综合性人类知识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寥若晨星。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美、英、德、日等国的学科划分,笔者整理并搭建了四部十二门学科结构(见表2),[7]这就是当代的人类知识体系。
如表2所示,最大的学科部类分别为第I部类理学、第II部类工程技术、第III部类艺术人文、第IV部类社会科学。这4个部类的不同组合形成了自然科学(第I部类+第II部类)、人文社会科学(第III部类+第IV部类),等等。其中,下面部类是上面部类的基础,上面部类是下面部类的应用。例如,理学是工程技术和整个自然科学的基础,工程技术是理学的应用。类似地,艺术人文是社会科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社会科学是艺术人文的应用。最值得注意的是第I部类+第III部类这个组合,它有一个优美传神的英文名称:Liberal Arts,直译为“自由技艺”,意指人类获得自由必备的知识。它是自然科学之基础理学和社会科学之基础艺术人文学科的组合,既是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也是现代大学的基础。[8]
对表2所示的人类知识体系即四部十二门学科分类表,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过去所有的学科分类,包括前面提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美、英、德、日等国的学科划分,其关系都是线性的,最大的学科群是学科门类,然后才是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等。这种划分缺少更大的学科群即学科部类的设置,看不出各学科部类之间的结构和关系。我们的划分设置了学科部类,清楚地表明人类知识的两大部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和四大部类组合而得到的各种关系,这样一来,人类知识的基础和现代大学的基础都得到了清楚的说明。其次,四部十二门学科分类法中第I、II、III、IV这四个部类分别对应四大文献检索系统SCI、EI、A&HCI、SSCI;反过来看,四大文献检索系统涵盖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全部文献。所以,人类知识体系即四部十二门学科分类表是具有完全的科学依据的。
区分知识和能力的开端。早在古希腊的学科划分“三科四艺”中,就已经区别了知识和能力。“三科”所指的语言、逻辑、修辞是学科知识,“四艺”所指的算术、天文、几何、音乐是技艺和能力。
能力对应的英文单词有“ability”“capa-city”“capability”“faculty”等。其中,乔姆斯基(N. Chomsky)在“先天语言能力”(Innate Language Faculty, ILF)重大理论中采用了“faculty”。20世纪中叶,天才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认知科学的第一代领袖乔姆斯基在他的革命性的语言学理论中提出了“先天语言能力”的理论假设。这个假设的提出旨在回答当时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语言能力从何而来”。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行为主义语言学,其认为语言能力是后天习得的。乔姆斯基认为,这种理论解释无法回答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所谓“刺激匮乏”(the poverty of the stimulus),即母亲并没有教给儿童所有的语句,儿童如何从有限的语言刺激中学会无限的语句呢?二是不同的人类语言之间可以互相理解(翻译),但人和非人类动物之间的语言为何不能互相理解呢?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让乔姆斯基提出“先天语言能力”的伟大假设。这一假设的提出,促使乔姆斯基开始研究语言和心智的关系。1968年,乔姆斯基在《语言和心智》一书中讨论了语言和心智的问题。[9]先天语言能力的假设在后来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渐被证实。其中一个重要的实验证据是哥普尼克(M. Gopnik)等人对一个具有语言缺陷病史的K家族的病史研究。这个家族具有一种特殊的语言缺陷,表现为对复数、时态、性、体等几乎所有语法形态特征的语言能力缺失,尽管这个家族对词汇的掌握没有问题,其非语言能力也是正常的。对这个家族三代共31人的语言缺陷进行调查,第一代2人,女性有缺陷,男性正常;第二代5人,3个女性全部有缺陷,2个男性一个正常另一个有缺陷;第三代24人,11人有缺陷(5男6女),13人正常(6男7女)。各种情况排列如图2所示。
图中,♂和♀分别代表家族中的男性和女性,下划线表示该成员具有特殊语言缺陷(SLI),加括号表示该成员未受SLI影响。令人惊讶的是,K家族的SLI遗传树图完全符合遗传规律,这就证实了乔姆斯基关于人类语言能力是由基因遗传的假设。
“先天语言能力”因其强大的解释力,在语言学发展中掀起了一场“认知科学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改变了语言(包括英语)学习和水平测试的方式。例如,英语水平考试普遍使用的完形填空,测试的是语言能力而非语言知识。
“先天语言能力”的提出,让我们知道,知识并不等于能力。由此可以理解,教育的目的除了传授和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心智和认知能力的培养。乔姆斯基发现的语言能力,是人类最重要的心智和认知能力。
认知科学定义的知识和能力。2015年,笔者在《论人类认知的五个层级》一文中提出人类进化论和人类认知五层级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生命进化过程中,依次产生了神经、心理、语言、思维和文化五种心智,从而产生了五个层级的认知能力。[10]
如图3所示,五个层级的心智和认知都是某种特殊的能力,人类凭借这种能力对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进行加工,从而形成知识和文化。例如,认知科学的“6+1”学科框架就是从五层级的认知能力产生的。图4呈现了由五个层级的认知能力到相应学科的映射关系。
更广泛地,我们可以认为人类的全部学科知识和学科体系,都是由人类的心智和认知能力所创造的,或者说,人类的全部知识和文化都是由五层级的人类心智和认知能力所创造的。由于五个层级的心智和认知能力是瞬时贯通的,所以,人类的全部知识也应该是综合交叉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认知科学的发展到21世纪初期形成的聚合科技NBIC表明,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从综合到更大的综合,是人类认知能力所主导的人类未来知识创新的根本趋势。图5呈现了认知科学、聚合科技统领的21世纪人类知识大科学结构。[11]
“知识”一词的中文词源学和词典解释已于前述。“知识”的英文是“knowledge”,《牛津词典》对其的解释是:“通过教育或经验获得信息、理解和技能。”(The 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and skills that you gain through education or experience.)《新牛津词典》对其的解释是:“个人通过经验或教育获得的事实、信息和技能;关于某一对象的理论或实践的理解。”(Facts, information, and skills acquired by a person through experience or education; the theoretical or practical understanding of a subject.)《柯林斯词典》对其的解释是:“知识是某人具有或所有人共有的关于某一对象的信息和理解。”(Knowledge is information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a subject which a person has, or which all people have.)《韦氏大学英语词典》将“知识”与“学习”“学识”“学术”作为同义词,意为“那些能够被个人或人类所认识的东西”。其中,“知识”指那些“通过学习、调查、观察或经验获得的事实或思想。”(Knowledge, learning, erudition, scholarship, mean what is or can be known by an individual or by humankind. Knowledge, applies to facts or ideas acquired by study, investigation, observation, or experience.)
上述定义中,关于“知识”的义项主要有“事实”“信息”“理解”“技能”“学识”等;获取知识的方法主要是“教育”“经验”“学习”“调查”“观察”等。由此我们可以给“知识”下一个经典的定义:
“知识是个人或人类通过教育、学习、调查、观察、经验等手段获得的关于对象的信息、理解和技能。”
“能力”对应的英文有两个:“ability”和“faculty”,前者指做事的能力,后者指官能、天赋。对“ability”,《牛津词典》的解释是:“能够去做某事的本领。”(The fact that sb/sth is able to do sth.)对“faculty”,《牛津词典》的解释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任何生理的或精神的能力。”(Any of the physical or mental abilities that a person is born with.)乔姆斯基的“先天语言能力”指的是后一种能力。综上所述,我们也能给“能力”下一个经典的定义:
“能力是一个人通过后天获得的做事的本领,或者通过先天遗传的生理或精神上的做事的本领。”
上述所有关于知识和能力的解释和定义,都缺少对知识与能力之间关联的表述。上述定义虽然明确知识需要通过教育、经验、学习、调查和观察等方法获得,但既没有明确知识与能力之关联,也没有明确教育与能力之关联。总而言之,“知识”和“能力”并未同时进入“教育”视野。很显然,关于教育的本质和恰当的定义,只能在认知科学的理论方法下才能给出。
基于认知科学重新认识教育
“6+1”学科框架下,教育进入认知科学的视野。20世纪70年代认知科学建立之初,采用的是六大学科的框架,哲学和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作为认知科学的六大来源学科,构成了认知科学的交叉学科框架。[12]进入21世纪,认知科学的创立者们将教育和教育学(education)纳入认知科学框架,形成“6+1”的学科框架(如图1所示)。按照认知科学的“6+1”学科框架,教育和教育学乃认知科学题中应有之义。那么,为何要将教育纳入认知科学的学科体系呢?
我们知道,创立认知科学的目标和任务是“揭开人类心智的奥秘”。[13]为了破解这个“上帝最后的奥秘”,认知科学的先驱者们把与人类心智相关的六大学科集合在一起,形成了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的学科框架。哲学和逻辑学从主客体的关系、符号和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系来探索心智和认知的奥秘;语言学通过语言符号的各种脑加工方式(如语形加工、语义加工以及语用加工)来探索心智和认知的奥秘;心理学从感知觉和注意、表象和记忆等感性认识的形式来探索心智和认知的奥秘;文化人类学从生命进化、心智的产生、人类心智和动物心智的区别、心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心智的个体差异性和文化差异性等方面来探索心智和认知的奥秘;计算机科学通过符号和计算,从人类五个层级的心智和认知来模仿并替代人类智能;脑与神经科学从认知的神经机制、心智与意识、心身问题等方面来探索心智和认知的奥秘。那么,教育和教育学与人类心智和认知又有何关联呢?
认知科学重新定义教育。事实上,教育和教育学是与人类心智和认知联系最紧密的领域和学科,但传统的教育观却忽视了这一点。传统观点认为,教育是按一定要求培养人的工作,主要指学校培养人的工作(参见《现代汉语词典》对于“教育”词条的解释)。西方的教育观表述得更具体一些,认为教育是为提升知识和发展技能在学校进行的教学、训练和学习过程(a process of teaching, training and learning, especially in schools or colleges, to improve knowledge and develop skills)(参见《牛津词典》)。《教育学基础》(第3版,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对“教育”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最后给出的定义是:“教育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促进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个体化的实践活动。”[14]
上述定义均未将“6+1”学科框架下认知科学对教育和教育学的影响考虑在内,也没有指明教育与心智和认知的关系,因而无法全面揭示教育的本质,也就不能理解和说明为何在21世纪要将教育纳入认知科学体系。因此,我们需要从认知科学来重新认识和定义教育。
首先,教育是人的心智和认知能力的培育过程。事实上,教育从一个人的胎儿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这就是所谓“胎教”。学前教育、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直至人的一生都处于心智和认知的不同发展阶段,因此,教育要与不同阶段的心智和认知发展相适应。
其次,教育要从人类认知五层级,即脑与神经认知、心理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和文化认知五个层级逐次展开,适应不同阶段的心智和认知发展(如图6所示)。
最后,教育是伴随人的终身发展的心智和认知培育过程。“终身发展”是教育这种特殊的人类认知活动的本质特征,其根据是人的心智和认知是终身发展的。个体的心智发展重演了种群心智发展的历史,因此,适应人的心智和认知发展需要的教育活动也应该和必须是终身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站在认知科学的立场,基于人类心智的发展来重新定义教育和教育学。
“教育是伴随人类终身发展的心智和认知能力的培育活动和培育过程。”
在这个定义下,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提高心智和认知能力。或者说,传授知识的目的就是提高心智和认知能力。定义项中的两种能力是心智能力和认知能力。心智能力是进化中获得的、对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加工以求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认知能力是使用心智能力来认识世界的能力。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行为和规律的科学。”
以上定义是在认知科学背景下对教育和教育学的重新认识,这种重新认识是必需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在21世纪之初要将教育和教育学纳入认知科学的学科框架,也才能理解教育和教育学在21世纪的全新含义。
NBIC提出未来教育的概念和远景蓝图。2000年,美国国家基金会和美国商务部共同资助了一个项目,旨在研究哪些领域和学科将成为21世纪的带头学科。美国70多位科学家参加了这一项目,并形成了一份长达460多页的研究报告,题目是《聚合四大科技,促进人类发展》(Converging Technologies for Improving Human Performance),它有一个响亮和颇具吸引力的副标题: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Nanotechnology,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这一被称为“21世纪科学技术的纲领性文献”的报告的最后一部分“统一科学和教育”(Unifying Science and Education)提出了未来教育的概念和远景蓝图。来自美国国家研究院(NRC)和各研究小组的大量报告证实,人类社会的未来依靠科学的持续进步,而持续的科学进步又依赖于科学教育。通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规范和引导,美国约一半的学校所教的科学知识将基于科学和技术统一的原则,而不是基于工业革命前所产生的一些孤立的学科。未来,聚合科技包括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的协同作用,不仅会促进基础教育、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也将促进终身教育和学习,这是不断发展的技术经济所要求的。[15]
人类认知五层级与教育发展五阶段
根据重演律,个体的心智和认知发展重演了人类心智和认知发展的历史过程。再根据教育阶段划分,我们可以建立人类认知五层级和教育发展五阶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如图6所示,纵轴为心智发展的五个层级,横轴为终身教育的各个阶段。从中我们可以分析演绎出以下几方面内容和结论。
人类心智和认知五层级与教育发展各阶段完全对应。根据重演律,从婴儿出生到成人的发育过程重演了人类心智从神经、心理、语言、思维到文化心智的发展过程。因此,从婴幼儿教育、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到大学教育,应该是与心智发展阶段同步和协调一致的。从图6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对应关系。
以人类认知五层级(纵轴)为变量,可以看到教育各阶段心智与认知发展的脉络。脑与神经认知从胎儿时期就开始了。根据乔姆斯基的先天语言能力理论和笔者提出的先天逻辑能力理论,[16]人类在胎儿时期就具备了语言和思维的认知能力;同时,在胎儿时期,左右脑的侧化已经完成,左右脑的发育也基本完成。脑与神经的认知贯穿人的一生,脑是所有人体器官中最后衰老的部分。事实上,除非遭遇病变,大部分人的大脑到濒死之际都能够保持清醒和有效工作。
心理认知是从婴幼儿时期(0~3岁)开始的。这个时期人的感知觉系统(包括眼、耳、鼻、舌、身五大感知系统和语言感知觉系统)开始有效工作,婴幼儿开始体会到父母亲情,并形成自我意识。从这时开始,心理认知能力将伴随人的一生。
语言认知能力包括言语(口语)的认知能力和语言(文字)的认知能力。言语知觉能力萌生于婴幼儿时期,但形成于学前时期(3~6岁),这个时期儿童的语言认知能力表现在口语的听和说以及言语的沟通能力上。
语言(文字)的认知能力从小学时期开始,识字是获得语言认知能力至关重要的一环。言语和语言这两种语言认知能力将伴随人的一生。
思维认知能力的形成从婴幼儿和学前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但其重要的发展阶段是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大学这两个时期。事实上,这两个时期各门知识的学习,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其目的就是思维认知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文化认知是最高层级的人类心智和认知能力,待到受教育者逐次完成婴幼儿、学前、小学初中和高中各阶段的知识学习并获得相应的脑与神经、心理、语言、思维等各个层级的认知能力之后,这种能力才开始形成。文化认知能力的系统发展和逐渐成熟,开始于成人阶段即高中大学阶段(16~22岁),并贯穿于其后的整个成人发展阶段。文化认知的能力表现在文化创新上,包括科学技术创新、哲学创新、艺术和宗教创新等。
以教育发展阶段(纵轴)为变量,可以看到某个层级的心智认知在相应教育阶段的体现和要求。在胎教阶段(-1~0岁),教育的目标主要是脑与神经层级的心智和认知能力的发展。在婴幼儿阶段(0~3岁),教育的目标主要是脑与神经认知、心理认知两个层级的心智和认知能力的发展。在学前阶段(3~6岁),教育的主要目标涉及脑与神经认知、心理认知、语言认知三个层级的心理和认知能力的发展。在小学初中阶段(7~15岁),教育的目标涉及脑与神经认知、心理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四个层级的心理和认知能力的发展。在高中和大学阶段(16~22岁),教育的目标涉及所有五个层级即脑与神经认知、心理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文化认知各个层级的心理和认知能力的发展。可以看到,学前、小学、初中和高中这几个阶段是人生发展最重要的阶段,涉及所有五个层级心智和认知能力的全面发展,其所对应的教育阶段称为“基础教育”阶段,国际上统称为“K12”教育。这是一个人毕生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也是基础教育阶段从初级到高级(从低阶认知到高阶认知)逐步提高人的心智和认知能力的时期。
从认知五层级与教育各阶段的对应关系还可以看出,教育的目标不仅是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心智和认知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教育的目的固然是要传授和学习知识,但学习知识是为了提高心智和认知能力。
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综合知识和认知能力的人才,最高目标是培养文化传承人。从人类认知五层级和教育发展五阶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出,文化认知处于人类认知的最高层级,它是以语言认知和思维认知为基础的。人类以语言和思维创建了全部知识体系,知识的积淀形成文化。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我们所学习的知识是前人利用语言和思维认知能力建构的。在学习这些知识的同时,我们也获得了语言和思维认知能力。在大学阶段即人生的成年期,我们开始理解和掌握全人类的文化,特别是本民族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主要是精神价值)的东西,文化的核心是科学技术、哲学和宗教。文化是人类所特有的另一种基因。除了和其他动物一样具有自己的生物基因,人类还具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基因,即“媒母”或“媒因”(meme)。
文化知识包含了全部的人类知识,文化认知能力包含了其他四个层级的认知能力,即思维认知、语言认知、心理认知、脑与神经认知各个层级的能力。
文化认知能力是最高级别的人类认知能力,主要是在高中和大学时期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认知能力的培养主要通过三种文化形式,即科学技术、哲学和宗教的学习。世界顶尖学府哈佛大学致力于培养三类人才:领导者(leaders)、学者(scholars)、工商业创业者和企业家(businessmen),而归结到一点就是培养人类文化的传承者(cultural inheritor)。可见,文化知识是人类最广阔最丰富的知识体系,文化认知是人类最高层级的认知能力。由此观之,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具有丰富知识和强大认知能力、富有综合创新精神的、能够引领人类前进方向的文化传承人。
五层级认知能力的培养
在认知科学发展的背景下,由于人类认知五层级理论和认知科学“6+1”学科框架的建立,教育不可避免地与认知科学结为一体,21世纪教育的面貌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
认知科学时代教育的目标和任务不仅是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心智和认知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从人类认知五层级与教育各阶段对应关系图(图6)我们不仅看到五个层级的人类心智和认知能力与教育各个阶段的对应关系,还清楚看到心智和认知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在教育发展各阶段的要求。
神经层级的认知能力培养。如图6所示,沿着纵轴方向即教育各阶段看,脑与神经层级的心智和认知能力的培养贯穿人的一生。在胎儿时期,脑与神经认知能力的养成就已经开始了,其中既有自然过程,如左右脑的发育和两种先天能力——先天语言能力和先天逻辑能力——的形成;也有教育过程,如胎教。根据认知科学,胎教有利于促进胎儿神经系统发育,但要遵循脑与认知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在婴幼儿时期,脑与神经认知能力继续得到培养和发育,其主要是通过学习和训练,建立必要的和重要的神经联接,为今后的发展打好基础。在脑的发育方面,婴幼儿期、学前期和小学初中都是大脑发育的重要时期。这三个时期,在心智和认知发展上应施以科学的教育方式。例如,学前阶段(3~6岁)是大脑充分发育的时期,应该通过适当的智力训练和行为能力训练引导孩子的大脑健康发育,尤其是专注力、创造力、观察力和记忆力的培养和提高。小学初中阶段(7~15岁),在先天语言能力和先天逻辑能力正常发育的基础上,要注重语言和逻辑认知能力的培养,同时还要注重行为能力(包括言语行为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高中阶段学生逐渐进入成年期,高中和大学阶段(16~22岁)学生的神经系统发育健全、大脑发育完备、心身发育成熟,为更高层级的心理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和文化认知能力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脑与神经认知的基础。
心理层级的认知能力培养。在胎儿时期(-1~0岁),由于胎儿的大脑尚未发育成熟,这个时期的心理认知是不存在的。在婴幼儿阶段(0~3岁),个体的感知觉逐渐形成,产生了与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亲情,并产生了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此后,心理认知能力持续发展,心理认知行为也将贯穿一生。在学前阶段(3~6岁),儿童的性格逐步形成,并产生喜怒哀乐的情绪,渴望被关注。同时,具备图形认知能力,表象和记忆力形成并逐步发展,开始形成概念,并对事物有了自己的心理判断。在接下来的小学初中阶段(7~15岁),从儿童时期进入青少年期,进入心理敏感期,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出现叛逆心理,同时情窦初开,会对身边的异性发生兴趣甚至产生特殊的情感。对这个时期的青少年要特别加以正确引导,帮助他们克服成长中的困惑、烦恼,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高中时期(16~18岁)进入青年时代,心理进一步发育成熟,情感日益丰富,意志力逐步增强,兴趣更加广泛和稳定,学习动机更加明确,理想和世界观开始形成,行为的自觉性更高,给认知能力培养以强大的推动力。大学阶段(19~22岁)进入成年期,生理和心理均已发育成熟,自我意识逐步成熟,独立意识增强,自我认识和评价更加全面和准确,开始了更为深入和丰富的自我探索与发现。同时,大学阶段常常也是人生中情绪体验最为丰富的时期,这与其生理的成熟、自我意识和社会性需要的提升以及社会环境的复杂性等因素密切相关。
语言层级的认知能力培养。“我言,故我在。”[17]语言认知能力是人类全部认知能力的基础。语言认知能力的培养在人的毕生发展中至关重要。语言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语言知识包括口语知识和文字知识。相应地,语言认知能力包括口语听、说和言语交流的能力以及文字表达和写作能力。
虽然在胎儿期已有先天语言能力存在,婴幼儿期也有口语个别音节听和说的语言能力的表现(实际上是先天语言能力的表现),但作为外部语言能力的口语能力是在学前阶段(3~6岁)形成的,表现为言语知觉能力、口语的听说能力以及言语交流沟通能力。此后,语言认知能力贯穿人的一生。小学和初中阶段(7~15岁)完成识字教育。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学生,在小学阶段学习并认识约3500个常用汉字,包括全部一级汉字和部分二级汉字,中学阶段继续完成全部一级汉字和二级汉字共约6000个汉字的学习。识字教育的意义在于建立语言的语形加工(包括词法加工和句法加工)和语义加工的脑与神经机制和心理机制,从语形和语义两个层次来理解语言、应用语言。因为人类认知是以语言认知为基础的,所以无论是培养领导者还是学者和创业者(上文提及的哈佛大学人才培养目标),这一阶段语言认知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都至关重要,其成败将影响人的一生。高中大学阶段(16~22岁)语言认知能力培养的第一要务是语用能力的养成。所谓语用能力,就是完整理解语言意义的能力和利用语言来做事的能力。一方面,语用加工要从说者、听者、时间、地点、语境五个维度来获得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所以,语用学的意义才是语言表达式的完整的意义。汉语是典型的语用语言,汉语表达式的意义只有在语用学的维度才能真正理解。所以,语用认知能力的培养对中国学生尤为重要,可通过对《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明清戏曲和小说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戏曲艺术的学习来获得。另一方面,语用能力是指人用语言来做事的能力(doing something in saying something),相应的语言学理论是牛津分析哲学家奥斯汀(J. L. Austin)和美国语言和心智哲学家塞尔(John R. Searle)所创立的言语行为理论,它是语用学的基础和核心的理论。[18]此后,塞尔又将其扩展为语言建构社会的理论,指出语言在建构社会实在中发挥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使用语言来做一切事情,包括建构整个人类社会。[19]学习和掌握语用学和语用逻辑,是成功应用语言交际艺术,提高语言认知能力非常重要的一环。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教育的目标仍然是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毕业证书是知识学习合格的证明,学位证书则是认知能力(表现为科研能力,即学位论文的写作)合格的证明。[20]
思维层级的认知能力培养。“我思,故我在。”[21]在语言认知能力基础上产生的思维认知能力也是人类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认知以语言为基础,以思维和文化为特征。
思维认知能力是在语言认知能力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在毕生学习和教育发展阶段中,它出现在语言之后。先天逻辑能力和先天语言能力在胎儿时期就已经存在,并且在婴幼儿和学前阶段也已经有所表现。根据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的研究,婴幼儿的思维认知主要是运动思维,即通过探索感知觉与运动之间的关系获得动作经验,在认知上发展了客体永恒性,知道了消逝了的事物的存在,具有了合乎逻辑的目标定向行为。思维作为一种独立的认知能力,其学习和养成主要是在小学和初中阶段(7~15岁),即通过自然科学知识(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和人文艺术学科知识(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的学习,逐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直觉思维能力。高中阶段(16~18岁)继续学习自然科学和人文艺术学科的知识,培养批判性思维等高级思维能力。大学阶段(19~22岁)及其后的研究生阶段,主要通过专业化的知识学习、科学研究和学术论文的写作,进一步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
文化层级的认知能力培养。语言认知、思维认知和文化认知是人类认知的三个组成部分。其中,文化认知是最高层级的认知形式,也是最高形式的人类认知能力。
根据人类认知五层级理论,文化认知是以其他四个层级的认知为基础的。在人的毕生发展中,我们依次获得脑与神经认知、心理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各个层级的认知能力,最后形成文化层级的认知能力。
文化是一种知识体系,一种认知形式,一种遗传基因。从知识体系上看,文化包含了全部的人类知识,同时也由全部人类知识来支撑。例如,国学是中华文化经典之学,乃“国故之学”,涵盖了中华文化知识体系,汇集了中国历代的文化典籍和学术成果。章炳麟认为国学首先是小学,此乃国学之基础,包括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版本目录学,其他还有经学、史学、诸子、文学等。清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文献《四库全书》被视为国学经典,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36000册,约8亿字。如此浩渺的知识典籍,足见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从认知形式上看,文化认知是在进化中获得的最高层级的心智能力,它以脑与神经、心理、语言、思维等四个层级的心智能力为基础并包含了人类所有层级的心智能力。所以,文化认知是最高层级的人类心智和认知能力。从遗传基因看,人类不仅具有作为生物和动物都具有的生物基因,更具有人类所特有的文化基因,即上文提及的“媒母”或“媒因”。作为一种行为方式,文化不是通过基因的方式遗传,而是通过模仿的方式从一部分人传递到另一部分人(参见《牛津词典》)。更简明地说,文化基因是一种思想信念或社会行为因素,通过NuR9ymXLJS4zx2EtX8451h47Uj/kpefccwGbdUxICm4=文化特别是模仿代代相传(参见《柯林斯词典》)。由此可见,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遗传方式”,文化基因是何等重要。20世纪美国制定了两大科学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 HGP)和人类认知组计划(Human Cognome Project, HCP),[22]前者旨在揭开人类生命的奥秘——通过基因来遗传,后者旨在揭开人类认知的奥秘——通过文化来传递。从人类五层级理论可知,文化层级的心智和认知能力是从脑与神经、心理、语言、思维的心智和认知能力及知识学习中逐次形成和获得的,包含了人类全部的知识和能力,形成了人类特有的、可以通过模仿和学习来获得的代代相传的行为和认知能力。
文化如同血液,流淌于我们的全身,我们无时无刻不浸润于自己的民族文化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5000年来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我们不能脱离自身的文化,犹如我们不能摆脱自身的基因。那么,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呢?这就要从中国人心智和认知的各个层级加以分析,即从中国人的脑与神经认知、心理和行为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知识和社会行为方式加以分析。特别地,要从中华民族特有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精神生产方式,即从中华民族特有的农耕生产方式即农耕文化,从中华民族的语言、思维和知识之特质,从中华民族的科学和技术、文学、历史和哲学、艺术和宗教来探索中华文化之特质,揭开中华文化基因之奥秘。笔者所带领的清华大学认知科学团队20年来所从事的认知科学研究,特别是近10年来所承担的两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语言、思维、文化层级的高阶认知研究”“认知科学与中华文化特质研究”致力于探索人类认知的奥秘,特别是探索中华民族认知和文化基因的奥秘,以上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文化传承人,使人类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根据以上分析,在教育的各个发展阶段,我们都能看到文化因素的影响。根据人类认知五层级理论,文化认知能力的形成,需要经过脑与神经认知、心理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各层级认知能力的培养和积累才能实现。因此,文化层级认知能力的形成始于高中阶段,发展和成熟于大学及其后的研究生阶段,主要通过各种文化知识的学习,即通过科学与技术、文史和哲学、艺术和宗教知识的学习,来获得文化认知和创新能力。大学及其后的研究生阶段,教育培养的目标是学生的文化认知能力和创新能力。文化需要创新,创新也需要文化,任何真正意义的创新都是文化创新,包括科学技术创新、哲学理论创新、艺术和宗教创新。
认知科学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
“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是钱学森晚年对中国科学和中国教育的关怀和思考。
“钱学森之问”引发了科技界、教育界、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一些人也提出了解决方案,但多数是就科技而论科技,就教育而论教育。迄今为止鲜有人将“钱学森之问”与知识和能力联系起来思考,没有将“钱学森之问”与认知科学联系起来思考。笔者认为,回答这一“世纪之问”应该以“知识与能力”“心智与认知”为切入点,从认知加教育的立场来加以分析和认识。
什么样的人是“大师”和“杰出人才”。“大师”有以下共同特点:第一,他们都是学贯中西、兼通文理的通才和全才,而不只是某一个领域的专才,都有强大的交叉综合知识背景作为其专业支撑。例如,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兼通文理、知晓古今,故而能深刻洞察社会问题,作出非凡的成就。郭沫若的成就遍及文学、诗歌、戏剧、历史、考古、古文字等领域,在中国现代史上,他还是著名的政治家和革命活动家。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不仅精通历史,更精通西方古今语言20多种,尤精梵藏经典。作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他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真正的国学大师。傅斯年评价他:“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所书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为寅恪先生自身之写照,正所谓“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第二,分析和综合两种方法的应用。上述大师们的成就深深扎根于专业和分析的方法论,但其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都体现出了集大成的综合性特色。第三,知识和能力并重。上述大师们都具备深厚而广泛的专业基础知识,更重要的,他们在语言、思维、文化方面具有卓尔不群的认知能力。第四,创新是大师和杰出人才的共同特质。民国时期大师们的学术成就,不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共同特质是以创新推动先进文化的发展。
回看来路,大师们所具备的,可能正是我们今天的教育体制所缺少的,所以才会产生钱学森先生的遗憾和追问,而这也正是我们的未来教育应该加以重视和改进的。
强调知识综合,注重能力培养。一直以来,教育被视为传授和学习知识的一种个人和社会的行为。但在认知科学时代,教育的内涵外延与发展路径已全然发生改变,应代之以新时代的教育观。
未来教育应该坚持知识和能力并重,更加重视心智和认知能力的培养。20世纪是分析的时代,人类知识被分割为“学科门类十几个、一级学科几十个、二级学科几百个、三级学科几千个”这样一种“支离破碎”的体系,现代大学教育强化了这种学科分隔。学生在被培养为专业化人才的过程中,综合认知能力未得到有效锻炼和充分培养。在认知科学时代,我们学习的知识除了专业知识之外,更要重视交叉综合的学科知识,提高综合的认知能力。
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心智和认知能力,要遵循心智和认知能力与教育发展阶段相对应的规律(如图6所示)。教育的最终目标对应于人类认知五个层级,旨在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心智和认知能力。历经婴幼儿、学前、小学和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的学习,个体逐步获得脑与神经、心理、语言、思维和文化各层级的认知能力,从而为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及其后的文化创新(包括科学技术创新、哲学创新、艺术文化创新等)奠定了基础。
重新定义教育,变革教育体制。培养“学术大师”和“杰出人才”,要进一步明确未来教育的定位,全面深化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
第一步是以认知科学重新定义教育。按照我们的定义,教育是伴随人终身发展的心智和认知能力的培育活动和培育过程。在这个定义下,教育的目标不仅是传授知识,还包括提高心智和认知能力,而传授知识的目的则是更好地提高心智和认知能力。
按照这个定义,目前的教育体制与教育的本质和要求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教育仅仅被看成是传授和学习知识的一种途径和手段,人类心智和认知尚未有效地进入教育视野。这是现行教育体制尚需完善之处。
第二步是根据教育的新定义,将教育发展各阶段(胎教、婴幼儿教育、学前教育、小学初中教育、高中大学教育)与人类认知的五个层级(脑与神经认知、心理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文化认知)相对应,重新制定教育发展各阶段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通过对知识的系统性学习,提高受教育者的心智和认知能力,这是未来教育的根本任务。
第三步是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根据笔者在清华大学和贵州某大学的教育实践,认知科学一旦进入教育领域,将引发重大的变革。例如,笔者在贵州某大学创办了认知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在基础课程中开设哲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民族学、教育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等课程,涵盖了“6+1”的学科框架。在课程安排上,第一、二学年开展“多学科宽基础培养”,第三学年为学生提供“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即在“6+1”的学科框架下,引导学生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学科专业来完成学位论文并授予其相应学科的学位。在这样的创新体制下,学生经过四年的学习,不仅获得了多学科交叉综合知识,也全面提升了五个层级的认知能力。经过多年的探索,这一培养模式经过了以下实践检验:其一,学生普遍具有较高的实验和实证能力,在学术研究和学位论文的撰写中,展现了较高的科研能力和认知思维。[23]其二,该高校认知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考研率和录取率在该校各学科专业中遥遥领先。其三,该专业其他学生(即除去考研学生外)实现了百分之百就业,就业率大大优于其他专业毕业生。以上充分证明,宽基础、多学科交叉的培养模式是有效的,认知加教育的改革也是颇具前景的。
培养杰出人才,实现文化创新。根据人类认知五层级理论,由于文化层级的认知能力依次包含了其他各层级的认知能力,因此,文化认知层级的引领者同时也将引领其他各层级的认知主体。
杰出人才应该具备以下素质:第一,具有实践经验和理性思维能力,不仅能够从经验和实践中学习知识,而且能够以理性思维进行逻辑推理和逻辑分析。第二,掌握分析与综合两种认识方法,不仅能够进行本学科的专业分析,还能够进行跨学科的归纳和综合。在认知科学和综合的时代,综合的能力尤为重要。[24]第三,通过知识的学习,具备脑与神经、心理、语言、思维、文化五个层级的认知能力。第四,在知识学习、学术探索和科学实验中,涵养了求实、求真、更求新的科学精神。[25]
五个层级的人类认知能力中,文化是最高层级的认知能力。人类文化包含科学、哲学、宗教三个层次,[26]文化创新是最高形式的创新。从这个层面上看,杰出人才就是具备文化创新能力——包括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哲学创新能力、艺术宗教创新能力——的人才,这也是“钱学森之问”中希望我们的教育体制能够培养出的大师和杰出人才。
优化完善“6+1”学科框架,实现认知教育大联盟。目前,相关领域的探索逐步深入,未来教育的图景已逐步显现。中国认知科学下一阶段的发展是认知科学与教育的结合,将认知科学的理论方法应用于教育,将极大赋能并推动中国教育的未来发展。从认知科学的立场和观点看,未来教育变革的必然之路是进一步廓清“6+1”学科框架,重新认知教育,变革教育体制,协同各方共同推动中国认知-教育事业发展,打造认知-教育大联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充满无限希望和可能的认知-教育新时代。
注释
[1]蔡曙山:《认知科学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蔡曙山:《论人类认知的五个层级》,《学术界》,2015年第12期;蔡曙山:《生命进化与人工智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2][24]蔡曙山:《综合的时代:从认知科学到聚合科技及其未来发展》,《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10月下。
[3][4]许慎撰、徐铉校:《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05、46页。
[5]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他说:“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都没有的……”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30页。
[6][11]蔡曙山:《大科学时代的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和综合创新》,《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5月上。
[7]蔡曙山:《认知科学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2007第4期;蔡曙山:《大科学时代的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和综合创新》,《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5月上。
[8]笔者在哈佛大学访问时了解到,哈佛大学每个学年第一学期都要讨论“现代大学之基础”这个问题,答案就是Liberal Arts。
[9]N. Chomsky, Language and Min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72.
[10]蔡曙山:《论人类认知的五个层级》,《学术界》,2015年第12期。
[12]蔡曙山:《认知科学导论》,丛书总序,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13][15]米黑尔·罗科、威廉·班布里奇编,蔡曙山等译:《聚合四大科技,提高人类能力: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14]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4页。
[16]蔡曙山:《认知科学框架下心理学、逻辑学的交叉融合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7]蔡曙山:《我言,故我在——语言、思维、文化层级的高阶认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蔡曙山:《论语言在人类认知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18]蔡曙山:《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绪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9]J. R. Searl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The Free Press, 1997; J. R. Searle, Mind, Language, and Society, Basic Books, 1999.
[20][23]蔡曙山:《科学研究与科学论文写作》,《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21]D. René,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of Rightly Conducting the Reason and of Seeking Truth in the Science, Independently published, p. 15.
[22]M. C. Roco and W. S. Bainbridge (eds.), Converging Technologies for Improving Human Performance, Springer, 2003, pp. 32, 43, 68, 98, 322, 417;米黑尔·罗科、威廉·班布里奇编,蔡曙山等译:《聚合四大科技,提高人类能力: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25]蔡曙山:《我言,故我在——语言、思维、文化层级的高阶认知研究》,附录三《母校独山中学校训》,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
[26]蔡曙山:《自然与文化》,《学术界》,2016年第4期。
责 编∕张 贝 美 编∕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