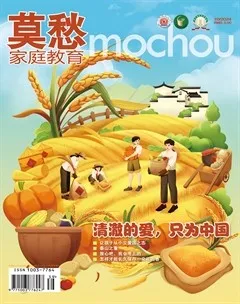我家的家庆日
10月1日是国庆日,也是我家的家庆日。我父母是1957年10月1日结的婚,我是1987年10月1日结的婚,我儿子是2015年10月1日结的婚,一家三代同在10月1日结婚,国庆日便成了我家的家庆日。
这天,我们一大家祖孙四代聚在一起,十几口人,其乐融融。每次聚会,父亲都会拿出他的宝贝,跟我们一起重温他当年的经历。
1
1948年,父亲在海门中学读高三,没等高中毕业,便奔赴盐城加入了革命队伍。部队给每人一根棉纱绳,用来捆扎被子、晾晒衣服。没想到,普普通通的棉纱绳发挥了大作用。南下途中,摸黑行军时全班人拉着绳子走,以免掉队和掉河沟里;渡江时,不会水又晕船的人,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到江南后,有个乡村恶势力猖獗,无人敢当农委主任,不满二十岁的父亲,提起纱绳捆成的井字形背包就住进了农户家,当起了农委主任。我问过父亲:你不害怕吗?父亲说怕,但当想到曾经拴在一根绳上的同学有的已牺牲了,活着的都在拼命工作,就咬牙也要坚持下去。
1957年国庆,父亲拎着井字形背包,母亲抱着外婆给的新被子,一起搬进了租住的屋子。他们第一次租的屋子是城郊农户的半间羊圈,芦苇席把羊圈一隔为二,夜里常听羊的反刍,我姐姐就出生在那里。他们第二次租的是染坊的一角,挂上一条旧被单,拿纱绳一拉算隔断,我就出生在那里。
2
1990年,我在一家百人小厂担任负责人,厂子虽小,但效益不错,在那时算是许多人羡慕的对象,但我却选择离职,到正在筹建的市报社当记者。我从小喜欢文学,新闻工作是我离文学理想最近的台阶。
父亲很支持我,他开了个家庭会议,拿出那根纱绳,再一次讲了他当初高中毕业证也没拿,就投奔革命的经历。父亲很动情地说:“我羡慕你赶上了好时代。”是的,改革开放让我有重新选择工作的权利,这是时代提供的机遇,我可以把个人理想与工作结合在一起。
报社筹建之初,除了领导外,大多数是刚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像我这样有工作经验又是党员的没几个,我就像大哥哥一样带着年轻人干,全身心投入。天天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腰间BP机震动了,立马到路边找公用电话亭回电。报社要求以五笔输入法打字,我边骑车边背字根,等红灯时从车篮里抓起字根表看一眼,手指在车把上模拟。到城郊奶牛场,遇到修路,扛着车走了几里路,也算是让自行车骑了我一回。
2000年国庆,在家庆日聚会上,我说起自己已担任了总编助理,不用那么辛苦到一线采访了。父亲却说,你别把升职当成脱离一线的理由。我记住了父亲的话,没等国庆假期结束就开始了工作。当时企业转制改革全面铺开,这一题材让年轻同事发怵,我正好熟悉企业工作,就主动担纲做了“企业改革进行时”的系列报道,用大量事实和分析回答了“为何要改”“改向何方”和“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等几个突出而尖锐的问题,不仅企业从业者信服,市领导也十分满意,后来几个重大而敏感的题材领导也指定我去采写。
2003年1月,刚任报社副总编的我准备去党校参加新任职干部培训时,已离休在家的老父亲又拿出他那根纱绳。这回他没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帮我把行李箱加捆了个井字。我知道父亲的意思,也把这井字深深烙在心上,以后遇事都要以这纱绳井字来衡量一下。
3
我从企业转岗到报社、文联、广播电视台工作了三十多年,经历了从手写到电脑无纸化,从单一平面媒体到广播电视网络和移动端开发,我经历了传统媒体从巅峰时代到艰难转型的全过程,接着又参与了开创媒体融合的新发展。
几十年来,家里的人口有变化,家里人的职业、岗位有变化,但我们的家庆日没有变化,父亲用纱绳说事的方式没有变化。现在,我儿媳妇也已十分熟悉爷爷和纱绳的故事,去年10月1日,正是儿媳入党前夕,她还专门在家庭聚会上拍了一张合家欢,照片上突出的就是我父亲和他手里拿着的那根纱绳。儿子儿媳结婚后还没孩子,但我父亲已给孩子想好了名字,说不管是男是女,就叫“国庆”。
如今我也退休,与94岁的老父亲各一间书房,我们各自读书看报写作,有时一起在客厅看新闻。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家的事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关心国家就等于关心自家。
老干部局发起公益义捐,我父亲也赶去参加,他说离休在家不能做什么事了,这也算是对国家表达一点自己的心意。今年春天,我还陪父母一起到昆山千灯顾炎武故居参观,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照壁前,老父亲说当年他奔赴盐城投身革命时,心里想的就是这句话。
编辑"乔可可"1525188915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