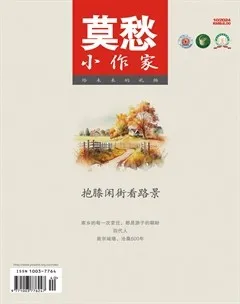茶末
最近喝的茶,是茶末,即细碎的茶屑。茶叶店有售。
弟弟是吴裕泰茶庄的老客,一年总得买大几斤西湖龙井和黄山毛峰。父亲为生计故,几乎绝缘所有需花钱的世俗嗜好,唯茶事不绝。去年,他因疾住进重症监护室,两天后醒来,第一句话:给我泡一杯毛峰。弟弟备的茶,总是双份,给爸,给我。由此多年,跟着忝受其惠。弟弟年小我七岁,我这兄长做得……不想也罢,想起来甚是惶愧。
叫他不要为我准备,说也无效。于是,我只能退而调整喝茶的方略。尽量少动用他送的新茶,多喝陈茶、杂茶。所谓陈茶,是他总担心供应断档,春茶未尽,秋茶又至,由此往复,时间靠前者谓之陈。杂茶是亲朋间的往来礼酬和网购茶,多为椟贵珠贱之物。这样,到了新茶开炒前,我找个机会让他知道“你买的茶,还有好多”,期在他不要再带上我一份。其实,我只是玩了一场自欺欺人的把戏——他是照送如仪。
买茶末,倒非弟贪图便宜,他说是一时兴起的“好玩”。可父亲不买“好玩”的账,一杯后,从此束之高阁。于是,这些茶末便成了我的杯中之物。
少时听父亲与友人聊茶经,余者漫不可忆,唯记得一句:粗茶细喝,细茶粗喝。俗解即:好茶叶,多放点;次茶叶,少放点。父亲读书多,这经验是从陆羽、卢仝处得来,还是自我总结,未得其详。弟曾与茶老板相聊,茶老板介绍说,所谓茶末,是多种茶叶碎屑的混合,其中贵者几千元一斤,贱者几十元一斤。但不管出自“侯门”“寒舍”,一旦成屑,都彼此彼此了。如民间形容浴客:脱得精光,都是一样。茶末,不值得玩味吗?
其实,初识茶末,就是在浴室。
初中以前,都是父亲带我们兄弟俩到浴室洗澡。凡事认真的父亲,总是亲力亲为给我和弟弟手搓全身。一场澡下来,不啻一次重体力劳动,且又在一个“神完气足”的高温高湿环境里完成。好不容易结束,父亲精疲力尽,盘腿坐在休息区“凉快”,喉头涌动。我知道那是口渴,因为我也口渴,弟也口渴。旁边的炕几上,就放着半杯未及清理的剩茶,油油的红绿色,杯壁上沾满了细碎的、茶客们谑称为“满天飞”的茶叶——茶末子。我咽着口水,禁不住揣度茶末茶倾倒入喉时那一泓如油的厚润感。
父亲回到家的第一要务:泡杯茶,也是一周唯一一次喝晚茶、一天喝第二泡茶。昏黄的灯光下,父亲端坐在那张漆皮磨损、棱角磨光的灯挂椅上。万籁俱静,唯间或听见他轻抿茶汤和执篾壳暖水瓶续杯的水流声。渐渐地,这一切都糅合进我的梦,并在我的梦里洇漫。
父亲已至鲐背之年,瞽目病足,弱不胜衣,只能在小小的房间里抓握门框桌椅摸索移动。唯坐在藤椅里,捧着茶杯嘬茶的剪影,还能使我依稀想起他昔日的神采。
我给面前的末子茶续上第二泡。茶末施施然点点向杯底摇落,有点像儿时洗澡晚归时,夜空熠熠眨眼的星星。父亲当然不要喝这茶,稍不留意,便满嘴茶末,欲吐不得,欲咽不能,纠缠得清兴荡然。我倒是无所谓,因为那一壁沫子和酽酽的黛绿色泽,交织成的回不去的温馨,使我沉溺其中乐而忘返了。毕竟,我不似父亲一般的茶中知己。但也未必,喝茶,喝出茶外的滋味,还不能算茶中知己吗?
喝着喝着,不由又想起茶老板说的茶末的出身。茶末,真是一道五味杂陈的茶呀。
赵光琦:江苏泰州人,作品散见于多家报刊。
编辑 沈不言 7865596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