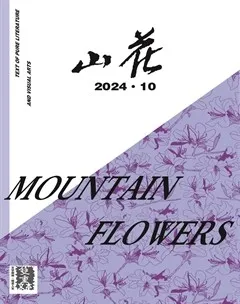山行与出逃
司晨者
把万座山合为一座山
将一座山上的万物
浓缩为一口钟并在每个清晨
用枯木将它敲响
枯木敲钟
钟声入心、安魂
但枯木不耐撞击,木屑纷飞
手掌心里握着的全是灰烬
山中的枯木也很快用光
无法支持不朽的铜钟
司晨者就用灌满清泉的竹筒敲钟
竹筒炸裂
清泉打湿袈娑
就像是每个晚上
他都要在菩萨座下泪流不止
而且忘了:新的一天
应该换一件干净的袈娑
白狼歌
在雪山之侧
我惊奇地发现:岩石堆高的山峰
没有亘古不化的冰川和雪
——而是风暴一样的白色狼群
不断拥到山上
从山顶与天空之间的裂缝
扒开界石,席卷而去
白 鹇
庙前空地上的一摊积水
只能倒映出古榕树比庙宇还大的
浓荫的局部——庙宇和空地
寄托在古榕树的怀抱中
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
在古榕树的枝干上,还有几尊
体量不大的金色佛像
管理庙宇的人,隔一段时间
就要爬到树上清理佛像上的鸟粪
他说,以前来过一群持枪的人
在树下练习射击,一枪一尊
打碎了不知多少尊佛像
一尊佛像从树上掉下,也必有
一只来历不明的白鹇掉下
人们把佛像的碎片和粉末
收集入坛,当成药,可以医治很多
绝症。庙宇的后山,古木森森
蜂鸣如雾,人们在每片芭蕉叶下
垒起了白鹇的坟堆
管理庙宇的人说:只要其他地方
有阳光,那儿就会下雨
我没有去看白鹇墓群,但看见一只
白鹇从空中飞过,洁净的影子
投在空地肮脏的积水中
猛虎山日记
猛虎听命于创物的神
用锦绣脊梁把时间背到人世
却没有把时间放下
一直背着
在丛林中漫游
时间一直在猛虎的
背上。猛虎出行之日
缺乏时间观念的物种不知道回避
而知道回避的物种
总是避之不及
“不知道回避者生,
知道回避者死。”
猛虎山警示碑上的这句箴言
要扒开厚厚的青苔,才能看见
江 边
一只黑猫在黄昏时的澜沧江边
跳跃,逮食空中蚊虫
腰身有异常之美,一会儿舒展
如同幼虎挂上灰色的虚空
一会儿曲卷着,脑袋与四脚相抱
像一团漆黑的矛盾体
打结,扭动,展开
突然静止,又突然惊动
在凝固与飞行之间,探索
动态之中身体的奇观和边界
江水平滑如腹,两条岸
守序地弯曲、延伸,明明已经消失
却又不曾移动过分毫。薄雾生于
水,是江面上的白山峰
没有跟着波浪前移,而是膨化不止
数倍变大,逐个吞吐岸上高耸的
悬崖。黄袍佤族人传说中
白茫茫的梦幻帝国,在深渊中
顷刻食人无数,又在顷刻之间将
腹中人悉数安顿在新的国度
——其实并没有变化
而是一场大雾把旧
换成了新。是所有人做了
一个相同的梦,从梦中出来,发现
用江水洗过的国度就像是理想国
我养在书房的那只猫,喜欢
蹲在窗台上望月亮,这只黑猫
则跳到江边的岩石上,像马戏团
钻火圈的老虎那样,朝着月亮飞纵
坠落到江中,又湿漉漉地爬上
岩石,接着飞纵,身体里
不乏务虚的决绝的人性
面 具
“睡觉时,制作面具的人
身上盖着五个面具
女鬼现身于子夜
看到床上躺着一个有六张脸的男人
以为遇上了统治黑暗的大神。”
——讲故事的人后来也制作面具
一个面具在手,他沉静地站在
人群之外,我靠近他
他就移至一蓬剑麻之后
以备我带着问题再次走近他
故事中的人和物没有必要追求
真实性,但他说:“我的母亲
是一个女鬼,是她的面具
惊醒了我,我要在面具后面
找到失踪多年的父亲。”
不远处,云朵低至屋脊
凤凰花树上,火焰还在生长
枯死之松待伐。清水溢出井口
来喊他吃饭的幼童,额头有红疙瘩
手中的面具被撕掉了双耳
鲁史镇
世界来到小镇,树木的祖先
孤独地站在两条野江交汇处的
岩缝中。鹰是老品种。道路一再
翻修,但路基下的马骨还在
语言晦涩,得返回几个朝代后才能
听清:母亲在喊人起床
叫他敲钟。和尚领导的起义军
在小镇后山被清军剿灭,讲述者说
爷爷昨晚还在月亮下划船
给一群提刀的和尚摆渡。是的
不是从前,就是昨晚,现在爷爷
还躺在江边树洞,战栗不休
担心清军前来捕杀。崔氏的老宅
在小巷中段,没有倒掉
院子里新建的玻璃屋内,主人说
——前来投宿的徐霞客害了怪病
整夜都在咳嗽、咯血。卖茶老人
给我煎了一壶普洱熟茶,味醇
气清,香高。告别时,他让我给他
录一段视频,他举着一个饼茶
对着镜头,刚准备说:“我是
茶马古道最后的守护者骆智忠!”
他养的八哥在老屋檐上,模仿他
把他要说的话提前说给我听
一条狗犹如古人,静默地领我
四下闲逛。北伐将军赵又新
冤死于四川泸州,一棵核桃像神的
宫殿,青苔壁立,天使的绿翅膀
时刻煽动,把消失的将军府
严丝合缝地罩住。有巨云
突然出现在小镇上空,暴雨要落
闪电对准江面,但空寂的世界
无人奔走,避让,灰尘长成了石头
不担心来自高空的清洗
妙高山问茶
庙堂之山崔嵬,土似羊肝
石头状如黑金刚。三天的雨雾
事物的属性,大的、远的、朝向
死亡和神灵的部分,被完整地
藏匿,如同不知去向的经卷
唯有小的、近的、一直在身边的
在现实中的这些,其属性如此明晰
站在人的一边,仿佛事物得到
允诺,从此有了固定的倾向
——绚烂的草木之间没有虚空
茶树时隐时现,说不准边界在哪儿
哪些树干高于庙堂,哪些枝叶
伸入了人的骨缝。它们无法确定
自己的起源和身份,甚至疑心
自己是麻栗,是红毛榉,是多依
是白蜡,是橡,是栲,是构
是樟,是椿,是榕,是无
而后面这些,又分别疑心自己
是别的,是茶树。谁都不是自己
是它或者它们。谁都是神的孩子
但又谁都蒙在鼓里。茶林尽头
荒街破败,连片的竹林自主枯朽
道路遭到遗弃,店铺边打纸牌的人
鸦雀无声。山坳上的墓碑是空的
墓主还在生活中慢跑、弹琴、打歌
事物远远没有走到终点,实相
提前曝光。这雨雾中以一片茶叶
以一只蚂蚁,以一张人脸作为起点
而铺开的潮湿高原,头顶的光
没有照耀,隔着一层迷雾
以正在失传的神话逻辑
推理:此刻会有驮经的大象
燃烧的凤凰,点石成金的异士
四张脸的天神和各有使命的怪物
在一团雾气中诞生,突然现身在
弯曲、泥泞的乡村公路上
山行与出逃
路下埋着鼓。路面是
坑坑洼洼的河床,从鞋边流过去的
水,一直被知识视为文字中间
找不到身影的源泉
禁地的外衣可以罩住任何
一个山峦,而神秘之物仅仅因为
它们保持了沉默或被沉默所困
——语言不动,山中处处都是
误指和冤案。我始终逃避
雷霆,但在这儿,必须触及到
它:杂木林中,高树突兀
小鸟乱飞,碎虫在落叶下产卵
那产生于空中的爆炸声垂直向下
星球坠毁,残片纷飞,拖着连环的
不断产生的巨响,在几米外
击中目标。然后是震颤
和震颤中惊现的哑寂。浓烟状若
升空的古刹,树冠上的火焰
像强制点燃的天灯。一只松鼠
惊魂未定,在一根倒下的楠竹上
朝着我的方向慢慢倒退
尾巴谨慎地触碰竹枝,不敢回头
担心发生巨响的地方还有巨响
马上会发生。它的双目所及
深渊中,屋顶还在,终于有人
背着盐巴出门,有人专门来到露台
摸了摸晾晒在竹竿上的旧衣服
我还蹲在原地,发现路上的
流水中,多了不少
碎叶,断翅和虫尸。站起身
望着远山缅寺金色的塔尖出神
感觉这路上的水,形成了幽深的河
正从我空洞的体壳穿过
并把松鼠、碎叶、断翅和虫尸
以及巨响,留在了血肉中
水云身
驮着经卷走向荒野
在不洁之地
化身为幽暗森林中
象征公义的神秘影子
或与孔雀结合,生下象首雀身的
梦幻守护神。大象的多重身份
源于它的庞大身躯
近似力量之神
水云身曰:我身在象腹之中
走遍了人世上的寺院和山山水水
但我心中无象
无力,无必去之所
水云之身,是肉身消失后
还在行走的一袭布衣
树 下
大地上的文明永远藏着
没有多少人看见
目光沿着斜坡往下,掠过巨石阵
旧时代装满闪电的澜沧江
横卧在深渊中
暴烈的战象兵团到南方受降
赛道上的老虎
河床上集体性奔跑的光头长老
翅膀与火焰之浪
绚丽的图像史
神灵不再亲手拍摄,画画的大师
退回了石洞。黑暗的机器沉重无朋
安装在河神的宝座,压住心跳
哦,矮山脉下沉,不见了踪影
像新生的鲸鱼躲在不见天日的
村庄旁边,等候捕杀它们的人
幽灵一样,出现在
暗流涌动的村口
无物不在剧变中
一切都交给了文字
而文字犹如光中沙砾
烈日悬空,万物发软,空气变硬
江水像一泓来自迷宫的甘泉
在汪洋的远方
凝固为玻璃海
甲辰夏日断想
写下不少向外的尖锐诗歌
但我还是迷恋
自足的内心生活
其实,我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得用诗歌推荐给读者,而且诗歌
更应该与我的影子
与书本,与语言本身
与众多伟大的幽灵或神仙对话
——把每个字放入火里去烧
放入血液去爱,放到孤独中发现光
如果它们还不变味
再写到纸上
我不相信人创造的事物
有永恒的结局,但我像所有
不安的人一个样儿:一直在用骨肉
铺设道路,用泪水清洗天空
相信神灵会附体,自己
有着超越自身的能力
而最终又止步于
遗忘、月亮、音乐
苍老、忏悔、枯坐
死亡和哀伤
昨天,我从亚热带丛林
探秘归来,攀上了三座鲜有人迹的
雾中山,看过了几座土司王陵
听到了不少没有文字记载的神话
做了长篇累牍的调查笔记
突然觉得,从今天开始
除了再写一些自己找到的文字
我应该像一个暮年还俗的长老
把生活早一点托付给——
遗忘、月亮、音乐
苍老、忏悔、枯坐
死亡和哀伤
斜光里的鸟群
身上佩戴白银
像转移中的一个星系
翅膀上托着镜子
像超现实的洞窟群在飞升
鸟群自成宇宙,虚空中
因此产生完善的实物
而忧伤是永恒的。鸟群消失
地上全是太阳的羽毛
过白雾镇
一匹白马驮着白银
要从溜索上过江
担心白马因为四蹄空悬而发疯
他们杀死了镇上所有的黑狗
挖开祖坟,用药水清洗
先祖的遗骨——原因是又有儿孙
患上了重病。姑娘丢了魂
他们责怪领她外出的人没在清晨
用暴雨冲洗眼睛,得吞服
雨水熬成的十碗稀粥
给古庙重铸佛像
有人托命于黄铜但把黄铜
软化成了自己
彼此有着相似的面容
赤蟒来到镇上,圆滚滚的躯身盘起
一座高塔,不少人吓得魂不附体
老先生念着古咒
领着他们焚烧大江
燃烧的粮食和旧衣服
堆在几十条竹排上
像一支孔明的部队等候东风
而东风未至
竹排载着灰
漂过烹象台和剥虎滩
漂到了狼烟中的北缅甸
黄 叶
有几片黄叶在飞旋,不知
是什么树上的黄叶。手和脸
也不曾觉察到风,但黄叶一直
悬浮在空中。密林的一端
是片空地,离开落日的两只白鹤
站在那儿:一只伸长了脖子
眺望着落日——围着落日翻飞的
鸟群还没有解散——不安之美
凝固为沉郁。另一只鹤暗黑的喙
插入镶金的草叶,轻微动弹
没有啄食,似在翻找折断的羽毛
它们的身姿仿佛是另外空间的人
变的,今天的人没有这般脱俗
身上的白色逐渐减少,让人怜爱
又让人心死。柚木的阔叶和
榉树高出众树的树干,受光最多
折光投向空地,使之像陷进黄昏的
舞台,有戏剧即将上演。而静止
阻止了一切:落日落尽,白鹤变黑
变小,逐渐隐去。空地上
我手握燃烧的松节火把
在蟋蟀和夜蝉的叫声中
静候那几张黄叶落入火焰
雨前的寂静
山上的受造物,每一种都可以
选为困鹰山的灵魂
这场还没有落下来的雨水
一座想象的建筑将以它倾斜的屋顶
接住,并转移到屋顶下成排的
水缸内。水缸里的火
早晨还在烧毁缅语抄写的经书
英语撰写的金矿开采报告
1961年,几个汉族书生记录下了
从阿佤人口头背诵的傣族叙事长诗
——《一百零一朵花》。规劝杀象人
不要磨刀了,原谅魔鬼变的仇人
勐永寺的长老,耄耋之年
瘦得像件空袈裟,但还是雨天动身
到长满古茶树的矿山走了一趟
给背诵长诗的嘴巴镶了金牙
什么是灵魂?困鹰山寨寨主
卫三木砍说:易燃易爆之物,或者
石头里的黄金,硬生生从记忆中
抠出来的一堆词语,不会滚动的
石头和死不掉的人。他还指了指
白雾里一闪而逝的闪电
说它就是他女儿选定的第二个灵魂
第一个,是勐允寺壁画里的女神
寂静其实是穹顶之下
可以指认的黏在受造物表面的一层
肉质纤维。当它收缩漶漫的边界
把受造物箍死,雨水降了下来
困鹰山人说,多少人在奔跑
想钻入灵魂去避雨。而我
暗想:需要几场这样的雨水
才能熄灭水缸里的火
雨水下了整整一个下午
从想象中回来的人,在构树纸上
书写他的奇遇,觉得这是一场
可怕的烈怒——仿佛有人
“在梦中播种射虎的子弹头!”
在受雇于他的文字中,绝迹多年的
孟加拉虎,正从勐永寺的后山松林
一头接一头地飞跃出来
幻 听
在烈日下的牛棚里乘凉
听见一山的狗叫
和一山的鸡鸣、鸟鸣、蛙鸣、虫鸣
暗自冥想:狗叫是因为所有的狗
在回应受造的第一条神犬的叫声
大声鸣叫的各位施主,也是在
回应自我类别中那受造的
第一位的鸣叫。鹤鸣也是
虎啸也是。而人的沉默,也是
在回应。这应该是一个
奇迹般的发声或沉默的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