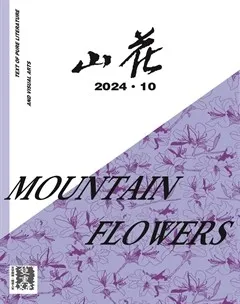天使之城的凡人歌
换窗记
称他为男孩并不准确,他二十四岁,从哥伦比亚来美国一年半,英语却已经相当够用,且没有讲西班牙语的人贯有的绕舌口音。门开了一道缝,他那张帅脸就闪现在那儿,眼睛和浓眉一样黑亮,是黑头发版的瑞恩·高斯林(Ryan Gosling),只不过更年轻。有意垮到腰下的破洞牛仔裤,白帆布鞋,黑帽衫,一抹微笑在嘴角浮现又散去,神态笃定,略带不羁。他似乎深知自己的资本,年轻,好看。他说他叫Edison。爱迪生?这名字让我忍不住想笑。在我眼里他不过是个大男孩,只比我儿子大一岁。
干起活来,我才发现爱迪生还真不是绣花枕头一只,不声不响,身手利索。同伴比他年纪略长,留着板寸,透着市井的混劲儿,偶尔看我一眼,带着鲁莽神气,那笑意也带着嘲弄。不会英语让他处于劣势,所有细节都得靠爱迪生与我交流。
他们是门窗公司派来的安装工人。
一个月前我在信箱取邮件,在那一摞广告宣传册中有一页是门窗玻璃业务。赶紧拿给房东杰伊看,我知道他一直盘算着把这三十岁老屋的玻璃窗换掉。双层玻璃,七个窗子,报价2999美元,还含安装费,免费上门估价。“这价格听起来挺诱人。马路对面的约翰家,几年前花了将近一万五千美元换窗子,跟我诉苦说压力太大,只好分了两期完工呢。不过也得小心,这只是吸引眼球的广告,真正来报价估计就不止这点钱了。”
杰伊打电话预约了估价时间,他白天上班不在家,接待的任务交给了我。
波兰裔的理查德如约上门。他长相斯文,白衬衣配棕色西装,柔软的头发三七分,中规中矩,像个中学英文老师,也像电影里看着眼熟却记不住名字的三四号配角。他的英文鼻音极重,我得连猜带蒙才明白他的意思。大概测量后,他拿出计算器摁了一会儿,9500美元,包括七个窗子和两个推拉玻璃门。“窗子没有超过报价的标准尺寸,可如果想用稍微好一点的玻璃则要加一定费用……”我暗想,这销售的套路来了。我心理上开始抵触,他那口里含着一块软糖一样的英语更听不懂了。好在他游刃有余,经验丰富,像个脾气极好的父亲熟知如何应对小孩子的不满情绪,不慌不忙回车里拿来一盏灯,插上电,把两种不同材质的玻璃紧挨着灯放好,微笑着示意我把手放过去感受温度。都是双层玻璃,一种让我丝毫感觉不到灯火的热度,另一种则灼烫得像挨着火炉。没有比较就没有贪欲,虽然贵一些,隔热效果太不一样了。“Once in a life time(一辈子就一回的事),当然用好的啊。”杰伊在电话里发话了。
“你是作家,多美好的职业!我那天去一个客户家,听说我是波兰人,他拿出一本书,居然是莱蒙特的小说《福地》,还是波兰语的,他一定要送给我。当晚我就读了一半,那本书我会珍藏一辈子。我真希望有一天能读到你作品的英文版……我也偶尔写点像诗一样的东西,为生存所迫,没有太投入精力,实在写不好。”他说二十年前他来美国是以留学生的身份来的,虽然欧洲离家更近,但他喜欢美国,就留了下来。“波兰和中国一直情感深厚呢……”
看到老猫火球进屋,他蹲下打招呼,同时掏出手机让我看他的两只猫。爱猫又爱文学,可为五斗米和居留身份折腰,他七八年来一直在这个犹太人开的门窗店打工。聊着天,我眼里的他不再只是个推销员,而和我一样是漂在异乡的过客。
“你不用非今天作决定不可,我知道七千美金也不是小数目,想好了再给我打电话。但这真是最优惠的价格了,我保证。”他信誓旦旦的折扣价和真挚的情谊让我不忍看他空手离开。一单生意,对他不仅意味着提成,还有打拼下去的信心吧?我再给杰伊打电话,当下敲定。
告别了文学爱好者两天后,一位来自委内瑞拉的大叔上门来量尺寸。他身形敦实,面相憨厚。登高爬低,一手尺子,一手本子,他熟练地把所有门窗测量了一遍,一丝不苟,像个严谨的科学家。量完了,他已经出汗气喘,我递给他一瓶水。坐在沙发上,他笑眯眯地跟我拉了会儿家常。“我当年是过来投奔我哥哥的,算起来在美国也有二十几年了。本来想看看就回去的,可是我太喜欢这儿了。洛杉矶,遍地都是机会啊,就留了下来。如今三个女儿有两个都工作了。偶尔也带孩子回老家去看看,变化是不小。孩子们喜欢那儿的文化,可真要选择,她们还是宁可在美国,毕竟,这里的许多东西是故乡没有的。因为美国强大富裕?好像也不只是,我说不清是啥……”看得出来,在无数个来美国寻梦的拉美人中,他是个幸运者。
第三拨就是爱迪生这哥俩。说好十点钟到,十点半还没有人影。我有些气急,电话打到门窗公司,一位女士说在路上了,可能塞车,请耐心等一会儿。又过了一刻钟才响起了敲门声。我提醒自己不要埋怨,反正也是晚了,被抱怨带着坏情绪干活儿对谁都没有好处。
他们也没有为迟到道歉,径直进屋,让我指认哪些窗户是需要更换的。虽然头天晚上我就已经把窗外所有可能碍事的家具花草都搬开了,爱迪生仍客气地告知我,室内靠窗的沙发也要移走。看我一个人费力地挪动那三人沙发,他主动上前搭了把手。
旧的门窗都是铝合金框架,虽然没有锈迹却也日晒雨淋变得相当难看。他们又敲又撬,摧枯拉朽一般,眼看着一扇扇窗户都只剩下空洞。还没到安装新窗那一步,他们已经大汗淋漓了,我拿出来的瓶装水却一直放在桌上,三个小时过去了,他们都没顾得上喝一口。我有点小小的感动。
“要不要来点音乐?”我坐在沙发上翻看着新到的史密斯森尼杂志,想起以前安装木廊的墨西哥人喜欢边干活边听热闹的西班牙流行歌曲,我边问边打开电视上的潘多拉音乐盒。
我们偶尔也聊几句。
“你叫哀米粒?很可爱的名字,和你的人一样。”爱迪生说。他正切割着一道过宽的门框,打量我的眼神似乎真诚又漫不经心。
“你来了一年多了,回去过吗?”我问。
“没回过。原因?你知道的。”
“没有身份,回去怕回不来了?”
“嗯,当时以游客身份来的。”
“听说你们那儿毒贩猖獗,是吗?”
“嗯。”他没多说,只微笑了一下,似乎见怪不怪。
他说他24岁了,梦想能多挣点钱,有个自己的家自己的住所。现在他和另外三个老乡租住在洛杉矶市中心一处民宅里。为了挣钱,他几乎没有周末,去过的几个观光点也都是星光大道、好莱坞山、圣莫妮卡海滩这种不要钱的地方。发了照片给家乡的伙伴,仍是被万分羡慕,他可是在洛杉矶啊!
“我现在只会安门窗,没别的技能。每小时十块钱,真不够花。”
我有些吃惊,记得理查德说这两个推拉门的安装费就需要1600块,公司却只付这两个没有身份的小伙子每小时十块钱?!
我忍不住告诉了爱迪生。他仍淡淡地嗯了一声,没有一丝吃惊或沮丧,手脚不闲地干着活。
我说洗手间的三个窗子其实也需要换掉,如果他能自己接活儿,就可以交给他做。
“嗯,可以的。”他并没对这赚钱机会显示过多热情,只说他确实可以找到更廉价的玻璃。
“那你量一下尺寸。”
“等我干完活儿吧。”
看表,已经快两点了。我问他还需要多久才完工,他说至少还得四五个小时。
“午餐你们怎么解决?”我问,我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我们去买个汉堡填肚子。”他答道,半立半蹲在厨房柜上,正给刚拆掉的门框补腻子。
“我打算做鸡蛋三明治,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可以为你们每人也做一个。”
他翻译给正在用切割机裁切门框的同伴听。
“谢谢。”板寸笑嘻嘻地望了我一眼。
半小时后,我们仨在厨房围桌而坐。除了三明治,我还给了他们每人一罐冰啤酒。
“哇!太好了,他喜欢喝啤酒。”爱迪生指指同伴,也痛快地呷了一口。
“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我自己的过去。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也远离家人,独自漂泊过。别灰心,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是实情,之所以说出来,似乎是想给他们一个理由,为什么我们仨坐在一起吃我做的三明治。
在世间行走,从不识愁滋味的少年,到遍尝人情冷暖的中年,每逢看到年轻的生命,回顾自己的来路,我都忍不住放下戒备,暗自提醒自己——要藏起身上的伤疤和心底的坚冰,让这羽翼还未丰的小鸟感受到同类的温暖和善意。就像那次我在网球场捡到一个钱包,费了不少周折才找到了那心急火燎的失主——一位刚参加了毕业典礼的高中生,那还温热的两千块钱是亲友们送他的毕业祝福。为表达失而复得的感激,少年送我一个星巴克的咖啡壶,还发来信息致谢,我回复他:“不用谢我。我希望,我相信,你也会做同样的事。请把善良的种子传递下去。”
我希望这两个异乡寻梦人,有朝一日过上了期许的生活,某天递给陌生人一杯啤酒时,会想到这次夏日的午餐。
啤酒,两人都喝光了。三明治却都剩下了,里面夹了煎鸡蛋、西红柿、奶酪、生菜叶,我猜因为没有肉,两个干重体力活的人吃得有点勉强,又不好意思让我看到,剩下的一小团都包在餐巾纸里放在桌上。
我洗刷碗碟,他们继续干活儿。
“Do you like dancing(你喜欢跳舞吗)?”爱迪生在客厅窗前清扫着切割下来的碎屑,抬起头,黑眼睛匆匆瞥向我。
“我不喜欢,也不会。”
“我可以教你。我的家乡人人都会跳舞。”
“你在哪儿教我?”我有点莫名其妙。
“哪儿都行,沙发,床上……”他微笑着又望我一眼,继续专注地干手里的活儿。明明是在调情,却一点也不轻浮,真诚得像真的在谈舞蹈。
我假装没听到,去后院清扫一地的碎屑,有点后悔给他喝了酒。
我曾在这座城市大学修过一学期英语写作,班里一位女生就来自哥伦比亚,她在美国嫁了一个黑人,不时跟我们秀恩爱,“我才不敢从我家乡找丈夫呢。许多人在那方面太随意,我受不了不忠诚的两性关系。”可我万没想到这在美国的“黑户”小伙子竟随时随地可以约人“跳舞”。
近四十度的暑热让人昏沉欲睡。门窗洞开,没开空调,T恤湿透了。我上楼去换了短衣短裤,心中奇怪对这陌生男孩的挑逗我竟没有丝毫气愤。年少轻狂,有他吃亏的时候。我甚至有些为他担心,不由得想到我那远在家乡的儿子。
“你穿牛仔短裤很可爱。”他正用清洁剂擦玻璃,扭着脸欣赏地打量着我,似乎很自信他的夸赞会打动任何女人。
我笑笑没接话。
“要是我说have sex with me(和我上床),你会说什么?”
“我会说不。”我哭笑不得。写作者的好奇又让我想知道究竟他在想什么。
“为什么?那是多么美好的事啊。我长得不好看吗?”他仍没停手地在干活,口气单纯得像在问我为何不喜欢看美式足球。
“你都不了解一个人就……”我反问。
“那怎么了?如果有人跟我这么说,我就不会反对,只要觉得对方可爱就行。”
“那之后还见面吗?”
“没机会就不见了呗,俩人在一起快乐就好。”
“你不担心自己被染上病啊?”
“不会,我会小心,有保护措施。”
“那对方要是怀孕了呢?”
“那就当爸爸呗,我会尽力做一个好爸爸。”
……
我心里明明已经大叫荒唐,可表面上还假作镇定,跟他若无其事地聊着,只不过我的口气越发认真得像个规劝儿子的母亲。
我知道,他妈生他时才十六岁,几次想来美国都被拒签。
“我和你不一样,我如果与某人have sex,一定得是与我相爱的人。”我试图纠正他的三观。
“当下的快乐多容易得到,很简单。爱一个人就复杂得多了。”
“抱歉,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将来你会受伤的,也会伤到别人。”我觉出自己的声音有些激动。他仍是有条不紊地干着活儿,声音不疾不缓。那干净真诚的微笑如烟头一般若有若无,总是那么笃定自信,像一棵在沙地上扎了根的小树。
他不再说话,只是安静地干活儿。
六点了,安装结束,打扫残留物、把工具和旧门窗装车,二人准备离开。
“你还没量那三扇窗子的尺寸呢。”我提醒他,希望他能抓住一个挣钱的机会。
“我太累了,改天吧。”他淡淡地说,脸上就像蒙了一层透明的灰,眼睛不再如早晨那么黑亮。他瘦削的身影似乎也松懈缓慢了,像刚经历了一场精疲力竭的战争。80美元,这是他这一天的所获,还不够三口之家在CPK(加州披萨厨房)吃一顿披萨。
看他们开着那二手皮卡走了,我回到屋里。窗明几净,地上被打扫得没有一丝垃圾废料。这屋里似乎根本没来过外人。
“活儿干得不错!”杰伊下班回来满意地夸道。
我没跟他说起那关于“跳舞”的讨论。他也许会恼怒甚至打电话给门窗公司投诉这“色魔”。
散步经过的邻居们都大赞,说换了门窗就像换了个新家,跟我要电话也打算换,“指定要给你干活儿的这两个伙计。”
两个月后,波兰人理查德打来电话做售后调查,“爱迪生呀,他不久前回哥伦比亚了。他妈妈被一个男人强暴,差点儿送了命。他扔下正在干的活儿,疯了一般赶回去了。大家都劝他别回,这一走肯定就回不来了。公司老板挺舍不得他,干活儿最麻利的家伙呢……”
厕所那三个小窗子仍是旧框旧玻璃。背阴,爬墙虎很快用细韧的脚爪攀爬上去,为那小窗覆盖了一层好看的绿色风景。
偶尔,我会想到那双再也不会相遇的黑眼睛。
Los Angeles, 这世人皆知的天使之城,日夜唱响的,不过都是凡人的歌啊。
卖车记
“我有五个孩子,来自四个不同的母亲。我结过一次婚,在驻德国的军中服役时,爱上了一个德国女孩……”坐在我面前的他六七十岁的样子,年轻时也许并不矮,如今老来发福,显得敦实疲沓,像任何一个干体力活儿谋生的美国老人。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肚子,汗水从脸上一道道地流下来,那贴在身上的蓝白条纹T恤也湿透了前胸后背。如果说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便是那双灰蓝的眼睛,闪着快活与狡黠的光。
他叫格雷,上门是为了买车。
老猫火球轻手轻脚地从楼上溜下来,生怕引起别人注意似的,它比往日更麻利机敏,瘦长的橘色身影像一块移动的日影,只一眨眼就钻过那开着一条缝的推拉纱门,跑到后院树丛中了。我似乎听到了蜥蜴们仓皇逃窜的窸窣声。
没错,这有点戏剧性的买车场面,我猜也许都是这猫暗中导演的。
我不久前读了一部日本小说,作者相信猫是有神性的,说对猫族的触怒会引发意外甚至不幸。正将信将疑,杰伊就用亲身遭遇验证了这句话的可信度。当年这小猫被他从动物收容站带回来时不过巴掌大小,像一块橘色的炭火,故取名火球,十四年来人猫相依为命。都说橘猫高冷,这火球更是没有丝毫媚态,不能容忍被撸被抱。晚上睡觉时倒会与主人同床,但也是缩在大床临门的一角,似乎时刻准备夺路而逃。曾有一次,杰伊想给爱猫剪趾甲,刚摁住脚爪,胳膊上就多了几条血道子。从此杰伊再也不敢以主人自居,任那猫把皮沙发当猫树,抓出许多划痕。兽医店寄来的明信片显示,该给火球打疫苗了。领教过那利爪的尖锐,知道那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杰伊心虚地戴上建筑工人用的硬皮手套,楼上楼下气喘吁吁地人追猫躲。半小时后,人猫大战以猫的险胜收场——火球拼死反抗,最终逃过了被塞进猫笼的命运,代价是恐惧绝望地嘶叫着尿了一地。杰伊无奈地摇头认输。记恨的老猫当晚果断与他分居,躲在沙发底下睡了一夜。
第二天下班途中,杰伊的银灰先生(Mr.Silver,他对那银灰色SUV的昵称),在高速公路上突突冒着黑烟瘫痪了。
二十七万公里,相伴十五载,远比许多夫妻相守的时间和路程都长。杰伊是个很恋旧的人,穿出破洞的T恤都不离不弃,实在不能穿了才洗干净叠起来收放在抽屉里。父母离世,唯一的弟弟也在外州,很是疏离。孑然一身的他如今又要与这老伙伴道别了,其不舍与难过可想而知。
街对面那位美日混血的退休警官约翰是个车迷,单身一人却有八辆车,全是他买下自己修配的旧车。“我估计是发动机坏了。修理费用低不了。买新车,现在不是时候,瘟疫还没过去,全球芯片短缺呢。”约翰打量着杰伊的车说道。不经意般望一眼路边他的几辆宝贝,像存有足够余粮的地主,隆起的肚子下是藏不住的底气。
好在杰伊还有辆平时通勤舍不得用的宝贝——车库里那辆双门的野马跑车,上班代步还不至于成问题。说好周末我陪他一同去车行看看,和许多务实的美国人一样,他想买辆皮卡,超大空间可以满足所有需求。
展厅里空荡荡的,往日西装革履恭候着的销售人员也不见踪影。杰伊去跟那歪坐着看手机的前台小姐搭讪,过了一会儿,才有一个穿制服的小伙子出现。“所有车型都缺货。你提到的那款福特皮卡定价5.8万美金,要等六到九个月才可能到货。预估啊,我不能打包票。”
“这5.8万是最终费用吗?”我问,想起以前买车是有还价余地的。
“不是。除了约10%的税,还要额外加五千美元的浮动费用,供不应求,目前所有车行都有这样的加价。”
我留意到各车行外墙上收购二手车的标语比往常更醒目。有些车行甚至特意标明:收购所有旧车,即使不买新车。
新车买不到,旧车总得找个出路吧?杰伊说他已经跟拖车司机咨询了,这样的不能开的二手车如果卖给车行,最多也就是五百块钱。如果拖到指定车行去修,就成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要价多少你都得修,否则你只能再雇车把这病车弄回家。
杰伊为人厚道单纯,遇事又总愿跟我商量,这份信任让我越发不敢辜负,我搜索着大脑中所有的“人脉”。“找阿勒克斯问问吧,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奥迪车行上班。好在我有他的微信。”是的,那是个鲜见的用微信的美国人。其实,跟这位阿勒克斯我还真算不上认识,一面之缘也纯属偶然:我去给一位华裔朋友的车做保养,回家后发现副驾驶座椅上有一把陌生的车钥匙,显然是另一个车主的钥匙被放错了地方。给车行打电话,不到十分钟,一个挺拔帅气的小伙风风火火地赶到了。
“哇,这花园收拾得真漂亮,太美了!”他显然是个很会讨人喜欢的年轻人,“我对这条街太熟悉了,我当年就是从街尾这个小学校毕业的。你前院这棕榈树以前还没我高,现在都超过房檐了!”他说曾与上海一家公司做过远程合作,希望有机会真的到中国去工作。他喜欢中国美食,也用微信。于是我们加了好友。
和许多萍水相逢的人一样,我们愉快道别后,像两滴水,各自融入了完全没有交集的河流,连个招呼都没再打过。
临时抱佛脚,我试探着给阿勒克斯留言。很快他就回复了,说没错,杰伊的车如果卖给车行,也不过几百块钱,他认识一位修车技师,可以上门看一看车的故障再作决定。
“是免费上门吗?”我知道美国就连水管工上门看一下故障都要收费75美元,没人愿意白跑路。
“当然是免费。他是我的朋友。”他爽快的回答让我暗自庆幸,保留着一面之缘的朋友多必要啊。
几天后他和穿着蓝色工装的小伙斯本思出现了。二人都友善、热情、幽默,和杰伊一边熟络地闲聊一边打开发动机盖,用各种笔一样的工具查探着,很快确认银灰先生果然是犯了心脏病,发动机坏了。
斯本思承诺回去找找旧发动机,到时候他可以在自家后院修车,成本会比车行低很多。
“斯本思找到了一个发动机,只跑了六万英里,要1400块,修理费600块。他说他不会像有些人中途再加价。你说我修不修?”几天后,杰伊下班回来说,“他还说可以保发动机一年。现在买新车难的情况下,修好了我至少可以先开着。”
“听起来是不错。我记得他说发动机的新旧决定价格高低,可否问问他如何看出发动机的年头和跑过的里程?”听我这么问,杰伊有些犹豫,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出他的意思是既然用人家就要信任,不要那么多疑。
“你知道,这不是信不信任他的问题,他也会被别人蒙骗啊。”
他同意问一下。
对方回答很干脆,“你没办法从一个单独的发动机上看出里程和年头。”
“就算是摊上了一个老发动机,如果能跑一年半载也不错。修好了再卖,至少可以卖三四千块。” 杰伊边自我说服边下决心修车。
“理论上没错。可是,这车既然已经跑了二十七万公里,保不齐别的部件也会出毛病。到时候搭进去的钱可就不止两千块了。”听我这么一说,这没主见的摩羯座感觉在理,便没坚持立即修车,继续开着那野马代步。
半个月过去了,那天我在前院浇花,看着趴在路边的Mr.Silver身上已经满是灰尘和鸟粪,不觉心疼。初识杰伊的那年,他就开着这灰马,坐在车里冲我微笑。狗与主人同居一室久了,从性格到外貌都会越来越像主人,就像人们常说的夫妻相。在我眼里这银灰的车和杰伊一样素朴、干净u4q7rqwo3zRoipdGoxcmUA==、安静。如今它没用了,就要离开了!我叹息着安慰自己不要太多愁善感,人生不就是或早或晚的无数场聚散吗?于是把浇花的塑料胶管接在水龙头上,给这老马彻底洗了个澡。尽管心脏停跳,它仍那么体面谦卑,良善无辜,让我想到枯死后仍在天地间挺立着的树。每次看到荒原上从容静立的枯树,我都会轻抚那没有了生命的树皮,仰望着它感慨——无一例外,死树比死人好看,也比死人更有尊严。
想到美国的旧货交易网Letgo(放手),死马当活马卖,我随手把老马的照片发了两张上去,并附了简短的介绍:相伴十五载的老马,心脏停跳,其他部件完好,外观干净无任何划痕。有能力医治者请联系……没想到,立即就有好几个人留言。车还可以跑吗?可以比1500块便宜点吗?
杰伊下班回家看到那则售车广告有些吃惊,他没想到居然还真可以在网上卖旧车。“不同于其他旧物售卖都不限数量,这网站每月允许个人免费卖一次车,否则就要付费。”其实那也是我才刚知道的规定。
“你形容这车就像我的马?”他读着那则短短的广告,理工男似乎有些不适应这文绉绉的描述,惊讶地笑着道。
“我只想说明你这车一直是自用,突然出了故障了,不像那些买卖过七八回倒了无数次手的车,更让人放心啊。我自作主张标了个价,最后卖不卖都随你。”听我这么解释,他也释然了,夸我比他这当地人还能应对这些麻烦事,全权委托我来谈判。
有人报价1300,我说不行。有人让我回复一个网络电话,被杰伊识破是诈骗。只有一个人很豪爽地说他要这车,并且付cash(现金),还留下电话号码要求直接联系车主。
几天后,格雷来了,带了一个朋友来看车。“这家伙太棒啦!”他背着手笑呵呵地绕着车转了两圈,像马贩子相到了中意的马儿,说他要定了这车,过几天雇辆拖车来拉走。“我这一辈子修了至少五百辆车。哪儿坏我都能修。许多人直接跟我订购旧车。也真巧了,几天前就有个女士说要一辆车,不能是黑的白的,只喜欢灰色的,只要四缸的,只喜欢SUV。你这Saturn(土星,美国本土品牌)占全了!这车虽然早在2010年就停产了,可质量相当棒呢。”
我立即喜欢上了他。不是说吗,成年人身上的孩子气最可贵。褒贬是买主,他活了一把年纪,对卖家那么坦率,挺难得啊。杰伊也很高兴,三五分钟似乎就把生意谈妥了,开始闲聊。听说杰伊出生在弗吉尼亚一个兵营,老人更开心了,“天哪,那是我当兵的第一站!你父亲也驻过德国?太巧了!”
晚上杰伊特意请我去吃了墨西哥餐庆祝,说他其实并不介意卖多少钱,给银灰先生找到一个懂车的买家就不算委屈了它。
回家碰到约翰,被他泼了一勺冷水,“我从不相信网上交易,猫腻很多。你们还是小心为好。”
杰伊安慰我说可能是警察多疑吧,也许并不会出什么意外。
一周过去了,格雷没有了动静。
杰伊给他发信息,他回复说“咱们还没谈好价格”。
我顿时像被蝎子蜇了一下,生气地说他想讨价还价为何磨蹭到现在?
杰伊一直调侃我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根据封面判断一本书),看来我这天真的毛病确实没改。
他问格雷出价多少。
“1100块?不行。大不了我找人修修继续开。”杰伊这老实人也有些不悦,但他很沉着,反而劝慰我,“不必在意他如何压价,关键我要想清楚多少钱是我的底线。我们人类都有自我保护或者说是贪婪的本能,你用不着生气。再说,他是靠倒腾旧车谋生。”
那老江湖似乎更沉得住气,只留了一句“孩子你考虑一下吧”,就再也没声息了。
阿勒克斯倒是给我发来一条信息,问是否还打算修车。他略嫌过分的热情加上与克雷的不悦经历让我对他也产生了戒心,回复他说杰伊打算卖车。
被晾在中途,好马也得吃回头草,我问之前那位报价1300的是否还有意买车,没得到回音。
热度只保持了一周,网站不再推送这条车讯,问津者更少了。
过了两周,杰伊又考虑修车这条路了。我再次把车挂在了网上,毕竟一个月过去了,可以再发一次卖车帖,这次标价一千三百块。
“我只有一千块,卖吗?我还需要搭钱修理。”有一位似乎很诚恳。
得到我否定的答复后,他说,“你如果未来卖不掉,请再联系我。祝你好运。”这位的真诚让我突然很踏实,似乎一下有了底气,实在不行,一千块有人托底儿啊。
“我还是再问一下格雷吧。毕竟他来看过车,算是最有可能的买主了。”杰伊很快得到了回复,1250块!
Done(成交)!
三天后的周末,敲门来提车的并非那老江湖,而是一位年轻性感的女子,一件吊带粉背心,露出肩头的黑色文身,刚遮住臀部的牛仔短裤,裹着小麦色的结实修长的双腿,脚上是一双牛仔及踝短靴。
她双眼明亮,一笑便露出洁白的牙齿,大方地进门,坐在了桌旁准备和杰伊完成交易手续。
“你是格雷的女儿吧?”杰伊微笑道,把几张打印好的文件递过去。
“我不是。”对方也明朗地一笑,说她叫马丽莎。
“那你是他儿媳?他说过他儿子今天一道来。”
“也不是。我是他儿子的女友。我永远成不了他儿媳妇,因为我从来不相信婚姻那一套。和一个喜欢的人过日子就够了,尤其是我认识了格雷这家人……你别看他像个粗人,心可细呢,每换一种狗粮,他都不放心,要亲自尝了才给狗吃。我相信我男友遗传了他老爸的基因。结婚了不开心还得离婚,许多时候turn ugly (丑态百出)……”她仍是明朗地微笑着,声音好听,语速却极快。看到我正在擦拭从一个古董店淘到的朗费罗的诗集,她问是否可以翻一下。
这时格雷到了。“我的天,这家很漂亮啊,这么多油画和瓷器。”说着他流着汗一屁股坐在餐椅上,自来熟地笑着接过我递给他的冰水,用粗壮厚实的大手拧开瓶盖,那指甲边沿有一圈深色油渍。他仰脖痛快地喝下一大口,骂了一句鬼天气,好像他不是来买车,而是来串门的邻家大叔。
看我对他的人生故事那么感兴趣,老人更来了兴致,“娶了那个德国女孩,回到美国,不到两年就离婚了。她不解地问我,洛杉矶,这天使之城怎么这么土?城里是平房,郊外是马厩。她是个都市女孩,根本不习惯牧场里的生活。孩子都留不住她,趁我开卡车给超市送牛油果,她买了张机票飞回了德国。后来陆续出现了几个女人。有一个喜欢上了我那会说甜言蜜语的邻居,跑了。有一个讨厌我和前妻的孩子,分了。有一个相处得还行,就是不能接受我那么爱旧车。我眼里的这些宝贝在她看来就是一堆丑陋的废铁……这些女人们现在都在哪儿?天知道,分手后都消失了,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凡是怀孕了的我都求她们把孩子生下来。她们不要我养着。人们总说lovers come and go , friends stay(情人来了又走,朋友永在),可是我觉得孩子们才是最亲最近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天使……”格雷说得口角起了白沫,在马丽莎的轻声提醒下用手背抹了一下。
“说实话,你们贴在网上那几句话打动了我呢!车,真的是和马儿一样,你对它好,它就跟你亲,就毫不含糊地为你东奔西走,比一些没良心的人强多了。”他口无遮拦地说着。我对他精明算计的厌恶感消失了。
马丽莎小心地翻开那诗集,长长的睫毛垂着,认真地读着那些配插图的诗句,似乎她不是坐在陌生人餐桌旁签购车合约,而是在街心花园捧读着心爱的小说。我发现她的侧影很美。她忽然抬起头,“格雷,我能不能借你手机用一下,我想把这几行诗拍下来。我喜欢。”格雷的诉说被打断,依言从腰包里翻找,却心不在焉地递给她一张二十块纸币。“这不能拍照吧?”我们都望向那举着钱的老人,放声大笑起来。
透过百叶窗,我看到一个身形结实的男子正在麻利地用缆绳固定汽车,还有一个年轻孕妇立在一旁看着,她一脸天真的快乐,像个还没长大的孩子。“那是我的小儿子和他的侄女,我大儿子的女儿。她还有两个月就生了,男友可是个相当不错的小伙呢。我的家人跟我一样,在意彼此,却不指望靠一张纸维系什么。在一些人眼里,我们是一家怪人,从不去教堂,也不指望政府,我们彼此照顾,对吗亲爱的马丽莎?”
也许是开心于买卖终于成交,格雷显得很放松,兴奋地继续掏心窝子,“我现在不亲自干活儿了,打算秋天去自驾,到东部玩儿它俩月。谁知道呢,我盼着遇到一个对脾气的女人,也许能就个伴儿……”他灰蓝的眼睛清澈得像个憧憬未来的孩子,与那足具街头智慧的老江湖完全是两个人。
这样的场面作为卖车的结尾,让我欣慰。
他们来之前,我已经让杰伊站在Mr.Silver旁边留了影。暮色中,看着它伏在拖车上消失在拐角,那稳稳的,干净的灰马,我湿了眼眶。怕杰伊看到也跟着伤感,我蹲在草坪上,假装低头拔掉几棵入侵的三叶草。
此后再上路,看到与银灰先生同样的车,我总忍不住细细打量那车牌号。如果有缘再见,我特别想看清它的新主人是谁。但愿,这老马仍被善待,干净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