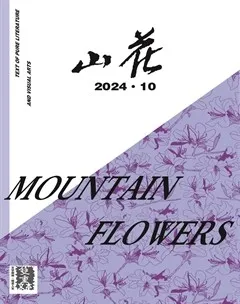暝色入高楼
当年,这爿酒店所在的地方还是一片瓦砾场,附近孩童常于黄昏时分到此“探险”,围观人群中偶尔也有她的身影。此刻,从八楼窗台望出去,街道纵横,楼房林立,宛如水泥森林。蒙城不再是当年那个只有一条主街的小县城了,某些地段的繁华程度与省城相比也毫不逊色。站到酒店顶层平台上,大概还能望到法院后面那幢七层小楼,它早已被笋群般密集的高楼摁进底部,那破旧的蓝灰色外墙——想必蓝色部分早已暗淡不堪,灰色却在加深,已然辨不出本色。
而她的小姨还住在那七层楼房的顶楼,没有电梯,每日徒步上下。
上一次见小姨还是六年前,廖青回蒙城过中秋节,恰好小姨来给母亲送月饼。几年不见,小姨见老很多,原本大而水润的眼睛无端缩小了几分,杏仁眼儿垂成三角眼,看人时神情恍惚,好似眼前蒙着一层阴翳。这些年廖青目睹身边亲人的老去,头发逐渐花白、稀疏,原本紧致的脸庞像沙丘那样塌掉,双眸瞬间暗淡下去……好似有神秘光照从他们身上移走。那次,静默不语的小姨似有话要和她说,但直到离开她们也没能找到安静的角落坐下。母亲屋里来了很多人,亲戚间的交谈大多夹杂隐隐的炫耀与排斥,早已不再纯粹。
自大学毕业定居外地,廖青与家人聚少离多,小姨和姨父的事还是母亲在电话里陆续告诉她的,民政局都去过不下十次,吵吵嚷嚷大半辈子过去了,还是照旧。在亲戚们眼里,小姨付出太多,俩人只要交换位置——如果倒霉的是小姨,姨父恐怕早就逃之夭夭了。
如果不是单位来此地举办业务培训会,廖青也不会在这个时间段回老家。所幸课程安排极为松散,小半日学习,大半日考察——说是考察也就是去本地新造的景点看看玩玩,她倒想趁此机会逛逛老城区,在那些仍保留着原貌的角落里或许还有过往记忆的残留。
这是九月,时令已过白露,但夏的余威尚存,两股势力来回交战,暑热和寒凉此起彼伏,让人颇有些坐立不安。那日下午,廖青请假在酒店房间睡到三点多,醒来时,窗外传来闹闹哄哄的声响,一些声音夹杂在另一些声音里,好似童年的早晨听见屋外有大人在说话,诉说着她入睡时外面世界发生的事。
小姨的脸忽然浮现于脑海,鲜明如昨。恍惚中,廖青起身推开房门,下楼走出大厅,走到那条通往大坝的路上,被汹涌的车流拦截在逼仄的某处,她才想起房卡还遗留在酒店房间里。那几年,她经常遗忘的是钥匙,小姨家的钥匙,被一根红布头拴着,或放在书包边上的侧兜里,或被她丢在学校宿舍里。
小姨住大坝附近,丁字路口左拐,走一截水泥路便可看见。小区在右手边,外墙贴蓝灰色马赛克瓷砖,所有窗户外都装了铁丝笼似的防盗窗,她每次都能不喘气地走到四楼——那个高度恰好可眺望大坝那边的珠游溪,褐色飘带似的恍惚的一条,无论晴天还是雨天都泛着不同程度的波光,只有下雪天才会出现那种杂乱交错的闪光,让人分不清何处是雪、何处是岸。
蒙城很少下雪,一旦空中有雪花飘落,学校八成会停课,大人小孩过节似的躲在家里看雪。那些夜里,小姨会做火锅给她吃,煮一大锅骨头汤,放入肉丸,大虾,土豆片,冻豆腐,白菜叶子,粉丝……各种菜肴在锅子里乱闯乱撞,水蒸气也在屋里游荡,升腾,直到被天花板截住去路。窗户玻璃上尽是淋漓的水珠子,奔走,破碎,又重新聚拢到一起。雪花的到来让廖青莫名地兴奋,每次看见都像是第一次见。小姨在做手工,手持钩针上下翻飞,不一会儿工夫便变出一簇簇艳丽、繁复的绒线花瓣,就像窗外雪花的游戏,飞舞,盘旋,弹起,最终归于广阔无垠的大地。
亲戚们眼里小姨的好日子在住进这幢七层楼房前就已戛然而止。可她依然每天穿着高跟鞋爬上爬下,一路发出清脆、明亮的声响,实在匪夷所思。“我们就不上去啦,楼太高,爬不了。”每次,他们奉外婆之命给小姨送来东西都站在楼底下如此仰脖说道,好像那不是人间七层楼,而是天上广寒宫。
没有电梯的七楼全城大概只此一处,但小姨的七楼比一楼便宜,还有赠送的阁楼面积,大不了走到四楼,歇会儿,喘口气也就上去了。年轻嘛,力气还在不断长出。那会儿,她和小姨都不怕走七楼。
七楼之上的阁楼上有天窗。
某些夜里,月光与星光垂直照下,洒落在床榻和地板上,就像天外来客。婚前的小姨有过一段好时光,人人都说她很像挂历上的某知名女明星——头发乌黑,一支独辫垂在胸前,杏眼微露,含情脉脉——小姨也是标准的杏眼儿,也喜欢梳独辫,或将辫子放在脑后甩来甩去,或含蓄地盘在胸前。小姨比那个女明星还多了几分古典气质,廖青读《红楼梦》读到“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那几句,感觉说的就是小姨。
当年,小姨还是那个刚从学校毕业分配到环保局的技术员,周末会骑自行车来找她玩。她带小姨去后山,满山满谷都是果实和花香。春兰,杜鹃,栀子是她们的采撷对象,柿子,青梅,枇杷以及不知名的红色野果都在山风中恭候她们的到来。蒙城既靠山也临海,而小姨家住海边,很少见到这些,稀罕得不行。有一年春天,俩人上山采茶,茶树排列似几何造型,每列间都留有空隙,她们摘累了便铺一张席子坐在那空隙中吃东西,聊天。小姨向她倾吐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她回到家,好几天都没缓过神来。没想到小姨会和她说这些。她似乎明白了小姨脸上忧郁表情的由来,一个人经历过那种事情,终归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给小姨做媒的人很多,但她要看过照片才决定是否见面。小姨订有《电影画报》,里面的明星照被她悉数剪下,分门别类贴在牛皮本上,多年后那个泛黄的本子才落到廖青手里。
遇到姨父之前,小姨正式处过两个男朋友。一个是中学数学老师,分手的原因居然是那个人在陪母亲看病途中,还和黄包车夫讨价还价,为便宜区区几块钱平白浪费宝贵时间。小姨认为自己不能和那种情况下还锱铢必较的人生活在一起。另一个是医院里的外科大夫,手指白皙修长,像捏绣花针的女人的手。这次分手,小姨的理由是闻不惯那人身上的消毒水气味,什么时候都有那种味儿……可她怎么能要求一个医生不携带来自医院的气味呢,这分明是找茬儿。
二十九岁上,小姨才结了婚,算是晚婚了。姨父在国营酒厂当推销员,天南地北地跑,不仅口才好,赚钱多,朋友遍天下,更重要的是相貌惊人,就像从《电影画报》里走下来的,甚至比那上面的人还要俊俏几分。
这次小姨似乎心满意足了,只有廖青知道是怎么回事,姨父和那个人实在太像了,不是具体的眉眼,而是身上所携带的气息——哪怕她只瞥过一眼集体照上露出的一个灰蒙蒙的人头。当年,小姨和同宿舍的女孩爱上同一个人,可那个人似乎谁都爱,又谁也不爱,不明朗不拒绝。同宿舍的女孩轻生后,小姨烧掉三大本日记,算是与过去告了别。这是茶山上小姨附在她耳边说的。此后,她背着小姨的秘密前行,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
小姨下班后哪里也不去,就坐在姨父单位分的公房里打毛衣,还用钩针编织帽子、茶杯垫和沙发巾。房间里除了带流苏花边的装饰物,最醒目的还是结婚照。镜框里,小姨双目含情,脸颊灿若桃花,而姨父一身正装,戴着金丝平框眼镜,一副大明星派头。人人都说,这结婚照更像电影剧照,好像这俩人不是真结婚,而是表演结婚。
车厢式结构的爱之小屋很快被姨父单位里的人收走了。那是他们结婚两年后,小姨做了母亲,一岁的小表弟刚刚学会走路,姨父将采购款挪作他用,且数额巨大,即使把所有亲戚的钱都凑到一块,也堵不上那窟窿眼儿。
某个春天的下午,廖青一家三口乘坐出租车去邻县看望姨父,他还是那么帅,甚至因脸庞、身形都瘦了一圈带了些憔悴和落魄的神色,还更显帅气了。姨父在里面自学会计,帮着他们记账,还教一屋子的人读书、认字。那些人没有文化,而他有。管教警察器重他,对他很好,他吃得也好,顿顿有肉。说这些话时,姨父脸上甚至洋溢着笑意,似乎为自己在任何地方都能获得优待而得意。姨父没有戴镣铐,没有苦大仇深的表情,除了剃着过短的板寸头,衣服灰扑扑的,似乎和在外面没什么两样。
回来的出租车上,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巾,那是临走时姨父偷偷塞到她手里的,嘱咐她务必带给小姨。廖青看到白软的纸巾上,有几行歪歪扭扭的铅笔字,那些字好似踩在云端里随时可能粉身碎骨。她只记得其中四个字:泪如泉涌。眼前浮现出姨父站在高墙内黯然垂泪的模样,那俊俏的脸庞因糊了眼泪水而有了强烈的戏剧意味,让她忍不住想笑。
后来,据母亲说,当她将那张轻飘飘、软绵绵的餐巾纸交到小姨手里,小姨哭得像个泪人。那套七层楼房顶层的房子就是小姨在那时花光所有积蓄买下,只装修了阁楼、卫生间、厨房、餐厅等必要的几处,其它仍保持毛坯本色。作为闯入者,廖青每次路过那些黑黢黢、没被装修的角落,总有种窥见“黑洞”的悚惧感,后来即使整个房子被装修一新,光线均匀洒落各处,也无法消除最初的印象。
小姨搬到七楼那年,廖青在县一中读高二。父母亲开始外出打工,家里只有年迈的祖父母,自顾不暇。她在小姨那间装修了一半的房子里度过了整个高二和高三的所有周末,直到离开县城上了大学。
二十一年后,廖青又走在了这条靠近大坝的路上。远远望去,深绿色草木占据两岸,溪流被推挤到中间位置,某些河段甚至不见流水的影子,褐色飘带再也飘不起来了。听母亲说,蒙城已经三个冬天没有下雪了,她所在的城市也如此,即使偶尔飘来一阵雪花,很快就会消散无踪。
来这里之前,她以为还能找到少年生活的蛛丝马迹——只要用心寻找总能有所发现,但她忽视了时间的力量,它把所有县城都变成同一座,似乎只有溪边吹来的风还留有一丝当年的余味。当然,那幢七层楼房还在,小姨也还住在里面,老小区面临改造可以加装电梯,但一楼的住户说什么也不肯装,其它楼层的诉求也不一,事情就这么拖着。
廖青还记得那锈迹斑斑的扶手,一旦上了四楼,就需要它的辅助才能顺利走完全程。而沾了铁锈味和石灰气息的手无论放在哪个容器里都洗不干净,就像贫穷给小姨带来的耻辱感。小姨不止一次地在母亲面前哭诉,说姨父那边的亲戚嘲笑他们要在那间破房子里待一辈子,别人都换过不止一套房子了,只有他们还在原地打转。
那天,还没走到丁字路口,在大车扬起的尘灰中,廖青忽然掉转头走回了酒店大厅。但第二天吃过晚饭,她又沿着大坝方向慢吞吞走去,走到一处岔路口,桂花的香气飘来,她心神陡然一振,似乎抓住了从前日子的一角。暮色在身边迅速聚拢起来,将她推至那条熟悉的路上。
那几年,每个周日的傍晚,从小姨家出来路过国营酒厂门口,隐隐的酒香在晚风中飘荡,下白班的人陆陆续续从里面出来……可这些身影中再也不会有姨父这个人了。后来,姨夫从里面出来,外婆让他跨了火盆,去了澡堂,在蒙城最好的酒店吃了一顿大餐,亲戚们都包了红包……亲戚们的助力也就到此为止了。
那之后,姨父做过车床工、保健品推销员、仓管员、私营企业会计、民宿合伙人等,赚过一些钱,也被人骗过。姨父与人合伙开民宿那一年,廖青已参加了工作,小姨兴冲冲打来电话问她要不要一起入股,廖青不知道她给别的表姐妹也发了协议书——她们干脆每人给姨父发了一万块钱做启动资金了事,这让小姨觉得自己被羞辱了,逢人便说,“我们又不是乞丐,要这一万块钱做什么”。可谁都知道一万块钱在当时并非小数目。
只有廖青什么也没做,一味躲避着,比表姐妹还不如。此后,小姨不再主动和她联系,她们只在亲人葬礼、过年聚会以及表哥表姐们的婚宴上见过几面,既没有更热情,也没有过分冷淡。母亲总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她早就忘了,哪里会责怪你呢。你应该去看看她的。”廖青也想去看她,但每次事到临头,都退缩了。廖青也有过艰难时刻,也曾把希望寄托在亲人身上,也都一一落空了。
当年,姨父不仅没能在开民宿上“捞一票”,还差点儿亏得倾家荡产,前期投入太大,后面无资金做创意推广,把小姨的工资折进去不说,还不得不向银行贷款,都是小姨用工资卡帮他还清的。那以后荒唐事更多,用炒股软件炒股,跟人学习如何饲养甲鱼,都一一泡了汤——财神爷离他不止十万八千里。
七层楼比想象中更为陡峭,像是爬一段垂直而上、漫无尽头的的天梯,天梯的顶端住着小姨一家。从前是三口之家,现在固定住户只剩两口人,他们的孩子早就搬出去住了。廖青还记得那大得近乎空旷的客厅,除了倚墙而立的电视柜,一排三人座的木头沙发椅和配套的茶几,便没有别的家具。又由于它的装修时间晚于厨房和卫生间好几年,好似一个从天而降的空间——本来是为了招待客人而准备的,却很少有人去那里。
廖青作好在那里枯坐半小时以上的准备,如果有电视机作掩护或许会好一些,她带了一个健身锤——通过敲打身体经络来达到保健目的,或许小姨会喜欢。母亲说小姨自从腿脚不便后便开始自学针灸,也不知弄得对不对。廖青在门外等了足足三分钟,就在她以为房里可能无人时,却有一个声音从里面传来,伴随着椅凳的碰撞声,门从里面打开了。
小姨的脸出现在微暗的灯光下,她穿着碎花、开襟翻领的睡衣,脸部有些浮肿,看不真切。看到廖青的刹那小姨略点了点头,好像事先就知道她会来。她换了拖鞋,跟在小姨身后进了屋内,内心莫名生出几分惶然和怯意。里面陈设几乎没怎么变,还是那几样家具,唯一不同的是它们变得陈旧和妥帖了,与周遭一切完全融为一体。主卧门里透出的灯光几经反射打在过道墙上,且与来自角落里影影绰绰的灯光聚拢叠印在一起,却没有明确而强烈的光源来彻底照亮这一切。廖青环顾四周,客厅角落里似乎堆满了东西,就那样随意放着,也没有隔板和货架,很像直播间仓库。小姨并未将她往客厅里领,好像这屋里还有另一个地方更适合招待她,廖青以为是阁楼,一架竖起的木质楼梯竖琴般通往那里,但小姨领她去了主卧,移门外有个小露台,放着一只圆形藤编茶几和两把椅子。廖青闻到酒味,一只棕色酒瓶竖在几案上,边上还有一只小小的玻璃杯。小姨指了指角落里那把圈椅,轻声说道,“你也坐吧”。
落座后,那酒味似乎更浓了,几乎扑面而来。小姨怎么喝上酒了?廖青皱着眉头,张了张嘴,终究没说出口。从前,小姨可是滴酒不沾的。
“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医生让我睡前喝几口解解湿气,就喝上了。没事的,喝得不多,就一点点。”小姨笑笑说。
——可她这个样子根本不像是只喝了一点点。
这方空间里唯一的光源来自藏在磨砂罩子里的顶灯,微弱、恍惚,好似萤火虫的微光。小姨的脸就隐在这光影里,比平时更显苍白了。小姨诉说着饮酒的好处,声音是轻的,语速缓慢、迟滞,随时预备着被人打断。可廖青没有打断她,只下意识地盯着那张光影下的脸,原本饱满充盈的轮廓似乎在缩小,越来越小,随时可能消失……廖青被自己的发现吓了一跳。
廖青住在这里的那几年,这个房间还是全灰的,没有任何装饰。那时,她和小姨都住在阁楼上,由木板隔出两小间,中间门洞以曲别针和糖纸做成的门帘相隔——是她和小姨花了两个周末的时间串成的,小姨住外间,她住里间,每当身体斜插着穿过门帘,便响起糖纸的窸窣声,好似吹过一阵馨香的、带甜味的风。
周末的夜里,她们早早吃过晚饭爬到阁楼上,她写作业,小姨织毛衣、钩花边,各自忙到深夜。夜宵是芝麻汤团或酒酿圆子,诱人的甜食,多年后她还念念不忘。现在想来,那是一个近乎隔绝的世界,忘了亲戚的白眼和姨父的眼泪,俨然是荒野里的庇护所。第二年夏天,阁楼上的晚风吹来她要离开的消息,小姨一贯平和的表情中分明带着几分惶然,但很快恢复如初。拿到录取通知书不久,小姨不知从哪里搞来一条挂脖式红色连衣裙,是《电影画报》上的女明星在晚宴上穿的裙子。裙子被她带到大学校园,只穿过一次便沉入箱底,多年后混在一批半新不旧的衣物中捐了出去。
廖青摸了摸随身携带的礼物,除了健身锤还有刚从超市货架上取下的保健品,大众货色,不值一提。她心里一阵愧疚,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并没有任何别致的礼物可以拿来馈赠给眼前这个人。大学毕业之初,她无数次地想过如何报答小姨,什么样的礼物才配得上这份情意,她甚至对自己母亲也没动过这种心思。
“前几天,你妈说你要回蒙城,我就想着你应该会来看我的……”小姨将那枚小酒杯紧紧攥在手里,用那种眼神望着她。
廖青没有吭声,她不能说自己并不想来这里,是母亲一定要她来的。
“当年,这么多外甥和外甥女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你。可后来,连你也和我疏远了,我心里真是难受……”廖青想,她到底还是将心里话说出来了,这样也好,她们之间是应该开诚布公地谈一次了。
小姨的眼睛有些发红,好像有更多话要从那里面涌出,果然——“我早就知道的,锦上添花是有的,雪中送炭想也别想。自古以来都如此。没什么好抱怨的。可你今天怎么想到来我这里呢?还买了这么多东西,害你破费了,以后不用那么客气的……”廖青恨不得夺路而逃,却不得不陪着笑脸,说自己以后一定会多来看她,只是这几年家里事情多,顾不上。
“我不怪你,你妈说你也不容易,身边连个搭把手的人都没有。”廖青心头一怔,不晓得小姨对她的情况了解多少,有些事情她连母亲也没告诉。生活在外地有个好处,只要自己不说,别人什么也不会知道。
廖青的担忧是多余的,小姨的心思根本不在她身上,酒杯斟满后,话题又自动漫溢下去。这回落到工作上。小姨的儿子也到了找工作的年纪,却处处碰壁,“好不容易考上事业单位,到政审环节却被刷了下来。你说这公平吗?老子犯的错误还要让儿子埋单!”小姨带着哭腔说道。
她愣怔着,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记忆里不曾存储小姨愤怒和怨恨的脸,全是温婉、克制的形象。什么时候她也变成这样了?廖青想起母亲曾告诉她的,小姨为了给儿子在省城买房向开厂的大舅借钱,几乎是狮子大开口,“她那个不是借,而是想让你大舅白白送钱给她,好像那是她应得的。可大舅也没欠她什么啊,谁也不欠她什么的……”。母亲的话再次飘到耳边。廖青有些后悔来这里了,要是小姨问她借钱怎么办,她会相信自己也没钱吗?
好几次,廖青忍住了查看手机的冲动,不想让小姨误认为她这么快就想离开——尽管,她比任何时候都坐立不安。从前,从这里的窗台望出去还能望见稻田、河流以及那条通往邻县的大路,白天火柴盒式的车辆在上面移来移去,到了夜里便只剩下闪烁的灯光。现在,窗外不远处是另一扇窗,无数扇窗户嵌在高墙之内,散逸出繁星似的寥落的光。小姨的七楼躲在高楼与高楼之间的夹缝里,好似峡谷底部,而露台上的她们宛如坐井观天。
“腿脚不好,被软禁在这七层楼上,哪里也去不了。”小姨叹息道,转而忿忿地诉说如何被庸医误诊,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双腿好似长出根系,一步也挪动不了。
“还好有酒,活血化淤的,真的好多了……”提起酒,小姨又笑了,好像那成了她所有活力的源泉。自她入座后,小姨一直慢慢小口抿着,从未停下过。昏暗灯影下,小姨脸上忽然绽出隐约而闪烁的光亮……这让廖青大感诧异,只不过喝了点酒,竟完全变了个人。但她知道这是暂时的,小姨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人了。
廖青终于想起要问问姨父的下落。自来这里后,她一直等着这一刻的到来。上一次见他还是在外婆葬礼上,披麻戴孝,和一大堆孝子贤孙跪在灵前。还是那样瘦削的体型,只稍稍厚实了些,好像一个失败者连中年发福的机会也被剥夺了。和谁说话都是一副唯唯喏喏搭讪的表情,逢人便递烟,打招呼,让人看着很不是滋味儿。
一旦他现身,她便有理由离开了。她和他向来是没有什么话说的,尤其是那件事情发生后……就是这个人害得她和小姨生了嫌隙。
“他去苏州了,今晚不回来了。”小姨轻声说。
廖青点点头,手脚不由颤抖着,有点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原来这屋里并没有这个人,他今晚不在这里,要是小姨的生活里从来没有这个人就好了……那一刻,她比任何时候都感到放松,腰部肌肉瞬间松弛下来,整个人瘫坐在圈椅上。
后来回想起这个夜晚,廖青依然很难相信它是真的,如果小姨没有喝酒,如果姨父在家,一切都不可能。七楼离地面估计有二十米,秋虫的鸣叫声传不到那里,暝色中的露台却给人一种随时可能脱离尘寰的错觉。这错觉引领着她们进入往事内部,它们原本躺在河床底部,水草丰茂的所在,被生拉硬拽出来时,不免激起水花和波澜。
不知怎地,话题忽然飘到虚无缥缈处,虚到不能再虚了,由一个英俊的男明星作为切口,小姨让回忆的石子落回到无常的一年。那也是廖青住在这屋子里的几年,除了糖纸门帘,甜的夜宵以及天窗,总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从里面渗透出来,时不时让她吃惊一下。
一个年轻男人戏剧般出现在小姨生命的低谷。昏暗的灯光下,小姨带着醉意的讲述开始了。廖青好似回到大学卧谈会现场,眼睛一闭,嘤嘤声顷刻来到耳边,追索着某些激动人心的时刻。但她的心,并没有像当年那样马上被搅荡起来。
姨父进去的第二年,那个男人在电影院门口看见了小姨,俩人连话也没说上半句,那人便展开了行动。被小姨严正拒绝后,男人天天等在大坝那里,上午七点到八点半,下午四点半到六点——那是小姨的上下班的时间,他以端正的站姿迎接她,比时钟还准时。小姨没办法了,不得不答应和那个人一起吃饭。
“可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啊?”无论如何回忆,廖青脑海里就是没有那个人的身影,连一点碎片影儿都找不到。
“他给我写过一封信,投到楼下信箱里,说我的情况他都知道,只要我愿意他可以等。收到信后,我整天提心吊胆,生怕他来家里找我。我让你周末过来陪我,一开始……也是因为这个。”小姨说。
廖青更为愕然了,原来当年在她和小姨的共同生活中,还有一个隐形人的存在,他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
“这几年,我倒是经常想起这个人。刚才你敲门进来时,我忽然想,有一天他会不会回来找我。当年,我如果狠狠心跟他走,不知道日子会不会好过些。”因为姨父的事,小姨不仅晋升无望,还一度被打压和鄙视,比她晚进单位的人都走到前头去了,只有她还在原地踏步。有几年,小姨想辞职不干,连退路都想好了,却到底没能跨出那个门槛。
“……那后来怎样了?”廖青踌躇着问道,既想快速知道内情,又有些抗拒。
黑暗中,小姨顿了顿,没立即往下说。就在廖青以为她不会再说什么时,那个略显激动的声音再度响起,“真没想到他会下那么大的决心……说不想趁人之危,要等你姨父从里面出来当面和他谈。他和我说那些话时,我都不敢相信。”说到这里小姨轻声笑了,好像此事的威力还未释放殆尽,仍在她心头激荡不息。
廖青目瞪口呆,好久才挤出一句话,“那你又是怎么回复他的?”她心里想的是,小姨怎么会碰到这种事,太不可思议了,而她居然一无所知。
恍惚间,一个早被她遗忘的人浮出记忆的水面。大一病休在家那年,廖青收到那人写来的信,边读,边止不住掉眼泪。他们在数学补习班上认识,座位挨得很近,男孩打瞌睡时,她会用圆规上的针头恶作剧般戳他手臂,直到他忽然睁开眼睛,怔怔地望着她。那时候,她根本不知道那个人爱着她,更想不到一个老实木讷之人会有如此排山倒海般的情感,瞬间爆发出的威力几乎将她淹没。格子纸上稚气、歪扭的字体,与课堂上那张恍惚、打盹的脸,成了那段时间里奇妙的安慰剂。半年后她恢复正常生活,男孩却从此杳无音信,好像自身使命已告终结就此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廖青也没想过要去找他,一度空虚的生活很快被别的东西填满。
“我自然不可能答应他……但要说一点心动的感觉都没有,那也不对。他离开后,我才知道自己也很喜欢他,舍不得他走。可一切早已无可挽回了。”小姨说道。
幽暗的顶灯似乎被什么东西层层罩住,此刻更显暗淡了。廖青抬头虚望了一眼被高楼挡住的远方,原本她和小姨绝不可能谈论这些,但此刻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她再次闻到桂花的幽香,在这七层楼上,它们像是某种天赐之物,极不真实。
“后来……后来,你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了吧?”廖青只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结束的,既然那是事物最终的结局,她有必要了解一下。
她和小姨足足相差了十二岁。她们朝夕相处的那段日子,她还未成年,还在某种羽翼的庇护之下。如今,她早过了小姨当初的年纪,好像这么多年她一直在马不停蹄地追赶小姨的人生,终于追上了却怅然若失。
“他说话算话,一直等着我,一等就是三年。可越是如此,我越觉得不该轻易作出决定。再说,那时候的我对爱情,对男人都怀有恐惧——我根本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当年,我对你姨父也是真心喜欢,可自从那件事情发生后,我的心就冷了,再也爱不起来了。我也想患难与共,也想相濡以沫……当然,我做到了,但那不是爱。我心里知道自己早就不爱这个人了。” 小姨喃喃着,好似沉浸在久远的梦境里。
这是廖青来这里后第一次想起家中的男孩。那个孩子长到七岁时忽然问她,“妈妈,我是谁?为什么在这里?”这是男孩第一次开口说话。因为这些话,她和丈夫想了无数办法,见了无数人。出差前,她把男孩交给他的祖父母,叮嘱他们一定要一刻不停地看着他。为了不让男孩接触刀具和火,她在厨房间装了门锁,把所有带利刃、会割伤的东西都藏了起来。
她没有一天不想逃离这种生活,离开丈夫和儿子,去过一个人的生活。可她怎么能丢下那个男孩呢?他那么可怜,在这世上,爱他的人越来越少,以后只会更加少。如果她一个人带着他,工作,赚钱,上课,心理疗愈,解决一切难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下去。她无法再骗自己,对丈夫的爱早已枯竭,就像一条失去水源的溪流,再也没有满盈的可能。
“后来,你姨父出狱了,我却没有勇气去找他,也不让他来找我。他等了我三年,后来走了,从此再无联系。”小姨快速说完这一切,舔了舔嘴唇,笑了。
lq1muOQ/3bATqhskcOWYrw==“你应该离开他的。”廖青忽然说道。
“谁?”小姨如梦初醒,待明白过来,摆了摆手,喃喃说道,“已经来不及了,一切都太晚了。”
“你应该离开他的。”当再次说出这话,廖青自己也愣住了。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说什么,只觉心里一阵揪痛。想起外婆家的玻璃台板下压着的小姨年轻时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她梳着独辫站在一株开花的白树下,眯着眼,神情有些恍惚。当年,青春年少的小姨怎么会想到自己的人生会落入如此境地?
“如果没有那件事,我和你姨父或许早就离婚了。”小姨忽然说道,“我不能落井下石。再说,你外婆也竭力反对,说绝不允许我们家的人做出那种事。”
廖青摇摇头,觉得事情不该如此,每个人都应该有选择的权利。“其实,我很感谢那个男人,一个女人在遭遇那样的噩运时还能被爱。”小姨脸上再次绽放出那种恍惚的、带着醉意的笑容。廖青喉咙一紧,硬是将涌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这一刻,俩人曾有过的隔阂统统消失了。
从七楼回到地面,廖青双腿发软,像是从山顶上下来。黑暗中,她走出小区大门,慢慢走到大坝那里,风从溪的对岸刮来,带来夜晚凉爽的气息。她想回头再望一眼那暝色中的高楼,但心里知道什么也望不到。某一刻,她的思绪回到很多年前,似乎那些日子里的阳光,风,草木,雨水,甚至汽车尾气,还能原封不动地还原出来。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就能走到她读的高中,补习班在学校对面的弄堂里,登上一架木质楼梯,推开靠右第二扇门便是。原本那里是一家印刷厂,院子里种着高大的法桐,上课时偶尔还能闻到空气中残留的油墨味。男孩的脸再次浮现于脑海,总是眯着眼,一副睡眼惺忪的表情。此刻,廖青不知道他在世上的何处,是生是死,经历过怎样的悲欢,但她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人。无论事隔多少年,他都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只要回头就能看见。
想到这些,一种近乎安慰的情感瞬间涌上心头,她莫名地想要跑起来,跑到那些树皮剥落的法桐树下,树底下已开始积累起黄叶,越来越多的树叶将放下戒备,放弃枝上高悬的日子,缓缓落下……等起风时,这个小城的一切才会真正变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