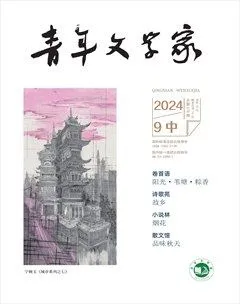《沧浪诗话》艺术赏析
《沧浪诗话》被学界视为宋诗学乃至整个中国诗学的最高成就与最高典范,而严羽则被视为一个沉迷于禅学境界与诗歌艺术本体研究的出类拔萃的诗歌理论家,也是宋代乃至整个中国诗学批评史上的集大成式的人物。现代人尽可以依据“读者反映”理论从理论范畴的视角来阐释《沧浪诗话》,将《沧浪诗话》中所涉及的一系列范畴、命题的发明权统统归属于严羽本人。不过,后人所阐释出来的严羽与历史上真实的严羽毕竟不能算一回事。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方能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过程进行历史的、客观的描述,不至于在对中国诗学精神进行阐述的过程中陷入更深的误区。宋、元两代的诗歌与诗学理论都有极高的价值,必然成为人们的重要研究课题。严羽诗学在宋代以及元代都没有为诗坛所广泛认可和接受,直到明代初年,经过高棅等福建人的大力提倡,严羽诗学才真正成为主宰诗坛的主流诗学话语。
《沧浪诗话》历来被视作评价唐诗的非常好的一部诗话。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提出了“兴趣说”“妙悟说”“诗主盛唐”等著名的评价唐诗的理论,还采用了“以禅喻诗”的方法来评价唐诗,他的这些做法是十分有见解的。
南宋诗人戴复古在《祝二严》一诗中,对严羽的才华与个性进行了高度评价,以“羽也天资高”“长歌激古风”的赞颂肯定了严羽的风范。从戴复古在此处对严羽的评价就可以看出,严羽天资聪颖,志向高远;从严羽“不肯事科举”可以看出,严羽个性独特,不随波逐流;从“持论伤太高,与世或龃龉。长歌激古风,自立一门户”则可以知道,严羽论诗的口吻激烈,不为世俗动摇,坚持执着,坚守信念,追求真正的理想与人生价值,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典型精神风貌。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把唐诗分为五个时期:初唐、盛唐、大历、元和、晚唐。对唐诗的分期我们到现在采用的还是严羽的这一方法。此外,严羽提出的“兴趣”“妙悟”“言有尽而意无穷”等理论体系也是对唐诗的精髓做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把握程度。
严羽是南宋人,由于黄庭坚“江西诗派”的开创和不断发展,南宋时的宋诗弊端日益显现,出现了严羽所说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南宋诗人纷纷想办法解救,其方法是回归唐诗,向唐诗学习,所以就出现了“四灵派”和“江湖诗派”。针对这一现实情况,严羽的《沧浪诗话》便出现了,他提倡兴趣韵味和汉魏晋盛唐诗歌,以及神气情兼备的盛唐诗。在《诗辨》和《诗法》部分中,严羽把唐诗的地位拔得很高,也告诉了南宋时期的人们究竟应该怎样作诗。严羽对汉魏晋盛唐的诗歌有着极度的崇拜,如同狂热的粉丝疯狂地崇拜着自己所喜欢的偶像那样。在《诗体》的第一部分中,严羽提到“风雅颂既亡”,纵观《沧浪诗话》的全篇,严羽对《诗经》的评价也只有这一句而已,而且就连这一句,他也只是一笔带过,他只说“风雅颂既亡”,然后他就再也没有说过任何其他关于《诗经》的评价了。在《诗体》的这一部分中,严羽按照时代、个人、体裁、用韵等方式对唐诗和宋诗作出了一个比较准确的区分。在《诗法》部分中,严羽并没有提到唐诗律诗中的起承转合,也没有提到唐诗中时间和空间的设置问题。总体感觉严羽对唐诗的评价都是到位的,但他太标榜盛唐,以至于忽略了其他唐诗或是宋诗的美。盛唐的诗确实很美,但初唐、大历、元和、晚唐以及宋朝的诗,也有着它们独特的价值,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长廊中,闪烁着属于它们自己的耀眼光芒。
《沧浪诗话》注重理论辨析,倡导妙悟入神,突出审美兴趣,以发展线索轮廓,探讨对诗歌描写艺术考证研究,重视前人力作,推崇诗歌特质流变。由兴趣、入神、妙悟构成美学审美体系。兴趣为特征、入神以思想、妙悟系本体。围绕别材、风雅、气象创作为入笔理论。创作中所构建的美学思想体系,立足于题材,别具一格,新颖含蓄,格调浑厚,风貌雄壮,题材选择的思想倾向力主意境昂扬。严羽抛弃依赖传统、照搬旧习,认为应以美学的理念去创,悟“道”的才气去构,雅致的文笔去作,运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构筑起展现人类命运深邃品味的史诗性篇章。
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兴趣的依赖程度,产生积极的态度,有着推波助澜的本能。《诗辨》所指的“兴”,则意为由感而生、触景生情的状态,“趣”情浓浓、雅韵随趣。其思想本质意义的“兴趣”要义,在美学体系中以含蓄吟咏、浑然天成、无迹可寻的诗学态势得以展现。就是说,严羽的“兴趣”审美内涵,主要体现在抒发情感与营造意境之中,通过含蓄委婉的艺术表现手法,展现了诗歌创编艺术的独特性与无可替代的雅致境界,同时在羚羊挂角的审美理想指导下,突出开化无痕、悟通自圆、浑然天成、水月相融的美学极致,以妙处无穷、悬中之音,给人以无尽的回味、独特的妙思,达到尽兴而归、趣意正浓、迷离醉酣、沁人心脾的诗画境界。
在《沧浪诗话》中,兴趣是灵,入神是魂,妙悟是美学理论中审美主体性的核心基础。绽放自我心灵境界,是严羽美学诗歌理论的重要一环。严羽的诗歌理论突出情感真挚、自然流露,其含蓄多义的表达方式充分展现了禅宗美学在其中的顿悟表现。妙悟学说源于禅宗,其要义是保持自身清净、清澈的精神境界。不仅是思维过程,更为关键的是审美认知中的价值观辨识能力。审美妙悟如同个性化的思维导图模式,各具特色,难以通过简单的口授或文字描绘达到完全一致的理解与传达。这是一种需要心领神会的哲学思想体验,往往在瞬间顿悟之后,方能妙笔生花,展现出非凡的创造力与表现力。禅道唯在妙觉,诗道亦在妙悟,以悟通妙,妙通则魂聚,聚集中的魂则笔下生辉,唯悟独具本色。严羽的独探妙悟理论,精准深刻地揭示了诗外之诗、妙外之悟的诗道审美特征。
诗韵之美,源于意味之浓。严羽的诗歌理论发展变化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他对宋代那些守旧、缺乏创新精神的诗体派别持批评的态度,尤其针对自标晚唐姚贾的“四灵派”。在理论高度上,严羽所秉持的创新思想远非“四灵”所能媲美,其独到之处无可比拟。严羽崇尚盛唐,主张从上做下不可偏废,以全面的眼光审视时代诗词理论的核心价值,他深入剖析妙悟学说,并探索其背后的科学道理,运用完美的逻辑思维揭示出蕴含浓厚哲理与深刻感悟的哲学美学思想。《沧浪诗话》是宋代最重要、最完整的诗歌理论著作,影响着元明清时期的诗歌理论思想。它的体系完整,不仅是中国诗歌文化理论的开源杰作,而且对当今诗歌理论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严羽以玄思开创了以禅喻诗、以悟定魂的诗论路径。他所构建的诗歌文脉,以及追求意雅悟道的理论境界,为中华民族诗歌的发展树立了崭新的里程碑,奠定了全新的根基。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对比了多位唐代诗人,包括李白、李贺、卢仝等。卢仝为人不羁,其好茶成癖,诗风浪漫且奇诡险怪,不为世俗所容。笔者却认为他所作的《萧宅二三子赠答诗二十首》中的《竹请客》《客谢竹》和《石请客》写得很有韵味。而严羽也认为卢仝的诗歌风格自成一体,他将这种风格称之为“卢仝体”,并表达了对这种诗体的赞赏。还有就是李贺,李贺被称为“诗鬼”,因其诗多涉及一些包含衰老、死亡意味的字眼,为人所不敢为,写人所不能写。而严羽对李贺的评价则是非常正面的。他在《沧浪诗话》中提到了“李长吉体”,用来指代李贺诗作独有的意境风格—诡谲新奇、怪诞华美。严羽感慨“玉川之怪,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这表明他对卢仝和李贺诗歌的独特性和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体现了他对诗歌多样性的重视。
在深入剖析《沧浪诗话·诗体》时,笔者注意到严羽依据时代、个人、体裁及用韵等多重维度,对唐诗与宋诗进行了颇为精准的界分。然而,在笔者看来,以“个人”(即诗人身份)作为诗体划分的一项独立标准,其必要性或可商榷。诗歌,作为诗人心灵之镜像,其本质乃是个体情感与创造力的独特表达,正如书法之于书者,一笔一画皆透露出作者独有的风骨与情怀。因此,单纯以诗人身份来界定诗体,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诗歌艺术更为本质的属性—即情感的真实性与独创性。实际上,真正能够触动人心、流传千古的诗篇,无不蕴含着诗人真挚而深刻的情感体验。诗人唯有先被自己笔下的文字所打动,方有可能跨越时空的界限,触动后世读者的心弦。反之,若作品仅停留于表面的堆砌与模仿,缺乏真情实感的支撑,即便是出自名家之手,亦难免显得苍白无力,难以激起共鸣。故而,笔者认为,在赏析《沧浪诗话》所论的诗体之时,我们更应聚焦于诗歌本身的情感深度与艺术魅力,而非过分拘泥于诗人的身份标签,唯有如此,方能更加全面地理解严羽所倡导的诗歌审美理念,以及唐诗与宋诗各自独特的艺术风貌。
修经悟道,方得正果;妙诗启迪,洼地成积。灵感与激情交织,笔下生花,此乃艺术家在创作道路上不懈积学勤勉之追求。《沧浪诗话》所蕴含的言境修悟,是修悟得道、勤学不辍、秉持博大精深之态度以及执着追求所结出的硕果,绝非短暂浅薄之功所能成就。严羽在诗学妙悟方面的成就,不仅仅在于他态度上的勤勉,更在于他多年积累的见解与感悟,他的灵魂浸透着风雅之气,诗赋如同胸中澎湃的情感,在高尚情操的殿堂中时刻回荡,余音绕梁。学者在探求学问的过程中收获的心得和感悟,皆称为“悟”,使人的境界和信念得到升华。然而,诗歌词赋中的艺术顿悟,与实体艺术的形式表现截然不同。心灵中的顿悟,仿佛心灵间的交融,令人豁然开朗,而要达到这种境界,深悟细研、反复锤炼是必不可少的。实体艺术,是可触、可碰、可摸的存在,与心灵中那种需凭悟性方能融会贯通的境界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在绘画等实体艺术领域,艺术家通过技法与材料的运用,展现其内心世界;而在诗歌词赋的海洋中,则是通过文字与意象的交织,让读者在心灵的共鸣中领略艺术的真谛。
《沧浪诗话》是一部重要的诗词基础理论论述作品,以高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概括了诗词理论的核心特征、特性和特点,该书不仅在宋代即已享有盛名,并一直传承至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是中华民族诗歌思想理论领域中具有指导性和示范性的经典著作。它对诗歌的内在艺术形象与诗词鉴赏思维特征的探讨,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严羽之后的诗人、词人,其中有很多就是受到了他的诗歌理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他的理论方法把哲理的思辨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使得诗歌既具有灵性,也具有思辨理性;既有历史的底蕴,又有对现实的戏仿。人生长河,爱恨别离,诗歌写尽了有关万物的灵感,延伸出人们的价值取向、奋斗目标。当一切终将消失,唯有诗歌永存。人生的意义也将永远封存在其中。诗正是体现着真善美,就像英国诗人济慈所说的“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希腊古瓮颂》)。
严羽诗学理论产生之后,诸多文人墨客在创作时引用其经典论断,融入笔端,尽管这些诗人在诗学理论的基本框架上有所遵循,但总体上与严羽的诗学观点存在区别。即便那些与严羽有交往的诗友,以及在作品中提及或引用过他诗论的宋元人士,他们的诗学观念也并未完全被严羽所左右。很难在这些人中找到像严羽那样专一宗法盛唐李白、杜甫格调的例子。由此可以推断,严羽的诗学理论观点,虽受时代背景影响,但由于过度追求某种风格而未能广泛引起诗坛的轰动效应,即使是在他的交游圈内也未形成一边倒的追随态势,使得他的诗学处境显得颇为寂寥,未能掀起太大的波澜。
在宋代端平更化的大背景下,严羽的诗学最终突破了纯然的艺术批评而进入“文化批评”,抑制了诗学的个人化与生态多样性,打上了鲜明的功利主义的色彩。
严羽“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论,乃是理解严羽诗学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他的“直接根源”说,实际上关系到诗人的政治理想,其诗学理想乃是其政治理想的反映。严羽虽然“没功名,没官籍”,不愿意从事科举,不愿意直接介入现实政治,却心存极为高远的政治理想。在严羽看来,从开元、天宝到庆历,再到天祐、乾淳,其政治环境连同诗学环境是每况愈下的。因此,他主张越过宋代的前三个时期,直接追溯到盛唐,这一主张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宋型文化的一种间接否定。
严羽及其诗学不为时人所重,必有其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其傲慢的个人性格因素以及偏激的批评话语之外,还与其政治理想或者对于当代政治的基本姿态有关。在特定的时代形势之下,严羽毅然决然要颠覆诗学理论的同时,进行政治范式的反叛,也是江湖诗人议论朝政、士大夫风气的一种表现,他的诗学实际上是带有“政治文化评论”的性质,而不是纯然自足的诗学批评,这是严羽作为朱陆传人的儒学身份所决定的。
所以,从严羽的《沧浪诗话》中,我们领略到了盛唐时期诗歌所展现的悲壮、凄婉、感慨的风范,以及深邃的屈骚悲情。中国诗歌范式从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铺张扬厉、豪放雄浑的壮美,转向韦应物、柳宗元等人的平静内敛、淡泊清新的柔美。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严羽的学说体系,加强诗词的鉴别与赏析能力,让这些诗歌作品绽放出璀璨的光芒,彰显出它们独特的价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