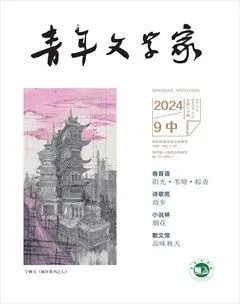郑珍诗歌中所见的“礼”
郑珍被称为“西南巨儒”,为学深厚,尤精三礼,而以诗名显。作为有清一代宋学派诗人的中流砥柱,他提倡以学为诗,将学问融入诗中,以追求质朴、厚重、缜密、现实的诗学境界。郑珍尤喜以“礼”入诗,或为典故,或为引申,使诗厚重且余味十足。
清代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一直不被学者所重视,一是诗歌发展到清代,其体例、理论已经较为成熟,达到的艺术水平有限;二是清中后期西学的传入,对传统文学产生了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有清一代无杰出的诗人,位于西南一隅的郑珍可摘清诗桂冠。郑珍(1806—1864),字子尹,号柴翁,别号子午山孩、五尺道人,著有诗集《巢经巢诗钞》。郑珍其人从不以诗人自居,而是以学人自居,其诗学多受程恩泽的影响,而展现出了尚学宗宋的特点。道咸以来,诗风为之一变,或是对“诗必盛唐”的审美厌倦,或是受到了乾嘉考据学派征信求实学风的影响,以学入诗的宋诗运动兴起。程恩泽首开风气,标举宋诗,推崇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等,以追求质朴、厚重、缜密、现实的诗学境界。而出自程恩泽门下的郑珍,虽处西南一角,不通外域,但其诗学却为主流,宗宋成为诗坛风尚,而郑珍也为宋学诗派的中流砥柱,可谓“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
郑珍的学术成就斐然,其在经学、史学、小学等领域有着巨大的学术贡献。正如莫友芝而言:“吾友郑君子尹,自弱冠后即一意文字声诂,守本朝大师家法以治经。”(《巢经巢诗钞·莫友芝序》)可见郑珍自幼是以治经为本,而诗作不过是“才力赡裕,溢而为诗”(《巢经巢诗钞·莫友芝序》)。不承想诗学是郑珍生平用力最少的领域,但在后世郑珍却以诗而显名。“论吾子平生著述,经训第一,文笔第二,歌诗第三,而惟诗为易见才,将恐他日流转,转压两端耳。”(《巢经巢诗钞·莫友芝序》)莫友芝预言不可谓不准。郑珍诗歌自清末就为学者所重,莫友芝赞其诗为“隽伟宏肆”(《巢经巢诗钞·莫友芝序》);翁同书称其诗“简穆深淳”(《巢经巢诗钞·翁同书序》);陈夔龙评其诗为“枕中鸿宝”“奥衍渊懿”(《遵义郑珍君遗书序》)。此三者虽从不同角度称赞郑珍诗作的风格,但都表现了同一点,那就是郑珍的诗作深奥难懂,善于用典。郑珍为学人诗派的代表,作诗讲究由读书、养气、学问、性情依次而发,最后合而为诗。正所谓“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赡乃相济”(《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根袛学问”是郑珍诗作的一大特点,其一表现在郑珍诗作中有许多的考据诗,充分展现了郑珍的考据功力,如《玉蜀黍歌》《腊月廿二日遣子俞季弟之綦江吹角坝取汉卢丰碑石歌以送之》《玉孙种痘作二首》《竹王墓》《题〈北海亭图〉并序》《题唐鄂生藏〈东坡书马券〉真迹并序》《黄爱庐(乐之)郡守出所藏方正学文衡山董思白黄石斋手书诸卷鉴别皆真迹也》《安贵荣铁钟行(庚戌)》《文待诏凤兮砚歌并序》《五盖山砚石歌赠曾石友钰刺史并序》《己丑正月陪黎雪楼恂舅游碧霄洞》《癭木诗》《浯溪游》《游石鼓书院次昌黎〈合江亭〉元韵》等。其二表现在郑珍诗作喜引经据典,其诗作几乎无一诗不用典。《巢经巢诗钞》引用的典籍有《山海经》《老子》《庄子》《孟子》《淮南子》《史记》《左传》《诗经》《尔雅》《论语》《孔子家语》《周礼》《礼记》《仪礼》,以及提及孔子的地方就有12处,引杜甫诗作78处、韩愈诗作55处,至于其他间接体现儒家思想的诗文更是数不胜数。此外,郑珍所引用各类方志图舆、神仙秘籍、释道经文,林林总总加起来不下150处,展现了其学识的广博精深、其诗作的奇奥渊懿。
郑珍生平经学著述丰富,而尤精“三礼”,其经学著作有《巢经巢经说》《仪礼私笺》《轮舆私笺》《凫氏为钟图说》,无一不与“三礼”相关。其诗作《巢经巢诗钞》共辑908首,其中引用涉及“三礼”的就有79首,比例不可谓不大,甚有诗作一篇即引遍“三礼”典故,令人赞叹!现将郑珍诗作中有关征引“三礼”的篇目摘出,希望从郑珍诗作中所见的“礼”来窥探其礼学思想。
一、诗作中所见的《周礼》
《周礼》,又称《周官》《周官经》《周官礼》,是第一部系统记载我国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分工的典籍。由于清代考据学的兴盛,清代学者对于《周礼》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中有惠士奇的《礼说》辨条析理,引有本源;有江永的《周礼疑义举要》,对于《考工记》的阐发尤为精核;有沈彤的《周官禄田考》、鄂尔泰等人的《钦定周官义疏》、段玉裁的《周礼汉读考》、阮元的《附释音周礼注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清代研究《周礼》的集大成之作,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极为称赞此书言:“这部书可算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此外对《周礼》中《考工记》一章做具体研究的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有戴震的《考工记图》、程瑶田的《考工创物小记》、阮元的《考工记车制图解》,以及郑珍的《轮舆私笺》。可见,郑珍对于《周礼》的研究是极为深刻的,以至于在作诗时可以随手引用。《巢经巢诗钞》中引用或化用《周礼》的诗作共27首,39处,其中较多的是引用《周礼》中对于农业的专有名词。郑珍虽为文人但关心农事,其农业活动,农民占据了诗歌绝大多数的题材。例如,《玉蜀黍歌》中写道:“职方五种载周官,较之尧称百谷已无多。”“职方”指古时管理农业的官职,见《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畜宜六扰,其谷宜五种。”对于“五种”,郑注曰:“黍、稷、菽、麦、稻。”《玉蜀黍歌》中还写道:“亦如九谷中有粱菰,南人未闻名者徒摩挲。”句中“九谷”见《周礼·天官·大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又如郑珍在《于堰南获早稻》一诗中写道:“入秋喜先熟,似得田公怜。”“田公”指的是保佑田地收成的神,见《周礼·地官·大司徒》:“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田主”,即社稷之主。郑注曰:“社神名后土,稷神名田正。”
此外,郑珍有专著《轮舆私笺》与《凫氏为钟图说》,是专门研究《周礼·考工记》中关于车制与钟制的。这两本专著,参考诸家、往复寻绎,在厘清前辈成就之时,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对于《考工记》的深研自然而然地就浸透在诗歌的创作中。例如,他在《安贵荣铁钟行并序》中写道:“旋虫啮朽篆带缺,空腹黯黪巢蜘蛛。”“舞修、鼓广各意创,尺度不中冬官凫。”“遗迹扫尽此钟在,鼎之崇贯鼓密须。”“篆带”,即钟腰之饰,见《周礼·冬官考工记·凫氏》:“钟县谓之旋,旋虫谓之干。钟带谓之篆,篆间谓之枚,枚谓之景。”郑玄注:“旋属钟柄,所以悬之也。”郑司农云:“旋虫者,旋以虫为饰也。”又云:“钟带谓之篆。”“舞”“鼓”,均钟体名;“修”“广”,即长、宽。见《周礼·考工记·凫氏》:“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钲上谓之舞。”注:“此四名者,钟体也。”“尺度”指舞、鼓的尺寸,记载于《周礼·考工记·凫氏》:“十分其铣去二以为钲,以其钲为铣间,去二分以为之鼓间,以其鼓间为舞修,去二分以为舞广。”“栾于”,钟之代称。《周礼·考工记·凫氏》云:“两栾谓之铣,铣间谓之于。”疏:“栾铣一物,俱谓钟两角。”郑珍在诗中通过引用《周礼·考工记》4处典故,基本上介绍清楚了古制钟体的各个部分,可谓以学为诗,将学问融入诗中。
二、诗作中所见的《礼记》
《礼记》,就是关于“礼经”的“记”,即对于具体“礼”内容的诠释和讲解,是礼学家对于“礼”的解读和所认可的各种意见的一种搜录。郑珍对于《礼记》并没有具体专门的著作,其研究的主要成果记载在《巢经巢经说》一书中。《巢经巢经说》收录了郑珍的读经笔记以及论文19篇,其中涉及《礼记》的有:《〈礼记正义〉》驳文、《〈曾子问〉“昏礼既纳币有吉日女之父母死”节》、《〈礼记注〉脱窜》3篇。篇章虽不多,但对于《礼记》既有整体的分析,也有对于其中一节的具体研究。在郑珍生平关于“三礼”著作中,关于《礼记》的尤其少,但在诗作中引用和化用《礼记》的地方确实最多的,共涉及56首,90处。《礼记》的大量引用,含蓄地表达了郑珍人生的诸多情感,如子孙早逝的悲痛,师长去世的哀痛,以及父母的安宁之乐和学生的归乡之喜。
郑珍在《才儿生去年四月十六,少四十日一岁而殇,埋之栀冈麓》中写道:“木皮五片付山根,左袒三号怆暮云。”“左袒”指袒露左臂,引申对子孙去世的极度悲伤。《礼记·檀弓下》记载:“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
对于师长去世的哀痛,郑珍在《题新昌俞秋农汝本先生〈书声刀尺图〉》中写到“请为皋鱼歌,和以子夏琴”两句,“子夏琴”指丧亲之后弹琴不成音调。《礼记·檀弓》记载:“子夏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弹之而不成声,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礼而弗敢过也。’”
郑珍的《胡子何来山中喜书此》中有“父母近在堂,定省犹难之”和“大鸟有回翔,稽留固其宜”四句,是借《礼记》的典故表达了父母安宁之乐和学生归乡之喜。“定省”,即按时看望。《礼记·曲礼上》记载:“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丑夷不争。”“定”,郑注曰“安定其床衽也”,指铺设安放床褥、被枕等。“省”,即向父母问候请安。此处统指对于父母恭敬照顾之意。“大鸟”,《礼记·三年问》记载:“今是大鸟兽,则失丧其群匹,越月逾时焉,则必反巡过其故乡,翔回焉,鸣号焉,蹢躅焉,踯蹰焉,然后乃能去之。”胡长新曾随父,学于莫郑,今以大鸟返回,以表欣喜。郑珍诗歌含蓄情感,但典故众多,以追求质朴、厚重、缜密、现实的诗学境界。
三、诗作中所见的《仪礼》
《仪礼》是中国最早关于“礼”的文献,在“三礼”中成书年代最早,且篇幅也最少。在考据盛行的清代,学者对于《仪礼》的研究尤为重视,且著作充盈。一是《仪礼》成书最早,年代久远,这对“凡古皆好”“凡古皆信”的朴学家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二是《仪礼》可谓“三礼”中最为艰深者,其辞简旨奥,脱伪刊漏较多,为诸经中最难治者。“《仪礼》出残阙之余,篇次各有不同,古文经久亡。”“其书自汉以后,传习者鲜。脱落谬误滋多。明代以来尤甚。”(唐文治《十三经提纲》卷五《仪礼》)郑珍关于《仪礼》有专著《仪礼私笺》,对于《仪礼》多有自得之处,博综众家,融通为一,至为精密。其诗作中对于《仪礼》也有引用,但较《周礼》《礼记》所引甚少,只有4处。
第一处,郑珍在《乡举与燕上中丞贺耦庚先生》中写道:“钩楹预礼礼,清簧间朱弦。”“钩楹”,即绕楹柱而向东,见《仪礼·乡射礼》记载:“司射东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挟一个,揖进;当阶,北面揖;及阶,揖。升堂,揖;豫则钩楹内,堂则由楹外。”又见《仪礼·聘礼》记载:“大夫升自西阶,钩楹。”
第二处,郑珍在《系哀四首并序》中写道:“禫祭逾月,欲歌先哽,痛念慈踪,触事如昨,我今不述,谁复知之?”“禫祭”,即除丧服之祭,见《仪礼·士虞礼》记载:“期而小祥,曰:‘荐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荐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犹未配。”郑玄注:“中,犹间也。禫,祭名也,与大祥间一月。自丧至此,凡二十七月。”
第三处,郑珍在《寄山中兄弟五首》其五中写道:“已脱三升服,堪愁六尺孤。”“三升服”,斩衰三年之服,见《仪礼·丧服》记载:“丧服。斩衰裳……衰三升。”
第四处,郑珍在《秋雨叹》中写道:“获者秉烂纷纵横,未获者倒如席平。”
“秉”,即稻把,见《仪礼·聘礼》记载:“四秉曰筥。”郑玄注:“此秉谓刈禾盈手之秉也。”
郑珍诗作中对于“礼”或为典故,或为引申,遍布《周礼》《礼记》《仪礼》,涉及诗作共79首,133处。其中所引“礼”的典故,随手而来,又切合诗作内容,升华了诗作的思想,使人读后韵味悠远。纵观郑珍生平的经学著作,无一不与“三礼”有关,其著作与诗作中所引的“礼”也形成了强烈的互补关系。其诗作中涉及“礼”引用最多的为《礼记》,共引用了90处,但与之相对的,郑珍关于《礼记》研究而留存的笔墨最少,仅《巢经巢经说》中的3篇。其诗作中引用“礼”最少的为《仪礼》,仅有4处,但是郑珍却留下了《仪礼私笺》8卷,对于《仪礼》的研究深入而有自得之处。郑珍作为宋学诗派的中流砥柱,引“礼”入诗使得诗厚重且余味十足,将宗宋尚学的学人诗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清朝诗坛的一座高峰。
本文系2024年安徽三联学院“思想政治能力提升”项目“全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对大学生就业焦虑的影响与应对研究”(项目编号:SZYB2024002)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