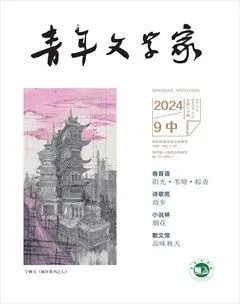南宋爱国词中的家国情怀

宋词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篇章。晚唐五代以来,“词”一般用于描写个人生活,抒发个体情感,词风相对婉约细腻。南宋以后,词坛风格发生巨大变化,明快豪放的词风逐渐取代婉约小曲,从“激昂欢快隐忧伤”逐渐转变为“战乱蜂起思报国”。这种艺术上的转变,主要在于词作内容上的巨大变化。南宋的社会环境激发了士子们的拳拳爱国心、殷殷报国志,他们开始描写社会生活以及国家大事,因此“爱国”成为南宋词的时代主题。在作品中,词人们抒发爱国情感,表达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坚守,形成了南宋爱国词中的家国情怀。
一、慷慨豪壮之语诉报国之志
南宋词人经历了社会巨变,他们将满腔报国热情书写于词作之中。他们写下对江山沦陷的苦痛,写下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写下对入侵敌人的仇恨,同时也写下报仇雪耻的壮志决心。
(一)生而为国,胸怀天下
辛弃疾是南宋爱国词人中以慷慨之语书写报国之情的词人代表之一,他是一位被称作“用生命写词,用生活实践词”的文学家,不仅在作品中表现了忠心报国的英雄气概,还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和大多数南宋词人一样,辛弃疾的一生都以报效国家、实现统一为理想。他一生经历坎坷,出生在金国统治下的山东,由祖父辛赞抚养长大。在敌人占领中原的时候,辛赞因顾及一家老小的安危,不得已在金朝为官。但是祖父辛赞“身在曹营心在汉”,时刻没有忘记沦陷的国土。辛赞经常带着年幼的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正是由于辛弃疾从小接受着祖父的爱国主义教育,抗金复国的人生理想,在他少年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并且贯穿于他的整个创作历程之中。辛弃疾留下了多首脍炙人口的词作,像“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都是辛弃疾忠心为国的体现,字字句句都在诉说着他的报国理想。
辛弃疾一生都有着明确的志向,只要自己得到任用,就一定要抗敌救国,收复失地。可他这样的主张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得到认同,因此他仕途曲折,一直处于“被贬官—被起用—被贬官”这样的坎坷之中。这样的经历非但没有令他消沉,反而激发了他的报国热情。辛弃疾在《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这首词的开篇写道:“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从字面上理解,词人抬头看见了西北方向有一片浮云,而这不仅仅是天空中看得见的乌云,也在用“乌云”暗指敌人正在侵略西北方向的大宋江山。辛弃疾在“潭空水冷,月明星淡”的艰难环境中寻找可以驱除浮云的“长剑”,以寻找“长剑”的行动来代指自己寻找消灭敌人的策略。以长剑驱散浮云,也是辛弃疾希望收复沦陷国土的理想写照。寻找长剑的过程势必十分曲折,寻找抗敌救国的道路势必充满艰难险阻。下阕中,辛弃疾写到“峡束苍江对起”,正体现了他的处境。双溪楼是两条水的交汇的地方,四面都是高山,在高山的夹持和约束下,两条水只能在山峡之中翻腾而无法跨越。辛弃疾在这里用溪水受高山的限制,比喻自己受统治者的限制。辛弃疾虽然早已预料会受到重重限制,还是要努力腾空飞翔,跨越高山。辛弃疾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民族的苦难,也能够理性地反思民族悲剧的根源,寻求走出困境的办法,在作品中以慷慨豪壮的语言抒发满腔的报国之志。
(二)誓死报国,甘于奉献
文天祥作为南宋丞相和杰出的抗战领袖,给我们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的爱国名句。他的爱国思想不仅仅体现在诗歌当中,《沁园春·题潮阳张许二公庙》这首词也是充满了爱国之情。“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开篇文天祥用三个“死”字,确立了他心中的生死标准:一个人作为父母的孩子,作为君王的臣子,如果能因为尽忠君王、尽孝父母而死,一定是死而无憾的。文天祥以从容的心态谈论生死,显示出了一种达观凛然,让我们感觉到有一股浩然正气扑面而来,这更是文天祥誓死报国、不畏牺牲的英勇精神。
文天祥在这首词中借历史典故进一步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骂贼张巡,爱君许远,留取声名万古香。”张巡、许远二人拥有崇高的气节,面对敌人威武不屈,誓死坚守城池,因此能够流芳千古。这里赞美忠君报国的张巡和许远,为后世树立了优秀的榜样。紧接着,文天祥用假设作对比,“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如果张许二公卖国求荣,甘心投降安史叛军的话,那他们一定会遭到人们的唾骂,怎么能够流芳百世?文天祥言在此,意在彼,看上去是在说张许二公,实际上想告诫那些卖国求荣之辈,他们卑躬屈膝的行为一定会遭到后世唾弃的。文天祥也是在委婉地劝谏,不同的人生选择,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国难当头,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人生翕歘云亡”都应该“烈烈轰轰做一场”。这是文天祥的一种人生大义,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最要紧的是抓住有限的时间,承担起戍守家国的责任,轰轰烈烈地为国家、为民族谋划一番事业,这也正符合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生信念。
文天祥借赞颂张许二公的品格来表达自己的生死观。词中凝聚着我国的文化精髓,为父母尽孝,为国为君尽忠,同文天祥的坚贞不屈一样,为后人立下了一面人生的“镜子”。这面“镜子”也以张许二公为楷模,劝谏人们应该誓死报效国家,尽自己的职责去做保家卫国的大事。
二、愤懑悲痛之音话忧国之情
南宋爱国词人满怀报国志向却难以实现,对家国无限的担忧之情涌上心头,挥笔作词抒发对于家国的忧虑之情。
(一)回顾往昔,金戈铁马
陆游作为主战派一员,主张未被采纳且被罢官回到家乡山阴,闲居时写下了他的忧国之作—《诉衷情》。词中回顾了陆游四十多岁时到梁州从军的一段经历,这也是陆游人生中仅有的一次前线生活,可想而知,对陆游这样一个渴望收复失地、渴望立功封侯的人来说,这段经历是令他永生难忘的。
“当年万里觅封侯”中一个“觅”字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陆游为了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单枪匹马奔赴战场的场面。从作品中我们可以切实感受到陆游希望走上战场杀敌卫国的心情,这段经历如今只能在梦中出现,“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正是因为怀念曾经的军旅生活,所以才会梦到。而陆游怀念的也不仅仅是一段军旅生活,同时怀念那个在战场英勇杀敌的自己,怀念曾经那个能够驰骋疆场实现报国志向的自己。然而在梦醒之后一切都不复存在,陆游看到的只有从军时穿过的“旧貂裘”,这件旧貂裘摆放在陆游触手可及之处。一个“旧”字承载了无限的回忆,一心想战场杀敌的陆游,如今只能带着遗憾回乡,这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愤心境。“鬓先秋”的一个“秋”字写得含蓄又引人深思,“秋”是季节的更迭转换,也是人的衰老迟暮。沦陷的土地还没有被收复,百姓还处在敌人的压迫之下,可陆游以及像陆游一样遭遇的爱国人士,却是从壮士变成了鬓发如秋霜一样斑白的老人,正呼应了陆游在作品中写过的“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感愤》)。“鬓先秋”三个字不仅仅是对年华逝去的悲哀,也是陆游对主和派的谴责,因为他们一味求和,使得一大批爱国志士从青年变成了苍颜白发的老人。最后,陆游只能发出“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无奈感慨,此处“身”和“心”的对比,正是救国理想与悲惨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陆游只能看着山河沦陷,面对“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现实,回忆金戈铁马的生涯。
(二)直面现实,忧愤难抑
南宋的文人志士们或是吟诗作词抒发个人情绪,或是隐居闲处远离世事。他们只能面对现实,在文学作品中抒发心忧家国之感。
南渡文人邓肃伤时忧国,写下“北书一纸惨天容”(《瑞鹧鸪》);朱敦儒满怀“胡尘卷地,南走炎荒”(《雨中花·岭南作》)的忧时愤慨;吴潜发出“望中原何处,虎狼犹梗”(《满江红·齐山绣春台》)的悲痛豪壮。张元幹满怀愁情写下《水调歌头·追和》,以一位报国无门被迫隐逸的老者口吻表达着忧愤之情。这位愁容满面的老者面对湖光山色,难以静心游玩观赏,既是因自己没有实现报国理想身无功名,也是心怀国土未复“梦中原”的悲痛。“元龙湖海豪气,百尺卧高楼。”词人希望自己可以和历史上的陈登一样,有着忧国忧民的责任,有着文武兼备的本领,获得机遇施展才能。然而倾盆大雨使得词人从理想回到现实,自己年事已高、鬓发稀疏斑白,“犹有壮心在,付与百川流。”即使自己满怀雄心壮志,但在时间的流逝中,也逐渐磨灭了理想。在这首词中,张元幹以夸张的手法抒发自己对故土的热爱与怀恋,以史抒怀,借用三国陈登斥许汜的历史典故表达自己收复国土的雄心壮志。从现实到梦境,又从梦境到现实,词人感叹时光流逝,痛惜国家破败,愤懑于自己胸怀报国之志却最终报国无门。报国理想与苦闷现实交织,忧愤之情尽情抒发于笔端。
三、沉着雄浑之言抒亡国之痛
在南宋爱国词中,有一些词人他们不仅仅是爱国文人,也是带兵杀敌的爱国将领。他们在战场杀敌卫国,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因此他们亲眼见到了战争的残酷,也切身地体会到家国破败的悲哀,在作品中书写国家灭亡的悲愤之音。
南宋抗战将领岳飞,多年来南征北战,建立了很多战功,但他没有居功自傲,而是在《满江红·写怀》中写道:“三十功名尘与土。”立下赫赫战功的岳飞竟说自己的功名像尘土一样小,这必然是他的自谦之辞。岳飞在二十岁时就走上了保家卫国的道路,十几年间,可以说是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统率岳家军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当时流传说,如果遇到了强兵,把岳家军的军旗竖起来,敌人看到后就会望风而逃。因此,当时金人与岳家军交战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的作战能力,我们可想而知。
在岳飞短暂的一生中,他辗转征战了几十个地方,在《满江红·写怀》中写道:“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当然,这是岳飞志在打击侵略的急切心情。他想把生命中的每分每秒都奉献给抗金复国的大业中,想要尽自己的职责,抓紧时间完成收复大业。他之所以如此急切,是因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从这句词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岳飞的家国仇恨,他通过这句词把心中的怒火彻底释放出来。靖康之耻让北宋遭受灭国的耻辱,当时金兵能够到达的地方,用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来描述毫不夸张。宋朝的臣子成长于封建礼教思想制度之下,面对这样的灭国耻辱,爱国人士势必想要报仇复国。此仇一日不报,心中的怒火就不会熄灭。岳飞此时有满腔的愤恨和悲痛。在词中,岳飞的愤恨达到了“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程度,虽然读起来有些夸张,但实际上这都难以消解岳飞内心的仇恨。他恨到要驾战车去踏平贺兰山,恨到吃胡虏肉、喝匈奴血。这是岳飞报仇雪耻的决心,也是他郁结于胸的亡国之恨。
岳飞的人生理想是率领岳家军直击敌寇,重整大宋江山,而他面临的现实却与之相反,当时“议和”之风几乎吹遍了整个临安。久经沙场的岳飞看到了统治者未曾见过的百姓疾苦,正如他作品中写过的“民安在,填沟壑”(《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百姓饥寒交迫,被敌人无辜残害,填满了一个又一个的沟壑,他希望立即统兵去解救百姓。岳飞多次主动请缨出战,但是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只能无奈地写道:“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挥鞭北上,驱除敌人,恢复华夏和平盛世。直到那一年,岳飞终于能够参与北伐战争,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即将胜利的时候,岳飞迎来的不是支援,而是“十二道金牌”勒令退兵,此时岳飞的心中不仅仅是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更是目睹家国破灭的亡国之痛。虽然岳飞经历了种种不幸,面对重重困难和阻挠,但是他在作品中依旧传达着以复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南宋词人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不顾个人的安危与得失,或奋力抗敌,或奔走呼号,留下了一首首爱国词作。叶梦得以“叠鼓闹清晓,飞骑引雕弓”(《水调歌头·九月望日与客习射西园余偶病不能射》)来抒发豪情壮志,李纲秉承“纵使岁寒途远,此志应难夺”(《六么令·次韵和贺方回金陵怀古鄱阳席上作》)的抗敌态度,韩世忠饱含着“对山河耿耿,泪沾襟血”(《满江红》)的悲痛豪壮,他们自觉地承担起复国、救国的重任,堪称民族的“脊梁”。南宋爱国词人的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是执着追求理想信念的精神;他们的情怀,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南宋爱国词人在作品中呈现着抗敌救国的人生追求、心念百姓的忧国之情、故土沦陷的亡国之痛以及戍守家国的使命责任等,正体现出爱国文学家们的民族气节和家国情怀,同时也展现了南宋爱国词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