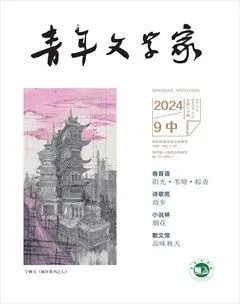从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角度分析《上层林冠》中树的能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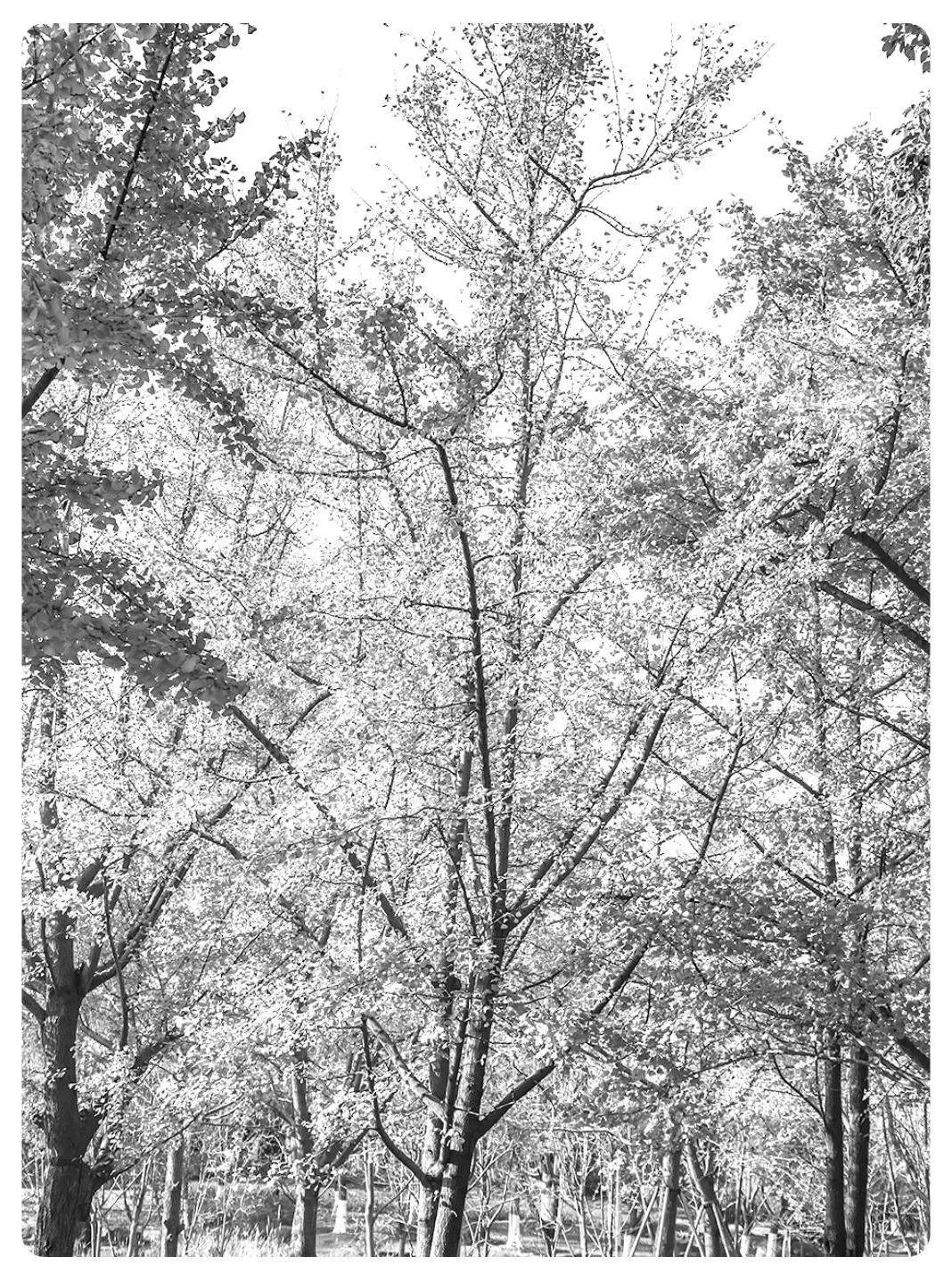
生态批评的第四次浪潮重点是探讨文学作品中的“物质转向”,以及其对于我们理解物质世界的影响。理查德·鲍尔斯的《上层林冠》通过几位主要人物各自与树之间发生的故事,呈现了非人类的植物的生命能动性。本文以生态批评及其物质转向为理论依据,对小说中涉及的物质与意义、树的叙事能力、实施能力三方面进行解读。同时,本文对理查德·鲍尔斯所传达的生态思想进行分析,探索其中蕴含的生态主题,进而促进人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思考,并从中获益。
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理查德·鲍尔斯于2018年出版的生态类小说《上层林冠》获得2018年曼布克奖提名,并一举斩获2019年度第103届普利策文学奖。理查德·鲍尔斯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西海岸木材战争为故事背景,用八位不同背景的主人公作为主角,通过树木来讲述故事。八位主人公被树的召唤所吸引,并从各个角度聆听树的声音。理查德·鲍尔斯将这部小说的焦点投到非人类的树上,表现其强烈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同时,理查德·鲍尔斯通过文中作为树的捍卫者的主人公们的言行来为树发声,体现出作为非人类的树木所具有的能动性。
理查德·鲍尔斯将树的身体部位比作一个完整的故事,从树根开始,他描绘出八位背景不同的陌生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与树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联系。并且,理查德·鲍尔斯通过这种方式,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人类应当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理查德·鲍尔斯在书中巧妙地描绘了几位主人公与树的关系,这些人的命运也随着他们与树的联系的加深而改变。在书的末尾,主人公们被树木召唤,以各种方式协助拯救濒危的森林。他们在抗议活动中遭遇了许多挫折,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小说中的最后一章,随着种子部分的圆满收尾,不仅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终结,更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开始,它深刻揭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人类与自然在历史长河中共同书写的一章,充满了深远的意义。此外,理查德·鲍尔斯也留下了人与自然成为共同体的希望。
《上层林冠》中涉及了各种各样的树与不同的人之间发生的故事,但相同的是,小说中作为非人类的树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能动性。不难发现在小说中,树木作为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自然物质,与人类共同居住在地球上,并且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首先,树木具有一定的“施事能力”,也就是具有发出某种动作或做出某种行为的能力,这也被认为是树生成意义的过程。同时,树木也具有“叙事能力”,即树能通过某种媒介讲述或描绘故事,这也是树木传达意义的过程。因此,作为物质的树与意义之间有紧密的联系,树可以生成意义也可以传达意义。
一、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
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在《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一文中主张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是类似于“羊皮纸的重写本”或是“波”的形状,即生态批评的每一次浪潮都有其新的关注点,但新的关注点一定是基于上次浪潮而形成的,相当于对前次浪潮的延续、补充与发展,并不会与上一次浪潮相分离。目前,生态批评被公认经历了四次浪潮。
生态批评的前三次浪潮均是在前有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拓展而来的,逐渐打破了种族、地域、学科间的限制。2012年,赛仁娜拉·伊奥凡诺(Serenella Iovino)和瑟普尔·奥伯曼(Serpil Oppermann)在《物质生态批评:物质性、动能性和叙事模式》中提出“物质转向”,标志着第四次全球性的环境批判运动的开始。“物质转向”是具有深远影响的物质生态批判,它借鉴了后现代主义理论,挑战传统的物质主义,强调事物本身具有自主发挥功能、创造性思维,超越事物本身,把人们置于物质世界之外。同时,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从微观层面入手,反对物质与意义的二元对立观点。因此,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研究重点在于物质与意义、物质的叙事能力、物质的施事能力。
作为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主要倡议者之一的简·班纳特(Jane Bennett)在《活性物质》中主张,物质是具有能动性的“生成过程”,反对将物质的能动性束缚于人类的意志。提莫西·克拉克(Timothy Clark)在《生态批评的价值》中指出,物质不是毫无变化的被动存在体,而是不断变化的。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在《新物质主义》一文中强调,“物质转向”使多种不同的观点有机融合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非人类物质有着不可估量的能动性”,也就是物质的施事能力。
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关于物质的观念,指出它可以把概念、特征以及运作机制组织起来,并且拥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及可行性。“物质转向”指出物质的活力使其处于话语建构的核心,而它与其他元素之间的关系也正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物质与其他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物质叙述。
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认为文本中属于非人类的大自然不仅是作家笔下的描述对象,更是能生成故事的物质,因此物质本身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叙事。黛安娜·科奥尔(Diana Coole)和萨曼莎·弗罗斯特(Samantha Frost)在《新物质主义:本体论、能动性和政治学》中指出,每一种物质形态都具有其“讲述”故事的能力。叙事能力是混杂形式的表达,物质叙事属于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语言和叙事是物体所固有的。瑟普尔·奥伯曼(Serpil Oppermann)在《物质生态批评:物质性、能动性和叙事模式》一文中指出,事物的能动性也可理解为其具有叙事能力,这种叙事能力又进一步拓展为讲述复杂爱情故事的“叙事能力”,则产物为“有爱情故事的东西”(Storied Matter),其讲述的故事成为物质文本。
二、《上层林冠》中物质的施事能力及意义的生成
《上层林冠》中的树木的施事能力并不是理查德·鲍尔斯的想象,赛仁娜拉·伊奥凡诺(Serenella Iovino)在《物质生态批评》中指出,物质的施事能力可以产生重要的影响,它们可以改变环境,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另外,树木不仅拥有出色的思考和沟通能力,还拥有自主意识。在理查德·鲍尔斯笔下,树的意义生成能力借助人类的活动而不断强化。
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帕特丽夏在其幼时因与生俱来的听力障碍无法与人类正常沟通而遭受社会的排斥,被人类驱逐。于是,帕特丽夏便每日与自然为伴,夜晚枕着松针睡在青苔上,与自然融为一体。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帕特丽夏获得了更多接近自然的机会,并且逐渐具备和树木交流的能力,成为树的知音。“一切高大的树干都环绕并守望着她”,帕特丽夏已经变成一棵被树所注视的目标。
通过与自然的亲密接触,帕特丽夏观察到了树与树之间的联系,并且开启了她的种子库项目。通过研究,帕特丽夏验证了树的社会属性,即证实树木彼此间可以相互交流、传递信息,甚至能够照顾彼此,在遇到危险时发出警报保护彼此。最终,帕特丽夏的研究在科学界得以认可。
《上层林冠》中,帕特丽夏坚信,所有生物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没有一种物种能够完全独立于另一种物种。树木也不例外,当一棵糖枫树遭受虫害时,它会发出求救和预警信号,以此提醒周围的树木,保护自己免受伤害。通过这种方式,其他树木可以分泌抗体来抵御害虫,从而减少损失。此外,部分植物的根部可以与土壤交融,相互输送养料,增强自身的保护能力,为下一代的繁衍提供支持。即使一棵树死去,它也不会消失,反而会在死后转化为营养,为其他树木的生长提供支持。
帕特丽夏指出,当人类走近树林时,树木会“感知”发出警报,提醒人们要小心,以免受到伤害。尽管树木可能会发出警告,但我们却无法从它们的话语中感知到任何信息。在“自杀树”中,帕特丽夏在一个生态专家聚集的地方,模仿了一生只能繁衍一次的传统,但最终她还是在众人的注视下,服下毒药自杀,并呼吁“不要自杀”的出现。
道格拉斯作为一名入伍军人,战争中他所在的飞机遭遇袭击并被击落,因挂在菩提树上而幸存了下来。理查德·鲍尔斯用大量笔墨对这棵菩提树的形成过程进行细致描述,菩提树经历了三百余年的成长后在关键时刻拯救了人类的性命。道格拉斯在此次经历之后开始加入种植花旗松的队伍中。这正是物质施事能力的体现。
三、《上层林冠》中物质的叙事能力及意义的传递
史黛西·阿莱莫(Stacy Alaimo)在《身体自然:科学、环境和物质自我》中指出,人类是由自然物质构成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本质上是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人类与自然发生关系并生成意义便是物质的叙事能力。
“桤木在谈论灾害,杨树八卦风的绯闻”和“诉说着曾经的灾难”“重复着风中的八卦”“预言着未来的天气”都展示了理查德·鲍尔斯如何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来描绘树木之间的对话,这表明物质也具有独立的叙事能力,可以被叙述出来。
《上层林冠》第一章中所涉及的不同主人公与树之间的故事都或多或少彰显了树木叙述事情的能力。尤根·赫尔一家是来自挪威的拓荒者,他们最终定居在美国中西部,并在那里种植了六棵板栗树,最终却只有一棵幸存了下来,当地人称之为“哨兵树”。约翰·赫尔决定每月拍摄一张照片,并将这一行动传承至后代,最终积累了数千张照片。赫尔家族四代人穿越时空,拍摄的“生成过程”见证着板栗树的变化,也记录着美丽的美景。这棵板栗树不仅仅记录了赫尔家族几代人的历史,而且还能够让人们通过拍摄的照片来重温当年发生的美好瞬间。
理查德·鲍尔斯希望借由赫尔家族的努力,使全世界都认清“生成过程”,“你们从来没见过完整的我们”,树木存在着多样性,而非仅仅局限于它们表层,因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树木,而非仅仅关注它们的表层。与树木相比,我们的寿命太短,仅仅可以观察它们的某些特征,正如赫尔家族几代人共同努力,最终将板栗树培育出了参天大树。
此外,咪咪·马一家种下的桑树陪伴着咪咪·马一家二十余年,用其一生讲述着他们的故事,并在最后与咪咪·马的父亲相继死亡,叙述着咪咪·马父亲的故事走向了结局。亚当虽然存在社交障碍,却能听到被麻布包裹的树向其诉苦并求救,随后亚当注意到了他姐姐种下的榆树逐渐枯萎,暗示着姐姐生命的消逝。雷和多罗茜一家遭受生活的打击后开始种植植物,任其野蛮生长,象征着雷和多罗茜一家得到慰藉后向往自由生活的状态。这一系列人类与树木之间的联系都是树的叙事能力的体现。
理查德·鲍尔斯选取自然界中随处可见的树木作为文本叙事的中心,将对宏观自然的叙事转移至自然界的一棵树上,把树的形象类人化,通过树木讲述故事,以树的视角看人类的行为,赋予了树叙事的能力,给予树人的生命力,并与人类的故事相融合,从而呼吁读者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上层林冠》不仅仅是“生态文学”的延续,它更加强调了树木的重要性,人们受到树木的影响,并最终成为它的忠实守护者,这也是对人类的傲慢、掠夺行为的深刻反思。
理查德·鲍尔斯在《上层林冠》中采用隐喻的手法以及寓言的形式书写树木的声音,从而支撑故事结构。因此,笔者认为树木作为自然的代表所发出的声音,以及自然的呼唤声对人类的启示值得后续研究。并且,后续对《上层林冠》的研究可朝物质生态主义批评视角下所描画的生态期望方向入手。理查德·鲍尔斯通过人与树之间的故事,深入探索了社会现状,并进一步探索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研究了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以及人类的发展前景,着重书写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且在其作品中传达生态思想,期望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枷锁,实现人类与非人类的和谐共生关系。生态批评家们认为自然是有灵性的,并且反对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此外,分析《上层林冠》中蕴含的生态主题,并促进人们对建设生态文明重要性的深入思考与反思,已成为对该作品研究的主要趋势。由此可见,《上层林冠》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生态文学”作品,更做到了以树为主角,而“人”则被树感召、指引,最终成为树的亲族和守卫者,这也是对人类的傲慢、掠夺行为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