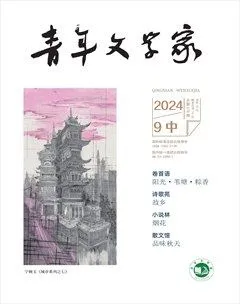浅析民间叙事视角与结构的创新应用

民间叙事作为一种蕴含丰富文化意蕴与独特审美价值的叙事策略,在重构民间历史记忆与故事讲述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贾平凹的《老生》作为民间写史的典范之作,不仅在叙事艺术上独树一帜,更展现了民间叙事视角与结构的深刻创新。本文主要从“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两个方面,对《老生》的“民间叙事”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探究小说的叙事视角,主要以唱师与匡三双线交叠、自我与他者内外透视两部分为主要内容;第二部分,以微观映射宏大,以及《山海经》的融入如何在结构上引导读者进行跨时空的思考,从而揭示作品在民间叙事结构上的独特贡献。
《老生》作为一部深植于中国乡土历史背景的文学作品,以时间为主线,精心构筑了近百年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历程。该作品不仅生动再现了历史的演进轨迹,更通过其独特的民间叙事手法,对既定历史叙事进行了富有洞察力的揭示与重构,展现了丰富的文学意义与价值。
一、民间叙事视角的分析
(一)双线叙事结构:唱师与匡三的视角交织
在文学作品《老生》中,其独特性在于运用“老生”这一角色作为贯穿全书的精神轴心,时间跨度自20世纪初延展至当代,借此映射中华民族历经百年的沧桑变迁。此“老生”角色,超越传统界定,具备沟通阴阳、横跨生死的“神职”特质,成为一位无所不晓的民间叙事者,全方位展现历史与人性的复杂交织。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入探讨唱师在小说叙事中的核心功能:
第一,唱师作为叙事载体的社会底层视角与宏观历史视野融合。《老生》巧妙利用唱师这一社会边缘角色,以其超脱凡尘的生命体验,构建起一种超越个体生命限制的广阔观察视角。唱师与匡三的双重视角交互叙事,不仅描绘了中国社会的动态变迁,也深刻反映了个人命运在历史洪流中的起伏跌宕。作者贾平凹选择唱师作为叙述者,意在借助其地位之低微透视历史的荒诞性。在丧葬仪式中,唱师的特殊位置赋予其审视时代风云变幻的独特高度和深度。
第二,唱师作为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与叙事者的三位一体。在承担叙述任务的同时,唱师亦是小说内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其叙述因此具备更高程度的真实性与亲近感。尤其在第三个故事中,唱师自身遭遇的挑战与困境,如艺术生涯的衰落,进一步强化了其叙述的真实性和多维度,展现了贾平凹在叙事技巧上的创新尝试。
第三,唱师角色在情节构建与人物引入中的关键作用。小说利用唱师执行丧葬仪式的职业特性,通过其行走秦岭各地的经历,自然引出一系列关键人物及其故事线,如老黑、李得胜等,有效推进了情节的展开。唱师的活动轨迹成为连接各个人物命运与历史事件的纽带,展现了作者精巧的结构布局。
第四,唱师叙事下的悲情美学与生命哲学探讨。全书以唱师的阴歌为情感基调,预设了一种内在的悲剧色彩,尤其是对死亡、消逝的深刻反思。唱师虽目睹生死,却也无法逃脱终将归于尘土的命运,这一设定强化了作品的悲剧美学。同时,通过唱师的见证,小说展现了如游击队的惨败等历史悲剧,以及戏生、白土等人物的生死轮回,深刻揭示了个体在历史大潮中的渺小与无力,以及生命在无奈中的延续与变迁。
同时,人物匡三在《老生》这部作品中作为四个独立故事间的联结纽带,扮演了至关重要的结构整合角色,其轨迹贯穿作品始终,确保了小说叙事的完整性与连贯性。匡三首次亮相于首篇故事,其因生计所迫加入游击队的经历,不仅串联起游击队兴衰的完整历程,其作为幸存者的身份更是自然过渡到第二篇章,其间叙述了他解放岭宁县并担任兵役局局长的后续经历,以及对白河长子白石职业道路的影响。尤为重要的是,匡三在第三个故事中对唱师命运的干预,将唱师的职业身份从县文工团的边缘角色转变为斗争史编写组的负责人,实现了唱师社会地位的戏剧性转变。
因此,通过匡三这一角色的精心布局,四个故事在《老生》中形成了既独立又相互勾连的结构整体,实现了断点中的连续与繁复中的有序。尽管各故事在情节上保持相对独立,但作品整体的统一性与深度,则是通过唱师这一核心人物的成长与发展脉络得以巩固和深化。匡三作为辅助视角的巧妙运用,不仅放大了小说中村庄、小事件与小人物的叙事格局,使之承载了更广泛的历史与时代意义,还成功引导读者窥见特定地域与时代背景下微观社会的历史印记。
(二)自我与他者:内省与外察的叙事策略
在《老生》的分析框架中,唱师这一角色的建构与叙事策略展现了贾平凹独特的艺术构思。尽管唱师同其他虚构人物共存于文本之中,其叙述方式却显著区别于传统的小说叙述模式,摒弃了直接采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常规路径,转而采取了一种创新性的叙述手法,即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述视角的灵活交织与转换。这种叙述模式不仅增强了叙事的流动性和多维度,还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认知视野和深层的情感共鸣。
具体而言,唱师作为叙述主体,其角色的特殊性在于能够灵活运用第一人称叙述,建立起与故事世界的亲密联系,同时又依托全知叙事者的特权,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穿梭于故事的各个层面与时间维度之中。这种叙述策略有效地模糊了叙述界限,使得唱师既能作为故事的亲历者,直接参与并见证事件的发展,又能超越单一人物的局限,洞悉并评述故事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外部环境,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叙事的真实感与深度。值得注意的是,唱师的直接现身在文本中相对稀少,仅在二十二个片段中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出现,而其余大部分篇幅则采用了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该视角赋予了叙述无限的自由度,使文本得以跨越时空界限,展现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场景与复杂人性,既深化了文本的真实质感,也拓展了叙事的空间与深度。
贾平凹对第一人称叙述的运用,超越了单纯强化个人体验的传统功能,同时,通过巧妙融合第一人称的亲历性与第三人称的全知性,克服了单一叙述视角的局限,实现了叙述视角的动态转换与叙事深度的拓宽,进而丰富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与思想内涵。
二、民间叙事结构的分析
小说“《老生》—由《山海经》片段与四个主体故事构成一种互文性的叙事结构。以某部古代经典著作为蓝本,来设置自己作品的基本叙事构架,建构起一种互文性的叙事结构”(韩鲁华《〈老生〉叙事艺术三题》),同时又运用单线式的叙述方式,呈现四个故事的具体所指,两种叙事方式的结合构成了小说的民间叙事的结构。
(一)微观透视宏观:《老生》中村落与时代的叙事映射
《老生》作为一部结构独特的文学作品,由四个相对独立而又内在勾连的故事单元组成,通过非线性叙事手法,以唱师和匡三为隐形线索,将这些故事编织成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作品选取清风驿、老城村、棋盘村、当归村四大场景作为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横跨多个历史阶段,从1949年初期到改革开放后,全面展现了在不同社会变革语境下,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这一历程揭示了在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呈现了历史进程中的多样面貌及人民生活的变迁。
小说以“秦岭里有一条倒流着的河”开始,在《山海经》的铺陈下,故事沿着上元镇说起,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分为四个地方发生的四段故事,上演着一场场“声响和色彩的世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上元镇、正阳镇、清风驿,以老黑、李得胜、匡三等主要人物与县保安团的恩怨情仇为发展线索,将叙事视角集中在特定时间与空间下,展现20世纪初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进程。在现代性与乡村社会融合的进程中,有老黑与王世贞的恩怨情仇,延安进步青年李得胜的革命,在这片淳朴的土地上上演着剧烈的社会动荡。乡村社会的愚昧、野蛮与革命的偶然发生交织混合,衬托出枪和死亡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剧烈破坏。随后,历史仍然保持革命的惯性发展,第二个故事作者则以老城村的马生、王财东、白土、玉镯几人的感情交织为主,在这个阶段中,阶级对立拉出的仇恨依然惨烈,即便如此,小说中白土与玉镯的故事让读者重温了磨难中爱情的温馨与感动。第三个故事中,阶级矛盾已经不能以滑稽荒诞来叙述,甚至可以说是到了另一个极端,在棋盘村的这场闹剧中,故事最终却由一个被随意指认的坏分子—全村最漂亮的女人来承担后果,这样的斗争融合着荒诞,即便是悲剧,也糅合进了喜剧的成分。第四个故事是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当归村展开,戏生成为当归村的村主任后,带领村民种植当归发财致富,终于换来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却赶上了百年不遇的瘟疫,全村死伤者大半。沧海桑田的变化是在警示着历史在完成了一个百年的轮回。就此,小说在隐隐的叹息中走向了结局。
(二)经籍牵引叙事:《老生》中《山海经》的嵌入与叙事创新
《老生》的结构布局独树一帜,不仅在于四个相对独立故事的巧妙编排,更在于其对《山海经》的深度运用。小说中,贾平凹巧妙穿插《山海经》原文片段,并虚构师生对话场景,以此作为各章节的开篇,形成了独特的叙事框架。这种创新性介入不仅为故事进展提供了新颖的衔接机制,还通过对《山海经》的现代解读,赋予这部古老文献以新的生命力与文化意义。师生间的虚拟问答,一方面作为叙事的引子,引导读者进入故事的特定情境;另一方面,它也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对话空间,既是对古典文本的再诠释,也是对当代社会与历史的深刻反思。“近三十年来,人们有如牛马一般被激发而膨胀起来的物质欲望所驱动,人们生活在紧张、重负、逼仄、压抑的精神状态之中。而这些历史与现实的种种是非,与在人类文明大举向自然进攻之前的《山海经》的山、水、植物、动物、矿产等组成的天地浑然,宇宙苍茫的世界一对比,就会感觉到在这样的大视野中,人类显得多么渺小,而人性堕落或丑恶导致的人类生存的悲痛与不幸,也似乎给融入天地之间而化为无了。也许这也可算是一种人类学观照人类生活历史与现实的视野。”(王光东、郭名华《民间记忆与〈老生〉的美学价值》)
尽管有批评指出,《山海经》的嵌入手法略显生硬,但从艺术创新的角度审视,贾平凹的尝试无疑是旨在开辟一种新的历史书写路径,试图通过这一独特的文学实验,引领读者回溯人与土地的深远联系,探索历史与文化的深层意蕴。基于此,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深入探讨《山海经》在《老生》中的艺术结构意义:
第一,叙事氛围与基调的和谐共生。《山海经》所述的山、水、神怪等充满着一种神秘和传奇色彩,而作者在《老生》中讲述人、事、物的命运,可以看作从野史或逸闻趣事方面生发,也大多带有传奇和神秘性。在《老生》中穿插引入《山海经》的相关章节,也直接将这种神秘感和神话故事的美感转接到了《老生》的故事之中,并且让小说中如唱师等带有神秘性的人物和相关传奇情节的存在具有了某种合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读者与小说中所写内容的距离感,所以《山海经》的叙事格调和小说的氛围是比较吻合的。
第二,时空同构的叙事架构。《山海经》的引入,可以看作是作者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在努力寻求一种时空同构的结合。“《山海经》上古、高古的民间记忆,和现当代的民间记忆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照甚至颉颃的关系。这种时空观念带来的是对于中国现当代史别样的理解,开掘出小说更为深层的思想意蕴。”(舒晋瑜《贾平凹:〈老生〉的写法是效法自然》)
第三,叙事技巧的创新借鉴。贾平凹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他一直苦恼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将自己经历的这几十年和所了解到的几十年,共计一百余年的历史写出来。《山海经》中“一座山一座山地写”的叙述方式给了贾平凹极大的启发,于是贾平凹选择了“一个村一个村,一个人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这样的叙述方式,将历史铺展开来,让读者在回望祖先遗留的光辉的同时,更见证了当下的历史。《老生》无绝对主角的设计,正如《山海经》中各山各水皆有其独特的异人神怪,体现了贾平凹对多元叙事与历史多声部的追求,展现了他在叙事方式上的独到创新与深刻思考。
在《老生》这部作品中,贾平凹通过将当代文学创作与先秦时期的古典文化典籍有机融合,实现了现代叙事技巧与古典美学旨趣的和谐统一,这一创举无疑标志着文学表现手法的跃进。他不仅跨越了时间的界限,还在文学创作领域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成功地在保留古典韵味的同时,注入了现代文学的新鲜血液,为文学创作的跨界整合提供了富有启示意义的实践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