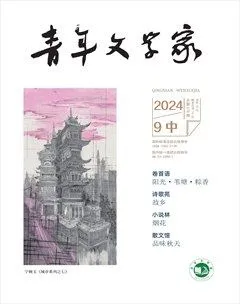《诗经》中的疾病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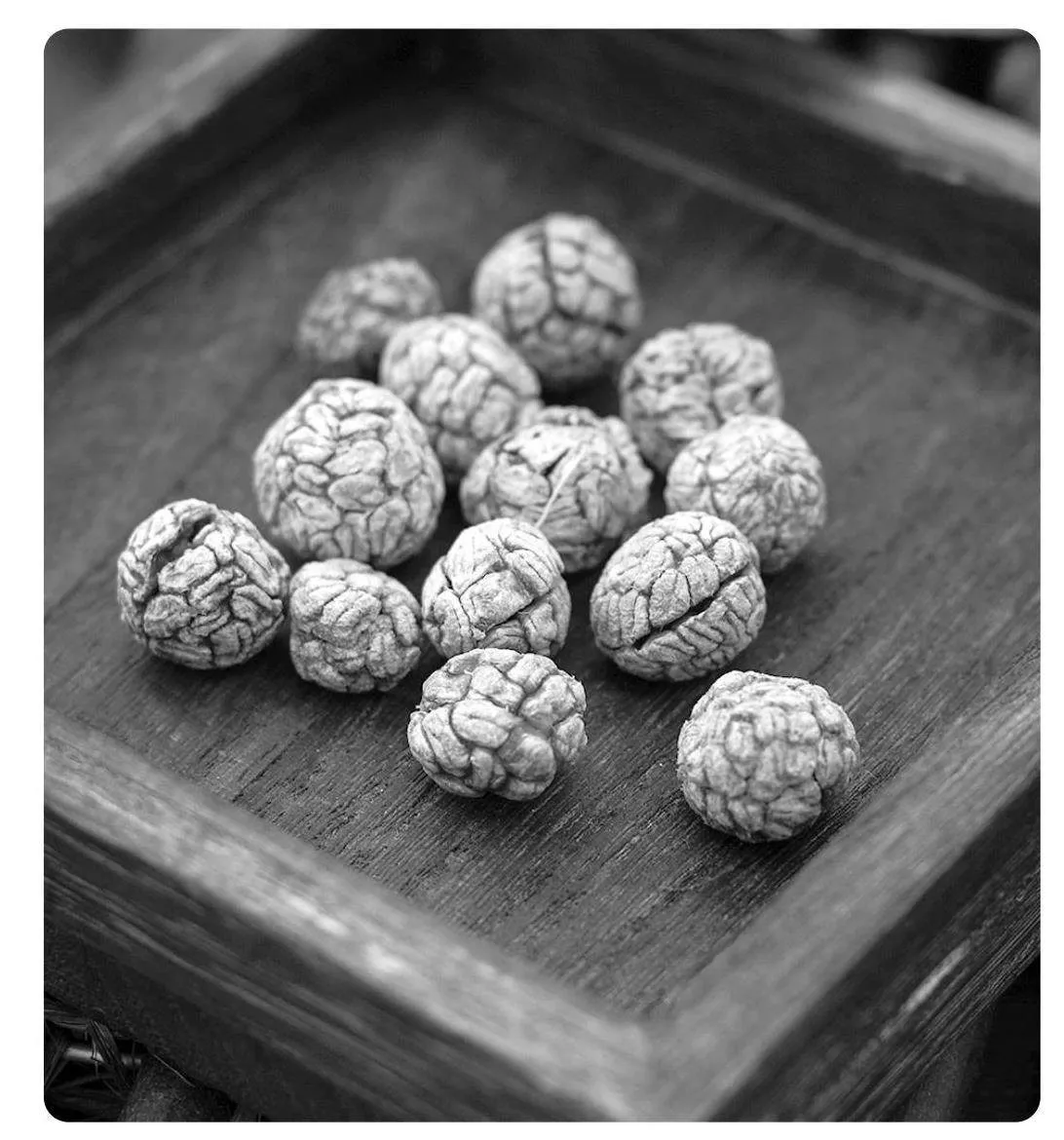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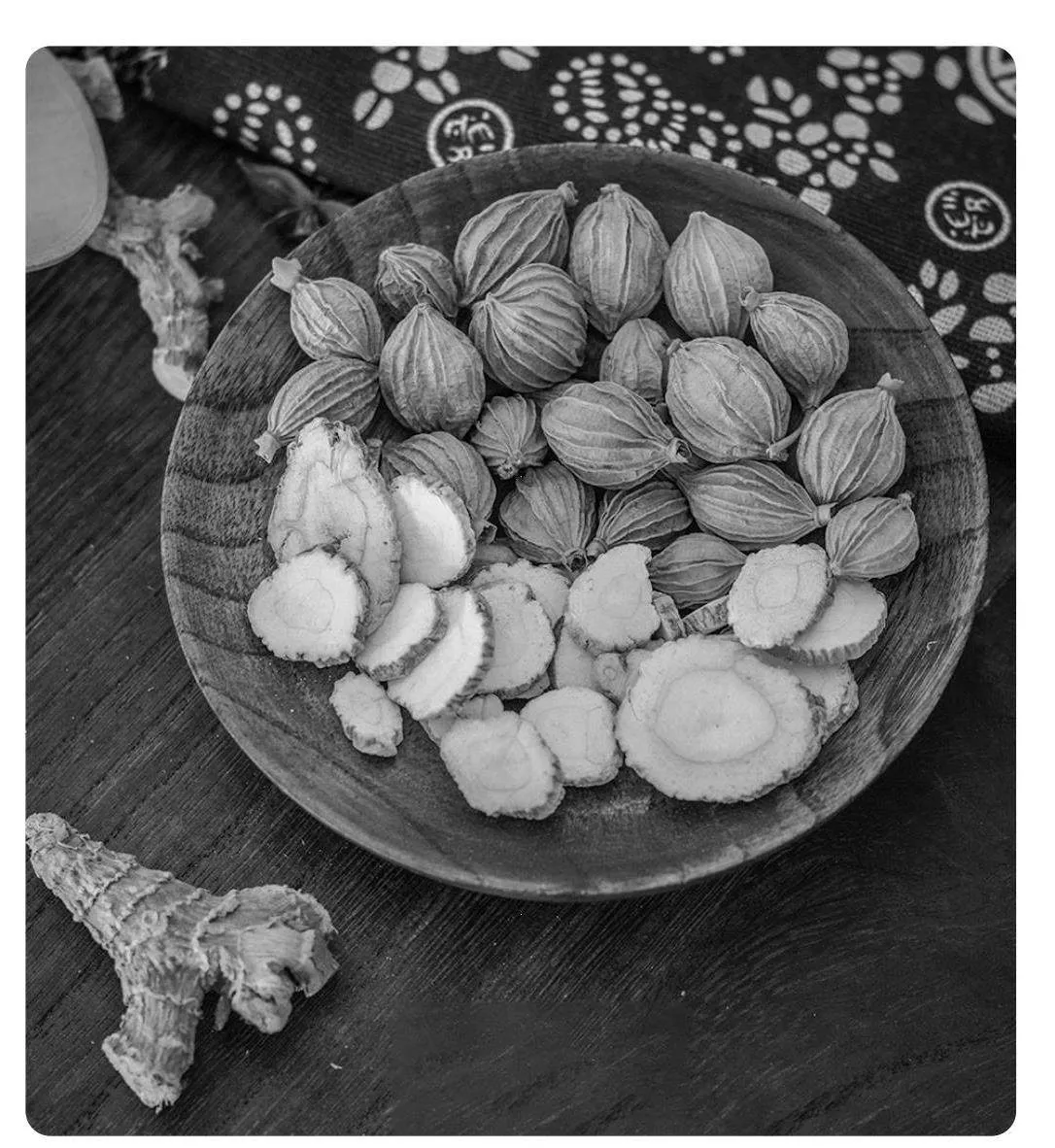
无论是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抑或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人类从未脱身于疾病的诅咒。文学起源于生活,并以更为艺术的手段生动地反映着生活。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疾病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诗经》既是诗歌创作的源头之一,也开创了中国古代疾病书写的先河。
谈到疾病书写,首先就要做一个概念界定。根据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可知,“病”指“生理上或心理上发生的不正常的状态”。所以,本文所涉及的疾病均指此不正常状态。因材料缺乏,且古人对于心理疾病的认识不够深入,对生理疾病之判定较易,而对精神疾病之判定则较难。故而,本文所指的“疾病”均属于生理疾病。当下对于诗歌疾病书写的研究并不少,对于《诗经》的研究更是成熟,但对于诗歌疾病书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唐宋诗歌,对《诗经》中的疾病书写只作创作源头上的肯定,并没有专论梳理。因此,本文采用文本细读法来对《诗经》中的疾病书写进行解读,旨在对其有一个粗略的认识或初步的理解。
一、《诗经》中疾病书写诗句概述
《诗经》的源头性地位,注定了后世大多数诗歌类型都可在其中发现雏形,疾病诗亦循此例。由于《诗经》中的疾病书写都属于“涉病诗”范畴,所以只要是诗句中出现了疾病类词语,都是研究的对象。通过数据统计发现,在《诗经》的三百多首诗歌中,涉及疾病的诗歌就有至少二十四首,可以看出《诗经》中的疾病书写并不是偶然现象。在“文史哲不分,诗乐舞一体”的时代,《诗经》根据音乐上的特点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有关疾病的诗句属于“雅”类的最多,“雅”类里面属于《小雅》的最多;最少的是“颂”类,仅在《周颂》里出现了一例。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就各类数量来看,“颂”类诗歌数量最少,基数小一些,有关疾病书写的诗句也就少一些;另一方面可能与各类的功用相关,“颂”主要是用来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内容多是歌颂祖先功业,多是一些赞颂之词,与疾病相关的词语进入到歌辞里面的可能性比较小。当然,“风”作为地方音乐,还是诗歌数量最多的一类,疾病书写的诗句并不多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相关诗句中表示疾病的名词很多,如“疾”“瘳”“疚”“瘉”“瘼”“瘨”等,这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先民对于疾病已有了较为细致和深入的了解。
二、《诗经》中的疾病书写与情感表达
具有“兴、观、群、怨”功用的《诗经》,从一开始就具备着可供无限阐释和挖掘的情感。从文学创作论的角度看,写作者的创作动机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方面是外部情境因素,写作者触景生情,从而进行创作;另一方面是写作者内心本来就有意想要抒发而进行创作。无论哪一种,都是写作者想要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某种情感。由于创作主体的不同,采用的情感表达手段也就不同,但也无外乎直接表达和间接表达了。借用疾病书写来表达情感很显然属于间接表达方式,那些诗歌的写作者们或通过疾病类的词语来模拟心情状态,来表达情感之真挚,或直接以疾病之本意来表达情感之深切。
(一)以疾病类词语模拟心情状态来表达情感
这类诗歌占《诗经》中涉病诗歌的绝大多数,其中又可以细分为两种,即以疾病模拟心情之忧郁和以疾病之愈模拟心情好转。属于前者的如《卫风·伯兮》,诗中写道:“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这是一首描写女子思恋远征丈夫的诗,诗中出现的疾病类词语是“首疾”和“心痗”。“首疾”是头痛的意思,“心痗”即指心痛,“伯”是周代女子对自己丈夫的称呼。丈夫因远征而离家。都说“女为悦己者容”,自丈夫离家之后“我”再也没有心思梳妆打扮了,和一心想着下雨却出大太阳一样,一心思恋着远征的丈夫,“我”却很难见到。只想说绵绵无尽的思恋,已经让“我”头痛不已。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株忘忧草,把它种植在北堂,“我”因为太过思恋丈夫,已经心病恹恹。在这里诗人通过“思”字明确表达了思恋之情,同时还借用了“首疾”“心痗”两词,来模拟思恋忧郁的痛苦,加深了思恋之情的程度。属于后者的仅有一例,那就是《郑风·风雨》,其中写道:“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膠膠。既见君子,云胡不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是一首描写妻子和丈夫久别重逢的诗。全诗三章,每章皆以风雨、鸡鸣起兴,这些兼有赋景作用的兴句,渲染出一幅寒冷凄清、鸡声四起的背景图,勾起人的离愁别绪,但好在这位苦苦怀人的妻子是幸福的,在这个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她的丈夫冒雨不期而至。“既见君子”之时,那种喜出望外之情,溢于言表。恰如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羌斋诗话》)。诗人一唱三叹,连用三个反问句,通过“夷”“瘳”“喜”三字表达出自己的喜悦之情。这首诗中出现的疾病类词语是“瘳”,病愈的意思。诗人用疾病之愈模拟由相思抑郁到“既见君子”之时的心情好转,既表现出自己曾经相思之深就像生病一样,也表现出如今见到丈夫后心情的无限喜悦。
(二)以疾病类词语之本义来表达情感
这类书写只占《诗经》中涉病诗歌的小部分。例如,《周南·卷耳》中写道:“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这虽是一首描写妇女想念她远行丈夫的诗歌,但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着重表现的是想象中思念对方,赶着回家的劳苦之状。全诗四章,第一章实写,通过“怀”字点明相思之情,二、三、四章是想象的情况,虚实结合,情感递进。此诗中出现的疾病类词语是“虺隤”“玄黄”“瘏”和“痡”。“虺隤”是指腿软的病,“玄黄”是指马久病毛色变黑黄,“瘏”是病的意思,“痡”是指过度疲劳而累病。在诗人想象的世界中,由于路途的奔波遥远,丈夫的马儿累坏了,仆人也累倒了。虽然在二、三、四章中没有直写思念之情,但是在诗人深切周至的想象中,思念之情就像桃花潭水一般细腻深长地涌了出来。此类中有一首值得注意的诗,那就是《豳风·鸱鸮》,“鸱鸮”为我国诗歌史中第一次出现的处于疾病状态的动物形象,诗中写道:“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这是一首禽言诗,全诗以一只母鸟的口吻,诉说它的过去,并抒写了它育子修巢的辛勤劳动和目前处境的困苦危险。这当然是一首有寄托的诗,诗人是想通过动物之口道人之遭际。诗中塑造了一个病鸟形象,来喻指作者饱受剥削的艰苦处境,抒发对于剥削阶级的不满之情。属于此类的还有《小雅·菀柳》等。
处于生老病死轮回中的人们,疾病的话题是永恒的,疾病带来的感受是深切的。通过《诗经》可以发现,早在数千年前的人们,就已经用疾病的感受来形容日常生活的遭际与情感了。
三、《诗经》中的疾病书写所体现出来的疾病观
周人的疾病观念是对商人疾病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商代的社会背景呈现出神权色彩浓厚的特点,鬼神观念极为兴盛。商代走出了原始社会,万物有灵的思想却延续了下来,并影响着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神灵降疾的思想非常浓厚,并且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周人对“德”内涵的改造可谓政治活动的一大创举,殷商因汤的德行而兴,因帝辛德行败坏而亡,周人认识到天命可以转移,因此周人有意识地赋予“天”道德与情感。“天”成为一种理性存在,其降灾与赐福和周王的德行息息相关。周人把疾病视作上天的警示,疾病来临时则会考虑自己是否有背德行为。这一点在《诗经》中的疾病书写中有所反映,如《小雅·节南山》,诗中写道:“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节彼南山,有实其猗。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这里的疾病类词语是“瘥”,本义为病愈,引申为瘟疫疾病。全诗十章,这段属于第一、二章。这是一首周大夫家父斥责执政者尹氏的诗。此二章以南山起兴,象征权臣尹氏,以山之险要象征其权之枢要,又以山之不平联系到尹氏秉政不平。首章点出“不敢戏谈”以致“国既卒斩”;二章点出上天再降饥疫以致“丧乱弘多”,民众无法存活,从而“不敢戏谈”之高压失控,遂而“民言无嘉”。一章言人祸,二章言天灾,由时间及顺序暗示天灾实乃人祸所致。
《诗经》中除了上述具有“天诫说”色彩的上天降疾观,还体现了气滞致疾的观念。无论是前文所述的相思之情还是怨刺之情,还是没有进行分析的如《小雅·采薇》所表达的思乡之情等,都用疾病的感受来表达其情之深。不管这种描写是诗人真的因为相思而头痛生疾,还是出于夸张的需要来表示其情之深,都能够认识到,诗人有意识地将情感滞涩得不到满足与疾病联系在一起。中医上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句话,放在此种语境下似乎也可理解。“六气致病说”在《左传》中被系统地提出,秦国的医和为晋平公治疗疾病时,子产认为晋平公疾病的源头不在于神灵“实沈、台骀”,而在于劳逸、饮食、哀乐不适度的缘故,在这些方面未能做到“节宣其气”。由此可见,六气失和致疾的观念并非偶然提出,而是基于当时较为成熟且普遍接受的共同认知,实乃对前人疾病观念的总结。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诗经》中的这些疾病书写,反映了当时人们所存在的无意识的疾病认知。
当然,如果抛开中医学的角度,站在文学自身规律来看“气滞致疾”观念,或许可以理解为,这些是诗人因欲望阻滞而试图精神突围的审美结晶,只不过是采用了疾病书写的方式。正如休谟在《人性论》中所说,“自然赋予人类以无数的欲望和需要,而对于缓和这些需要,却给了他以薄弱的手段”。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欲求因外在客观世界的束缚而无时不处于驱进与自我调适的矛盾与挣扎之中。人类既“因自己力量的有限而无法抗拒自然、社会对人的压迫而生苦难”(谭大友《生存智慧的当代阐释》),然而在此基本底色之上,诗歌作为描写人类社会图景、表现对自我与世界认知的文体,于此有鲜明表现。或许也可以说,所有文学作品的表达都是抒发作者内心欲望阻滞、追求欲望畅通的结果。
《诗经》中的疾病书写可以折射这一时期人们的疾病观念是毋庸置疑的,结合这一时期的其他文本来讨论会显得更加丰富。如果抛开医学的角度,从文学自身规律来看也许是另一个话题,值得进一步挖掘与深入。
《诗经》经典性的体现,不仅仅是因为文学史对它的书写,更重要的是其自身所具有的无限释读性。首先,本文从疾病书写的角度观照了《诗经》。得益于数据上的统计,我们才能知道从疾病书写的角度出发具有可行性,同时也积累了文本基础。其次,笔者看到了诗歌具有的表情达意的功能,探讨了《诗经》疾病书写与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可知早在数千年前的人们,就已经用疾病的感受来形容日常生活的遭际与情感了。最后,本文站在历史的维度,粗略解读了《诗经》中疾病书写所体现出来的当时人们的“上天降疾”和“气滞致疾”疾病观念。同时也看到,就文学自身而言,所谓“气滞致疾”而形成的诗歌,或可理解为诗人因欲望阻滞而试图精神突围的审美结晶。
本文系2023年“西华杯”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李调元《新搜神记》涉梦故事研究”(项目编号:xhb2023027)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