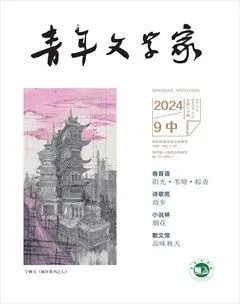论宋元学者对《论语》中“樊迟学稼”的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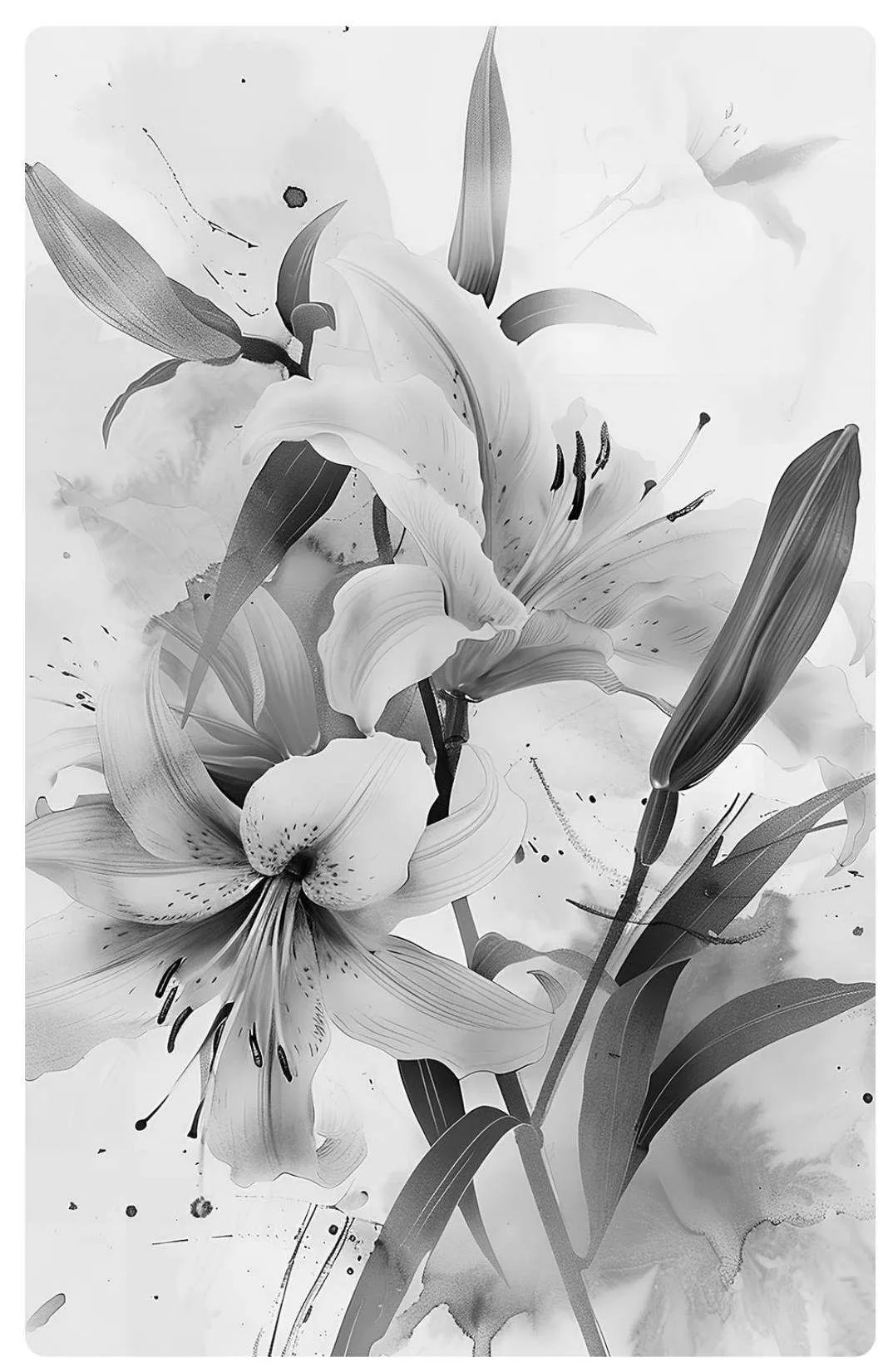
“樊迟学稼”是《论语》中的一个章节,出自《子路》篇,历代学者都对其进行过解读。对于孔子称樊迟为“小人”这一行为,宋元学者都以“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观点来解释。这一观点无疑体现出宋元时期理学强调对儒家“道”“德”“义”“理”等抽象概念予以重视的思想特点。《“樊迟学稼”诠释史》一书则正是通过梳理包括宋元在内历代士人关于“樊迟学稼”章的诠释,从而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发展进行回顾。本文也正是充分利用该书作为研究基础,分析宋元学者对“樊迟学稼”的解读,探析其传承与发展。
作为中国传统学术发展体系的主体,儒学发展历经其草创与发展、低落等阶段,而至中唐则又产生新的变化。中唐时期,新禅宗运动、新文学运动与新儒家运动三者共同推动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儒家思想也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变化,于北宋时演变为日后主导中国思想文化主要形态的理学。在这一“新儒学”的思想指导下,宋元学者关于儒家经典的诠释与解读也就具有与前代所不同的表现。
一、宋元学者对“樊迟学稼”的诠释与解读
与唐代以前的儒学思想不同,宋代兴起的理学则更着眼于儒学“形而上”层面的体系建构。在释老学说的冲击与挑战下,为儒学奠定哲学形式上的内涵,成为宋代儒学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故而,理学在哲学形态上更具思辨性,其关注点也多在“道”“理”“气”等抽象概念上予以发挥。这种学术取向上的转变,在宋代以及理学成为官方权力话语的元代时期的士人对于经典的诠释中得以体现。以《论语》“樊迟学稼”章为例,在理学思想影响下宋元时期对其的解读更多基于“本末”,也即“大”(礼、义)、“小”(稼、穑)层面进行探讨。
(一)关于“学稼”与“小人”的讨论
正是在强调儒家思想中抽象概念的哲学内涵这一背景下,宋元士人更进一步将“君子”所应具有的人格特质予以理论层面的强化,甚至于将之进行严格的限定。故而,对于在《论语》的原本语境中与“君子”“大人”有着一定区别的樊迟,宋元士人则在其构建的叙述话语中将他的这种差别进一步放大。
宋代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云:“樊须游圣人之门,而问稼圃,志则陋矣。”朱熹在《近思录》中也指出,“樊迟请学稼圃,而夫子斥以小人”。朱熹认为樊迟在孔子之门却未学该学之事,这是他被称为“小人”的原因。
元代史伯璿在《四书管窥》第三卷对“樊迟学稼”也有阐释,在这一篇中着重解释了“小人”这个概念,这里“小人”被解释为以度量大小而言的与“君子”相对的概念。书中说道:“《君子儒》章考证谓《集注》程、谢二说,恐子夏不至此云云。文公尝言子夏太细密谨严,又云其促狭于子游。叶贺孙之问,亦言其太紧小。如此,则君子、小人只是以度量规模言。若樊须小人之类,盖对大人、君子言之,特有小大之分耳,非言善否之殊也。”史伯璿还提出:“儒是学者之称,樊迟以学稼圃而见斥为小人,岂可援以为例?”作为论证,即认为“小人哉,樊须也!”是不可以被用于论证程子所言的“君子儒为己,小人儒为人”。
元代王义山在《稼村类稿》中亦言:“周公以勤劳稼穑之人为小人,即夫子以问稼之樊迟为小人。夫子所谓小人者,非对君子小人并言之小人也。”并引用了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所说的“小人,细民也”,即“小人者,细民之事”,作为“小人”即“细民”的解释。
无论是宋代的朱熹、杨时等人,抑或元代的史伯璿、王义山等人,足可见宋元士人都大体强调“小人”和“大人”的差异。这一大表现就在于二者的分工各有不同,“大人”通过“劳心”来治理百姓,“小人”通过“劳力”来供养大人。由此,与“稼”“穑”等“劳力”相关的“小人”观念也就为宋元士人所建构产生。
(二)对“大人”及其人格与责任的叙述
由是,在宋元士人的话语体系中,能够教民以礼义的“大人”,其境界与重要性也就远胜过于樊迟所代表的从事“稼”“穑”的“小人”。这种“大”“小”的取舍很明显地体现在宋元士人的著述之中。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樊迟学稼”进行了解读,他说:“礼、义、信,大人之事也。好义,则事合宜。情,诚实也。敬服用情,盖各以其类而应也。襁,织缕为之,以约小儿于背者。”可见,朱熹也认为礼、义、信是“大人”所作之事,统治者崇尚义则事事可以合乎情理。百姓的敬重和信服是对统治者崇尚礼、义、信的回应,那么就无须学习种稼。
宋代钱时在《融堂四书管见》中说道:“农圃,小人之事也;礼义信,大人之事也。上之所好者大,则在下者莫敢不承,四方之民从之如归矣。何以稼为哉?”礼、义、信是“大人”做的事。如若统治者崇尚“大人”之事,稼穑之事就不必亲自学习了。
宋代陈祥道在《论语全解》卷七认为:“樊迟不知君子之道,而请学小人之事。”精通大道的人,可以处理各种事务。由此可见,陈祥道把学稼归为“小人”之事,如统治者推行礼、义、信,那耕种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元代胡祗遹在《紫山大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指出孔子以礼、义、信答“樊迟学稼”是“富哉言乎”,即认为这种回答是富有哲理的。在他看来,以礼来规范臣民,则统治者可以得民心;以义来引导百姓,百姓则心悦诚服;以信来教化臣民,则统治者能体察实情。胡祗遹认为,相比于“稼”“穑”等“末”,能够实行王道安定天下对于“士”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元代何异孙的《十一经问对》同样以道义作为讨论“樊迟学稼”问题的标准:“问:‘《子路》篇樊迟学稼圃,其意谓道之不行,不若田园之为乐,何孔子责之之深?’对曰:‘此迟务外规利,屏大就小之见,谓学稼则必有禾,学圃则必有蔬。未若正谊而利不敢谋,明道而功不敢计,夫子既答以吾不如,且俟其出,而责之以小人也。’”何异孙从利义观出发解读“樊迟学稼”,认为樊迟研究问题没有深入研究而只停留于表面,只谋求利益而忽视了对道义的追求,显然他认为“樊迟学稼”只是谋利的小事,与仁义之道大不可比。
通过以上诸例可以看出,对于宋元士人而言,“君子”与“大人”所应关注的,正是要追求用礼、义、信教化百姓的大道,并且认为只要实行了这一大道,那么耕作等事也就自然得以解决。而这也正是理学强调以儒家圣人人格为标准,以实现“内圣外王”为终极人生目的的思想主张的具体体现。
(三)“稼”“穑”与“本”之间关系的讨论
此外,在宋元士人关于“樊迟学稼”章经义的表述之中,还应注意的一点在于,其对于“稼”“穑”等事,认为要有“本”上的界定。
宋代戴埴在《鼠璞》指出:“夫子固以须无志于大而鄙之,然夫子所谓不如农圃,则是真实之辞。古者,人各有业,一事一物皆有传授。”在戴埴看来,农圃等事是各有专业、各有传授的,故而,樊迟以“稼”问孔子,则无疑是一种在职分上的错误。
元代胡炳文的《四书通》卷七中同样提到这种“术业专攻”的观点。他引用了冯氏之说“周宫阁师伍农以耕事,仕圃以树事。术业有专攻,稼圃亦二有业,不通习也。而谓圣人兼通之手?”和韩退之所言的“圣贤之能多,农马之知专故也”来论证学稼圃之事有专攻,孔子可能未必精通稼圃之事。
胡祗遹在《紫山大全集》第二十二卷云:“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盖学业有专攻,苟以不通无用之虚言乱人耳目,则不若不论之为愈也。老子亦曰:‘我无事而民自富。’唐柳子厚见当时劝农之弊,反致劳民,废夺农务,故以种树为喻,而作《郭橐驼传》。”可见胡祗遹先是就事论事,从术业有专攻的角度来解释学稼之事,如不精通农圃则不如不说。
宋元士人这种对于“樊迟学稼”予以“专攻”与“本务”的解读,认为其理应是一种对于身份与职分的区分。他们认为,“稼”“穑”应是专业从事这一工作的农人的职分,而并非理应有更高要求的“君子”所应着力的本务。这种观点同样也是理学强调“内圣外王”,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为人生终极意义的思想的侧面反映。
二、宋元学者对“樊迟学稼”的解读中体现的传承与变化
从前文中可以看出,宋元学者在看“樊迟学稼”这一问题上有传承之处,如陈祥道在《论语全解》中说:“君子能为小人之所不能,而不能遍能小人之所能。”王义山亦言:“周公以勤劳稼穑之人为小人,即夫子以问稼之樊迟为小人。”可见“君子”与“小人”的责任各有不同,这一点得到了宋元学者的认同。元代学者在对“君子”“小人”的解释上进一步阐发,如何异孙“未若正谊而利不敢谋,明道而功不敢计”之语,即是从利义观角度进行分析,指出樊迟认为学稼就一定可以得到禾,学圃必定可以得到蔬,是着眼于小利,与仁义之道相去甚远。而在术业有专攻的问题上,宋元学者也持有较为一致的意见,如戴埴、胡炳文、胡祗遹等都阐述过相似的观点。从整体上来说,宋元学者对于“樊迟学稼”这一问题的理解基本一致,都极为强调统治者崇尚礼、义、信并用此教化百姓的重要性。而这种对于礼、义、信等抽象道德原理予以的高度关注,则正是理学思想一个重要的特点。
作为一种对于中唐以来社会思想发展新变化的回应,理学在北宋产生,并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人的推动下逐渐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至元代被官方确立为科举的正统学说,遂与政治权力相结合,而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理学的话语体系建构之中,儒学本有的伦理内核被赋予以高度形而上的抽象内涵。仁、义、礼、智、信等伦理概念也就被视为根本道德原理,并被进一步论证其内在基础。由此,这些道德品质以及具有这一系列品质的“圣人”自然被理学者极力推崇至极高的地位。而实现这样的道德原则和理想人格,达到“内圣外王”的精神境界,也就成为理学思想的接受者所孜孜以求的终极人生归宿。故而,在此影响下,宋元学者对“樊迟学稼”诠释解读也发生了变化,更加侧重于对抽象哲学概念的强调与重视。
本文结合《“樊迟学稼”诠释史》一书,研究分析了宋元学者对该典故的不同的解读,试图通过对宋元士人的解读来对宋元理学的一些特点进行讨论。
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而言,如何把握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这是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黄俊棚所著的《“樊迟学稼”诠释史》一书,则正是对此所作的一种回答。其完整地梳理了中国古代各学者对于《论语》“樊迟学稼”一章的诠释解读,其中更是包括了杨时、朱熹等理学大家。这对于学术研究,尤其是对于宋代理学思想的相关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意义。此书以汉唐开篇,以明清结尾,文中内容、注释较为准确,引用文献均出自正史,较为全面地囊括了“樊迟学稼”有关内容的史料,为后续学者继续深入研究“樊迟学稼”问题提供了较大便利。此外,耕种之事在古代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古代有关农业的书目并不多,本书有关“樊迟学稼”的论述或可部分回答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