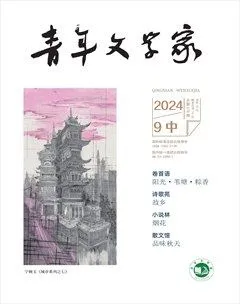游于幻境,行在当下

《镜花缘》是我国19世纪清代文人李汝珍创作的长篇古典小说,江宁桃红镇的民间坊刻本于1817年问世,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小说以百花仙子下凡的神话故事为发端,通过主人公唐敖等人的海外游历,引出唐小山的寻父之旅和百位才女中科的故事。作者用游戏的心态、诙谐的笔法和别样的旨趣,为读者呈现了一部如“镜花水月”般虚实相间,又极具社会现实意义的优秀文学作品。
近年来,多有学者将《镜花缘》作为描述人物游历过程来建构情节、叙述故事的游历小说来研究。旅行叙事是《镜花缘》的一大写作特点,书中描述了三次海外游历。作为生活在清朝乾嘉时期的文人代表,李汝珍博学多识、通晓古今,精通音韵和围棋,然而他满腹治世之道却无从施展,仅在板浦(今江苏连云港)捐了一个盐官的微职。正是在这样不得志的境遇下,李汝珍倾尽心力,用笔墨描绘了一个如梦如幻的镜花世界。“游”是贯穿《镜花缘》的主脉,小说通过旅行故事的书写方式,呈现主人公在海外各国的游历中找寻着自己的精神皈依的过程。
一、游于幻境,书写人生—《镜花缘》的旅行叙事特点
旅行故事是游历小说的主体,李萌昀在《旅行故事:空间经验与文学表达》中,将旅行定义为旅行者“通过对日常空间的出离而获得的非日常的空间经验”,并进而提出一个典型的旅行故事需要包括三个要素:非日常空间、旅行者、故事。从旅行叙事的角度切入,《镜花缘》具有情节构思巧妙、叙事借异写实和思想深刻递进三大写作特点。
(一)千里埋线,构思巧妙的情节架构
《镜花缘》从旅行者、空间和故事角度呈现了三次不同的海外游历,分别是:小说第八回至第四十回中,唐敖、林之洋和多九公等人maAJArr4FayzmVAhY2YMnEfhgsN9K3Vz2eXMlpEMWX0=历时五百四十天,途经四十多个国家,以唐敖隐居仙岛为终(第一次);小说第四十三回至第五十四回中,唐小山在林之洋、多九公、林婉如、阴若花等人陪伴下的寻父之旅,历时一年后同返岭南(第二次);小说第九十四回至第九十五回中,唐闺臣(原名:唐小山)在颜紫绡、林之洋等人陪伴下的再次寻父之旅,以两位女仙归隐,林之洋独返岭南为结(第三次)。观览全书,虽然书的前后两部分略显分节,但瑕不掩瑜,既有古典小说埋线千里的巧妙结构,又有独树一帜的“游戏”旨趣。作者在几次游历的书写中,对途经国家的详略安排、见闻侧重、奇人逸事等,无不进行了精心设计,以“仙界—人间—仙界”“归隐—寻父—重聚”两条主脉络构建了“李汝珍”式的旅行故事。
“在旅行故事诸要素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旅行者。无论空间还是故事,都必须与旅行者建立联系,方能在小说中产生意义。”(李萌昀《旅行故事:空间经验与文学表达》)《镜花缘》三次游历中的旅行者随故事情节而异,林之洋作为经验丰富且从事海船生意的“商人”参与了三次旅行,多九公作为一位年长智者参与了前两次出行,而唐敖与唐小山父女两人分别是第一次和第二、三次出游的旅行发起者。首先,唐敖出行的缘由是科考不公遂有弃绝红尘之意。从书中描绘来看,唐敖此旅是一次寻觅和救赎之旅,途中历经波折,沿途搭救数位被贬谪人间的百花仙子,并以归隐小蓬莱告终。从小说叙事的角度分析,唐敖之行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埋下伏笔,引出唐小山的游历;二是完成梦境所托。第二次游历以唐小山为旅行发起者,主要同行者除了林之洋和多九公等人,增加了林婉如和阴若花两位才女。同时,小说的叙述视角从奇人异邦转为由唐小山遇险获救、泣红亭抄记碑文、众仙姑施救等几个主要情节串联而成,虽然篇幅不及首次游历的二分之一,但起承转合的作用不可小觑,既承接寻父主题,又为下文的百位花仙中榜相聚进行了铺垫。小说结尾处第三次出游的旅行者为唐闺臣、颜紫绡和林之洋一家,游历的过程仅用一段不足百字的叙述交代,最后以两位女仙归隐结束,自此,三次海外游历告一段落。
综上可见,李汝珍在《镜花缘》三次游历写作中,极力渲染旅行者的不同身份和出行缘由,通过旅行者的见闻和感受,千里埋线的情节构思,推动小说主体叙事的发展,突出主题思想,为读者构建了一个集神话、漫游、寻道、修仙等为一体的“镜花”世界。
(二)借异写实,时空位移的写作技巧
《镜花缘》中着重叙述了三次海外游历,作者从陌生化的空间构图出发,以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诙谐细腻的笔墨,创造了海外诸国怪诞离奇的“非日常空间”景象。无论从时间叙事,还是空间叙事的角度来看,虚实相间的转换、现实社会的影绰,无不在作者书写的三次旅行中自洽表达。
首先,从时间叙事论之,《镜花缘》的故事跨越千年,从“武周时期”到“圣朝太平之世”,时间表达有条不紊,顺叙、插叙、倒叙和平叙交替使用,从而构成了一个连贯细密、脉络清晰的故事线索。平行于小说的主体叙事时间,开篇前两回仙界“蟠桃盛会”和“女仙斗棋”似是架空于人间的时间运转体系之外,本是两条互无关联的时间线索,但仙界“女仙斗棋”恰与人界“天星心月狐”下凡的武后下令百花齐开时间相重合,由此构成了虚实结合的时间叙事,将天上人间的人物关系、情节发展在分与合的时间叙事中铺叙纤悉、遥相呼应。作者看似随意的时间设置,实则冲破自然时空的束缚,体现文学虚构的超越,可谓“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文赋》)。
再者,以空间叙事观之,《镜花缘》继承和发展了《山海经》的神话精髓,通过三次旅行勾勒了四十多个异域风情的海外国邦。彼时的中国,文人心目中“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观念根深蒂固,加之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知之甚少。正因如此,当唐敖一行游历海外各国,体会各地风土人情时,多因其“天朝人氏”的身份备受尊崇,如在君子国偶遇吴姓兄弟,当得知来者身份时,吴之祥躬身道:“原来贵邦天朝!小子向闻天朝乃圣人之国,二位大贤荣列胶庠,为天朝清贵,今得幸遇,尤其难得。”不仅如此,由于与生俱来的“天朝基因”,导致了多九公和唐敖在黑齿国被两位女子以才论道后的“螳臂当车,自不量力”的尴尬境遇。诸如此类,数不胜数。在作者以“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先进文化和技术”的视角下,造就了巫咸国传播养蚕技术的才女薛蘅香,以及女儿国揭榜成功治理河道的唐敖,多九公博学多才、通晓医术,沿途救治病患,体现了东方大国的博大胸襟。
配合旅行者和故事情节,小说在时空叙事过程中借异写实、丝丝入扣,看似真切,实则虚幻,就像作者对靖人国的描述:“到了城郭,城门甚矮,弯腰而进,里面街市极窄,竟难并行……满口说的都是相反的话,诡诈异常。”与之相反,在描述“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度时,作者则不吝赞美之词,如对“君子国”的描述:“不多时,到了门前。只见两扇柴扉,周围篱墙,上面盘着许多青藤薜荔;门前一道池塘,塘内俱是菱莲。”虽是作者艺术创作出的虚幻国度,但空间景物描写细腻真实,如身临其中。真实与虚幻交替、时间与空间位移构成了《镜花缘》的时空叙事。作为旅行发起者的唐敖、唐小山,主动探索未知的空间和经历,从而实现对自我人生的超越,这蕴含着李汝珍的期待视野,也是其人生观和创作观的艺术表达。
(三)精神皈依,层层递进的思想表达
千百年来,“游历”似乎成为中国文人墨客们历劫后向内寻求精神皈依、向外探索治国之道的途径之一,无论是战国时期屈原的《远游》,还是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无不表达了作者远离尘世喧嚣、找寻心灵归所的愿望。悲时俗,离人群,而后遁逸,这正是《镜花缘》中唐敖、唐小山父女两人的游历思维模式。
作者笔下的唐敖在经历仕途挫败后,在充满未知和期待视野的旅行途中亲临了好让不争的君子国,也目睹了鄙陋不堪的无肠国等,最终隐居仙山,不问世事,实现了道家“虚无主义”的思想蜕变。唐小山的寻父之旅,屡屡遇难但都能化险为夷,小蓬莱泣红亭的百位才女榜,途中陆续集结的女仙,恰是作者要赋予她此行的意义,唐小山由此从一位民间孝女逐步蜕变为女仙,在其中榜、寻父和集结众仙的过程中,逐步履行其作为百花之首的职责,拥有了更为强大的责任感和大局意识,体现了作者平等的女性观。胡适曾说“《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镜花缘〉的引论》),如今看来,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李汝珍对于女性地位、女性生存状态是极为关注的,他用笔墨建构的百位花仙的“历劫—归仙”经历、极尽想象勾勒的“女儿国”等,表达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深度思考。
由此,《镜花缘》的三次海外游历书写,从旅行者的视角叙事,通过时空位移、虚实相生的叙事方式,抽丝剥茧、层层递进地表达了旅行者的思想蜕变和精神归途,唐敖父女最终都达到了知行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正如作者篇首所言:“不惟金玉其质,亦且冰雪为心……常有为常,变有为变。”一部《镜花缘》,写尽了天上人间。
二、镜花水月,与时俱进—《镜花缘》旅行叙事的现实意义
《镜花缘》作为我国古代文人小说的代表作,继承了《山海经》的神话精髓,发扬了“游记文学”的写作特点,融合作者的博学底蕴和游戏旨趣,可称为一部旅行叙事的巅峰之作。除小说的上述叙事特点外,其审美、空间和意识形态的旅行视角,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镜花缘》的旅行审美视角在作者的笔下淋漓尽致地呈现,四十多个海外国家的风土人情、景观意趣无不从旅行者的视角展开,丰富而深刻,对于现当代写作有很好的启迪作用。着眼当下,旅行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旅行审美视角不断丰富,“人在旅途”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在旅行书写中记录见闻、褒贬时事、抒发情感、畅想未来。现代旅行书写不仅延续了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对于旅行叙事的反复吟咏,还融入了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带来的审美视角的拓展,必将推动小说美学之独特范式的探索与实践。只要人在路上,就有无限文学创作的可能。
其次,《镜花缘》的空间视角丰富而立体,最具现实意义的是《山海经》的继承与创新,为古代中国的浪漫神话注入了一丝活力。随着时代的发展,旅行空间已不仅局限于地球上的某个国家或地区,星际探索一次次刷新着人类的认知,神话与想象本是一鸟之羽翼。从《镜花缘》的文人之旅到今天的太空之旅,不变的是人们亘古的找寻,正如《流浪地球》中的那句:“人类的勇气和坚毅必将被镌刻在星空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讲,救赎和探索的流浪之旅,相对于寻道和修心的镜花之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既是对现实问题的揭露,也是对未来命运的深度思考和探索,在空间架构上延续了《镜花缘》的特点,在时空交错中启发人们关注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最后,《镜花缘》的意识形态视角深刻且敏锐。唐敖虽抱着远离世俗的想法开启海外游历,但在旅途中极为关注各地的风俗民情,细心观察和剖析社会问题,在“出世”“入世”间徘徊取舍,最终选择归隐。唐小山既有古代女子善良聪慧、重孝守义的优良品德,又有博学多才、知人善用的独特才能,还兼具现代女性独立自信、审时度势的眼界胸怀,是作者为人称道的“女性”观和先进民主思想的体现。李汝珍在《镜花缘》中不惜篇幅展现女子们的学识才艺,让女性的美丽与智慧大放异彩,不仅在当时的文学描写中是超前的,对于现代旅行叙事作品的女性形象塑造和书写也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作用,启发读者审视和探寻古今女性的命运与情感生活的异同。
综上所述,从旅行叙事的角度来细观《镜花缘》这部经典著作,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李汝珍满怀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思考,以文为戏,成就了这部至今仍被海内外无数人追捧和借鉴的小说。“女汉学家费施曼称赞《镜花缘》是一部‘熔幻想小说、历史小说、讽刺小说和游记小说于一炉的杰作’。”(徐永斌《话说李汝珍》)书中的旅行叙事既延续了传统游记文学的特点,又影射了社会现实,构思巧妙的情节架构、虚实相生的写作特点、层层递进的思想表达使得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情感丰富细腻,丰富立体的旅行视角对于当今的旅行书写仍有借鉴作用。此外,李汝珍进步的民主思想、平等的女性意识隐含其中,既能还原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可启发读者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和思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镜花本空相,悟彻心无疑。”(孙吉昌《绘图镜花缘题词》)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镜花缘》的旅行故事还会沉淀出更多珍贵的文学魅力,它将继续承载着作者的涉笔旨趣不断发光,耀眼于文学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