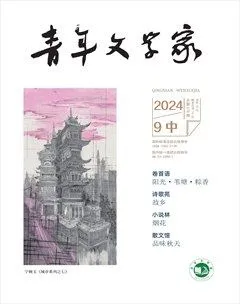浅析梁启超《桃花扇》评注中的戏剧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西方文化强势进入古老东方文化的地盘,二者发生激烈的碰撞。这场文化之争的实质是一场关乎政治与制度的较量。当看到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强行敲开中国闭锁的大门时,知识分子一方面痛心疾首,另一方面也在积极进行现实性的反思。在西方军事强权之下,其文化自然处于一种制高点,使得古老的东方文化在它的面前显得底气不足。在此背景之下,“师夷长技”自然成为一种摆脱落后的手段,制度与军事方面如此,文化方面亦如此。戊戌变法是梁启超从上至下进行强国的一次尝试。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正式宣告资产阶级改良派从上至下改革理想的失败。流亡期间,梁启超开始把变革的视角转向文化领域,从下至上对国民进行思想上的教化。梁启超试图取法西方文化,进而变革本土文化,启迪民智,最终目的仍然是鼓吹变法。基于此,梁启超率先推动了小说界革命、戏曲改革等一系列文化方面的运动。
在戏曲改革领域,梁启超所做不多,却有开路之功。清末民初,戏曲备受民众推崇,上到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皆是茶楼座上客。尤其是京剧,“民国”初年,四大须生和四大名旦在戏曲舞台上争奇斗艳,佳作频出。因此,京剧拥有广大的受众群体。在内外环境的推动之下,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逐渐走向艺术的成熟。戏曲表演的内容与方式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舞台上的表演大多是帝王将相与才子佳人,宣扬的不外乎是因果轮回、忠义节孝等伦理道德。因此,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发动文化运动时,必然不会忽略戏曲这个封建文化的栖息地。可以说,梁启超是20世纪初对中国古典戏曲进行第一度思考的重要人物。戏曲自古就被文人斥为“小道”,但梁启超率先提出“体裁论”,戏曲之“优于他体”,他反对厚古薄今,从整体上肯定了戏曲在历史和社会上的地位。他本人亦亲自进行戏曲创作,把古老的戏曲放在现代视野下进行审视,对戏曲进行现代化的编写,以此来适应时代的新变。梁启超一生著述等身,对于戏曲的论述散见于他的文章之中,并不成体系;但他对孔尚任《桃花扇》的评注中,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戏剧观仍然清晰可见。
首先,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
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往往不可避免涉及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即如何处理作家主观表现同客观事实之间的关系。孔尚任的《桃花扇》在中国古典戏剧史上被当成尊崇历史的典范。《桃花扇》的故事取材于南明小朝廷抗清的历史真实事件,侯方域同李香君的爱情穿插其间,剧作家的目的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因此,《桃花扇》中的人和事大多是历史上实有其人其事。在处理史实材料时,孔尚任标榜其主观上是遵从客观发生的历史事实的。但是作为一部历史剧,《桃花扇》不是真正的历史记录,它是一部戏曲艺术作品,其创作意图是以此寄托孔尚任内心积郁的兴亡之感。所以,孔尚任才会说,在“儿女钟情,宾客解嘲”(《桃花扇·凡例》)之中稍有点染,而这种点染的艺术手法正是历史剧区别于客观历史的根本所在,也是艺术作品的魅力之源。
梁启超曾说他“生平不喜观剧”,但他却偏爱《桃花扇》,并赞它是一部“哭声泪痕”之书。梁启超《桃花扇》的评注工作完成于1925年,他的评注没有字词典故的寻常注解,而是偏重于史实的考据,从历史的角度对《桃花扇》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评注,这是一种重源流、重考辩的点评方式。在梁启超的考据之下,《桃花扇》中的艺术真实却并非如孔尚任所说的那样符合历史真实。比如,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是崇祯十六年(1643),侯方域侨寓金陵;但在历史中,侯方域居住在金陵游会时是在崇祯十二年(1639),崇祯十六年侯方域正被叛将刘超所俘。对于南明抗清将领史可法的结局,孔尚任的处理是以史可法无力回天而投江自尽来收束。这种悲剧人物命运的艺术化处理,使得《桃花扇》的结尾充满了悲壮的意味。但梁启超却认为,孔尚任采用的结局乃民间俗说,不可信,“此种与历史事实太违反之记载,终不可为训”(梁启超《小说丛话》)。在评注本中,梁启超多次指出孔尚任与史实记载有出入的地方,尤其是对一些积极抗清最终以死明节的英雄的结局的处理上。比如,孔尚任笔下的杨龙友,清军南下时他仓皇逃回老家贵阳,但梁启超却为杨龙友抱不平:“乃不录其死节事,而诬以弃官潜逃,不可解。”(《桃花扇注》)
在梁启超的诸多评论中,他以真实的历史为尺度,严谨地考量孔尚任对史料的裁剪运用,虽有不满但并无苛责,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孔尚任是剧作家,不是史学家;《桃花扇》是一部历史剧,不是真实的历史。在戏剧中,梁启超承认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存在的矛盾,并大加赞扬了孔尚任对历史的艺术化处理。《桃花扇注》中,他认为,孔尚任“专好把历史上实人实事,加以点染穿插,令人解颐。这是他一家的作风,特长的技术。这种技术在《小忽雷》着手尝试,到《桃花扇》便完全成熟”。这里所谓的点染穿插便是历史的艺术化处理。孔尚任《桃花扇·凡例》中也曾说:“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可见,梁启超对于《桃花扇》中人物故事的虚构和嫁接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在《桃花扇》评注中,梁启超对历史作品的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观点看似有所矛盾,实则他持有的是一种严谨审慎而又不乏灵活的艺术观点。他认为历史作品涉及真人真事,尤其对于一些历史上有气节的名士的命运的歪曲改写是不能赞同的;但作为文学艺术,却要度取其“意”,也就是要考虑剧作家创作的内在意旨,为剧本文学服务,哪怕为此适当改变历史人事,也在所不惜;读历史剧,务必不能刻舟求剑,将文学完全等同于历史。
其次,重视戏剧的社会功能。
清末易代之际,清政府对民间思想的约束渐趋式微,散文、诗歌等所谓正统文学的地位受到冲击,代之在民间兴起的是历来被斥为“小道”的小说、戏剧等文学艺术。这些艺术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容纳各种新思想,同时以一种亲民的姿态娱乐大众、服务大众。因此,小说和戏剧拥有广大的受众群体,而知识分子自然不会忽视这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一文,指出社会的变革、民智的开启需要借助戏曲和小说,“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
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这一篇文章之中,梁启超把戏曲作品包含在小说之中,他认为戏曲具有“熏、浸、刺、提”等多方面的功能,正所谓“借雕虫之小技,寓遒铎之微言”(梁启超《新罗马》)。在戏曲之中,梁启超期望能传达出他的政治理想,通过戏曲强大的感染力,能够实现启迪民智的社会效果。梁启超甚至亲自创作戏曲作品,其目的就是以大众化的戏曲为载体,宣传理想,教化百姓。他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都是旧小说戏曲的不良内容造成的,所以梁启超十分看重戏曲的思想和内容。
在诸多古典戏曲作品中,梁启超单单选择《桃花扇》作注可谓大有深意。这不仅是因为《桃花扇》高超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桃花扇》中所承载的国家兴亡的深刻主题。可以说,这个主题同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深深契合。20世纪初,中国社会积贫积弱,面对西方列强的鲸吞蚕食,身为中国人的梁启超对社会现实感到十分痛心,一方面是底层国人的麻木,一方面是国家上层的愚昧贪婪。对此,他认为必须唤起中国人的反抗意识,才能促成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而在《桃花扇》中,梁启超找到了这种民族精神的共鸣。孔尚任把历史兴亡之感寄托在戏剧之中,他对戏曲的社会政治教化功能认识透彻。孔尚任认为戏曲不仅能够“警世易俗”,还可以寓教于乐,以富于艺术魅力的表演形式,为社会各阶级喜闻乐见,“下自屠爨贩卒妪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硕学”(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皆能受此感染。因此,民众在观看戏曲时能够在无形之中得到教化。可以说,梁启超对戏剧功能的认识,同孔尚任对戏剧的看法不谋而合。在二人看来,戏剧不再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微言,而是承担起启蒙思想、教化民众的重要职责。
梁启超《桃花扇》评注中对戏曲的现代化变革不是体现在戏曲内容方面,而是对戏曲体制方面的革新。孔尚任《桃花扇》的体制是按照古典传奇体制进行编写上演,按照生、旦等角色进行扮演,以曲牌联套的体制进行演唱。《桃花扇》一共四十出,每一出即是故事发展的段落,同时也是音乐发展的段落。但梁启超在《桃花扇》评注中,不仅仅对其原文进行评点,而且在戏剧开头大胆地改变了中国戏曲原有的按“出”来结构全篇的方式。他借鉴西方戏剧的结构模式,以“幕”的形式在每一出中进行新的段落的划分,一幕就是一个相同的时间和地点,并且还在每一幕中详细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以及表演所需要的道具。同时,他在剧本中取消了角色的划分,直接按照西方戏剧以名字首字来代替角色。比如,在第一出《听稗》中,梁启超把原来“一出”划分为“三幕”,强化了舞台表演中时间、地点以及人物的转换。这种改变可以使读者和演出者更清楚地注意到时间和空间的改变,增强了戏曲的写实性。
西方戏剧在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此后春柳社、春阳社、进化团等各大戏剧团体纷纷成立,为西方戏剧的中国化推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早期这种新的戏剧样式还没有被人们所熟知,中国的戏剧家们囫囵吞枣地吸收这种戏剧的养分,急迫地想要为己所用。由于对西方戏剧的特征不甚了解,早期戏剧家常常把话剧同戏曲糅合在一起进行演出。这种生搬硬套的结合,在今天看来显得不伦不类,但这种结合却是中国话剧初创期的一种勇敢尝试。也正是在话剧同戏曲碰撞结合的过程中,中国的戏剧家们才逐渐厘清话剧和戏曲是两种各具特色的戏剧艺术,二者都有其艺术的独立性,根本没有所谓的先进和落后之分,如果有,那也是思想内容方面上的暂时性落后,而非艺术表现手法上的优劣。总而言之,对戏曲的改造梁启超当数第一。虽然这种改造在某些程度上是对戏曲艺术独特性的破坏,但从客观角度出发,梁启超是打破古典戏曲僵化视野的第一人,他开启了对中国古典戏曲进行现代化的第一度思考,他把中国古典戏剧同西方戏剧结合起来,试图向大众介绍一种新的戏剧的样式,并竭力地发掘一种新的思想宣传的工具。梁启超的这种尝试同他的戏剧改良运动密切相关,而戏剧改良运动就是同当时整个时代的改革创新、向西方学习的理念遥相呼应,其实质就是古老的戏曲如何救亡图存的现实问题,如何利用拥有广大受众的戏曲进行思想启蒙。
在《桃花扇》评注中,梁启超在原来每一出戏的开头都加上一些文字,或是诗词,或是一出中的关键韵白与唱词。梁启超曾言,《桃花扇》的文辞之美不及孔尚任和朋友合作的《小忽雷》,因此在每一出的开头加上这些韵文,可以看出梁启超对提升《桃花扇》文辞之美的意图。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这种增加文采的方式虽然有助于读者对《桃花扇》剧作意图进行更深刻的理解,但是在实际的演出过程之中,这种方式可实施性并不太大。由此得知,在梁启超的内心深处,对戏剧的理解还是古典文人式的解读方式,注重案头阅读而非“奏之场上”。
在《小说丛话》中,梁启超曾盛赞《桃花扇》“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华丽”“寄托之遥深”。对于《桃花扇》,梁启超倾注的不仅是对艺术的探索热情,更多的是对侯李二人所处时代的感同身受。梁启超因《桃花扇》艺术之精美而对其倾心,更因其“寄托之遥深”故而心生戚戚之感。虽然梁启超的戏剧观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戏剧观,但在特殊时期,梁启超所流露出的戏剧观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此外,他对《桃花扇》所做的研究,为后世学者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可以说,梁启超的《桃花扇》评注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戏剧改革更是有首开风气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