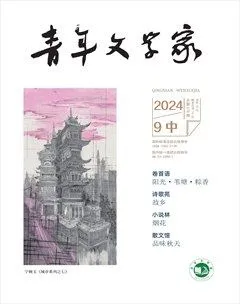黄连树下弹琴
“黄连树下弹琴,苦中取乐”,小时候,母亲时常这样教育我。苦生苦长,乐观坚强,已成为深刻记忆,成为温馨回忆!
寻觅野菜
盼望着,盼望着,春天来了!我们这些缺衣少食的山孩子,终于可以不用缩手缩脚,身子蜷成树疙瘩,手肿成小馒头,脸皴成桦树皮,终于可以像南来的燕子,漫山遍野地翻飞,寻觅各种野菜,帮衬父母度过青黄不接的日子。
听,“三月三儿,抽毛芽儿,结绳绳儿,卷饼饼儿,给你嫂子当枕头儿”,山间小道上到处飞扬着我们这帮无邪儿童的欢声笑语,尽管我们脸上满是饥饿的菜色!
看,荠菜、灰灰菜、野韭菜、野小蒜……这些隐没在杂草丛中的各种山野菜都是发光体,引得一群群叔侄、姨甥们一阵哄抢,它们都是各家能够填饱干瘪胃囊的稀罕物啊!
高小毕业的母亲,要比周围的亲友们机智,好吃的熟悉的野菜太少,难填饱肚皮,她就教我顺着山涧沟渠寻觅饭蒿和桑叶。
怕我误采饭蒿,食后中毒,她就教我学会一看二闻。
她说,饭蒿的背面是乳白色的,其他野蒿的背面是青黑色的;饭蒿有一股清香味,野蒿是水草味的。桑叶好辨认,尽量采嫩叶就行。
饭蒿采回来后,用开水一焯,再用凉水漂洗几遍,切碎加盐搅一点儿玉米面,煮成稀糊糊,味道不比荠菜糊差。
桑叶洗净、焯水、切碎,放进开水锅,倒入一点儿石磨生黄豆浆,煮熟,做成懒豆腐,吃了很耐饿。现在大餐馆里有时也有懒豆腐,用精美蔬菜做成,可我再也吃不出童年的清香味道了。
长大后,不免感叹:“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
助力抢夏
夏天,天高云也长。
“豌豆算割,豌豆算割……”“麦黄快割,麦黄快割……”房前房后布谷鸟清脆的催叫声,催醒我们准备帮大人“抢夏”了。
父母天不亮就下地了,我和弟弟赶紧起来,招呼妹妹们起床做事。扫地、放鸡、喂猪、做饭、送饭,这些必修课,必须赶在上午八点上学前完成;中午父母不歇晌,我们姊妹五个陆续从学校赶回家,烧茶、做饭,还要给父母送到地头,还要喂猪喂鸡;下午放学后,时间长,活路更多。第二天的口粮要是没有了,来不及背粮到小磨坊加工,我们还得自己用小石磨推“麦辣子”(小麦磨碎,不去皮、不去麸),还得削好一大盆子的洋芋(细粮少,全靠掺洋芋充饥),还得上山打猪草,还得洗父母满是汗渍的脏衣服……
我们家人多活儿多,忙不过来怎么办?抱团呀!我常常邀请堂弟堂妹们把削洋芋皮之类的活儿都拿到我家来做。我们先帮她们,她们再帮我们,比着干,赛着做,效率自然高多了。说实话,还是占了堂弟堂妹不少便宜,毕竟他们家务活儿的总量少些。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当我读到白居易的《观刈麦》时,情不自禁地改为:“童稚荷箪食、携壶浆,相随饷田去,父母在抢夏!”
爬树采药
别看我们年纪小,却多是上树的高手。深秋了,落尽了叶子的树梢上还有几个诱人的烘柿子。机灵的三妹不用竹竿,而是脱掉鞋子,往双手掌上吐些唾沫,身子一纵,噌噌几下就爬到树顶上,任凭树枝像秋千一样荡来荡去,她用双脚紧紧勾住树枝,双手轻盈地摘下柿子放在背上的小背篓里,刺溜刺溜地溜下地来。我们惊叫着,欢呼着,如一群嘻嘻哈哈的小画眉。
我们还是采药的“犟人”。父母为养家糊口,“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贫瘠的山地上耕种。想上学,只能自己挣学费!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在各个山梁上采药。即使一天只能采到一点点柴胡、连翘、五味子,能挖到一两斤黄姜,我们也不会放弃,我们相信愚公移山,我们相信人定胜天。
上山骑牛
隆冬时节,我们一边上学,一边放牛,一边割牛草,一边捡牛粪。牛儿是我们最好的玩伴,到了平旷一些的山顶,吃饱了的它们便高兴地弓下前腿,让我们依次爬上牛背,它们甩开尾巴驮着我们来来回回在山顶游走。郭老曾在《天上的街市》中畅想:“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敢情是受了这一启发?
四季更迭,时节如流,我们就这样度过了有忧有虑、苦乐相伴的童年。奇怪,再回首穷困童年散落在树林草丛间的那些小碎片,不觉辛酸,不觉愁苦。原来“愁”是“离人心上秋”!那时的我们,祖辈健在,父母年轻,姊妹无邪,虽物质贫困,但亲情丰厚,关爱富足!最最关键的是,母亲教会我们:即使坐在黄连树下,也要坚持弹琴唱歌,苦中取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