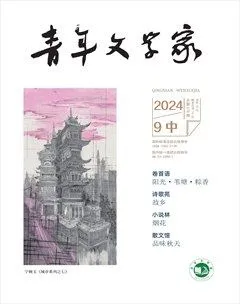一个人走过村庄

偌大的村庄,也不过一人。
一个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就像一闪而过的影子,或者被剪辑而零碎的梦境。当村子里有人想起他,才突然发现他已经消失多年,好像他的存在若有若无,缥缈得像早晨的雾。其实,一个人的生命也是漫长的。在村庄里,一个人的历程高度概括了一群人的生活内容:从出生到死亡,几乎没有人能走出村庄,有时冲撞了与邻村的边界,打一场不疼不痒的仗,还是要把头缩回来,依旧在村子里转悠,陪伴一个人的,终究是他长长短短的影子。
然而,村庄是不变的。即使土坯房换成了砖瓦房,年轻人长成了中年人、老年人,村庄依旧是千年以前的风貌。就像一件没有出土的文物,蓬头垢面地藏在岁月的灰尘背后。它沉默在南来北往的风中,送走一茬又一茬人,收藏了他们的欢笑和泪水,爱情和苦难,把它们埋在自己的怀里,收藏在三尺黄土之下。村庄延续着日子,这里的树木似乎永远不会长高,通向村外的道路永远不会缩短,村子的年龄刻在同一道皱纹上,爬不出皱纹一样深的沟壑。数百年来,村庄做着同一个梦。
其实,村庄也在新陈代谢,似乎每年都要送走几个人。就在昨天,爱着急易发怒的二大爷走了。他是一位残疾军人,一条胳膊在战争中被打掉了,空着一只袖子在街上晃。他是村里管治安的委员,一年四季就穿一身绿衣裳,戴一顶绿帽子,即使被风雪漂白了也不改初衷。如果说村里有一点儿声音,那就是他发怒的吼声。晚上,谁家忘了关门,他扯开嗓子告诫;偶尔来个货郎,他也皱着眉头大声询问;有个别外村后生偷溜进村来会女朋友,也会被他拦住,厉声地审问。他那晃晃悠悠的袖子,从村东飘到村西,像一个幽灵,驱除任何一丝扰乱村庄的风和影子。几十年了,村里人习惯了他的吼声,习惯了他的存在。如今,他也走了。虽然村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丧礼,虽然每个人都为他流下了眼泪,但由此而产生的涟漪很快被时间抹平,村子也变得更加沉寂。日子照样从墙头爬过,星光也如流水一般,安抚着每个夜晚。由村庄而搭建的舞台,把生与死演绎得波澜壮阔而又稀松平常。
第二天清晨,当树梢淹没在晨曦的时候,村东的一家大门开了一条缝,一个人走出来。他笑了笑,他的笑似曾相识;他打了个哈欠,那慢吞吞的声音,轻抚亘古不变的节奏,缓缓地随风飘走,落在村庄的某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