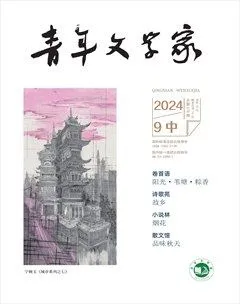我的创作人生
明年这个时候,我能不能出去旅行或者回老家将息,我并不知道。如果把一个个无奈的人生都归于客观,说是一个害人的病菌阻挡了彼此前行的道路,那只能说我们地球人已经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而我的生命也启动了衰退的旅程。
枣树开花结果不久,长长久久从泥地里睡醒过来的蝉儿动用随身的乐器,在午后不停地嘶鸣,尽最大能量释放压抑的情绪。马枣与团枣,一个形体苗条,一个形体圆粗,就像年轻男女;成熟后,一个酸一个甜,就像一对厮守多年的夫妻,经常对峙,却常常留有后路。
小的时候,哪儿会区分什么雄蝉和雌蝉,抓到一个算一个。用棉线缚住它们的细手细脚后,它们再想振翅欲飞,恐怕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了。小孩子玩心十足,自然没想到这些到手的小生命是多么来之不易。等从书本中得知,那些会鸣能鸣的都是雄蝉,而雌蝉的乐器构造不完全,根本发不出声音时,我已快速地长大了。在了解了蝉的“悲凉一生”后,我如鸣蝉一样,尽做些在闷热的季节里极其喧嚣的事。
其实,人生就是对时光的一段段反射。孩提时,你在老家的泥地里逶迤爬行,从大人的脚印中多多少少还能找到痕迹。等渐渐地长大了,告别了村口蜿蜒的小溪,走出了重重大山,爬过道道危岭,目睹了各种车辆行驶后留下的辙痕,才知道一次次负重是人生一幕幕重头戏,而父亲的独轮车只能承载与他体重两三倍的重量,只能承载儿孙的少年。少年的记忆里有无数梦幻一般的故事,他已经没有精力牵挂了。最后,他以完全躺倒的方式完成所有在人世间的游戏,虽有种种不舍,祈望晚辈走好山外的每一步却是由衷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
要说人生的内容,不外乎是堪称高贵的思想与普通的实践。就作者而言,许多许多的时间与光阴都融入了一串串文字当中。说是完成日更也好,说是倾注文学创作实践也罢,除了天赋外,恐怕更多是磨炼,包括思想上和艺术形式上的继承与创新。
不管你怎么谈论文学,如何勇敢地在文学道路上行走与奔跑,文学女神总是远远地站在你的前方,笑盈盈地向你招手,而等你接近她想与她牵手的时候,她又马上跳开,又站在前面向你发出新的邀请。学无止境,写作也如此。在清醒地知道了这一情况后,面对自己撰写出来的作品,只能说与过去的文章相比有进步却不能轻言有多大深耕,只能说在写作手段上有所精进却不能轻言有多么纯熟。因此,我本人最多是一个业余级的写手,说自己的人生是写作的人生,只是站在老家的樟下山上把自己的身体略微抬高而已,对别人、对这个世界而言,并没有什么可参考、可借鉴的实际意义。
如此说,一点儿也没有自谦的意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局限性。等你歇下双脚,自鸣得意的时候,人家已整理好所有道具,又踏步向前了;等你把习作本陆续上交的时候,人家的创作已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我想,文学创作既是一场无人在现场“加油”的比赛,也是一场并不存在敌我双方你死我活意义上的竞争,更多是学识上的比赛,才艺上的竞争。而在学识与才艺的背后是文学思想的沉淀,艺术视野的扩大。天有多大,心要有多大,一个人的视野大小常常决定一个作品的艺术生命。反之亦然,一个作品的背后可以准确地看到一个作者有别于他人的思想学识和艺术才能。
沉淀的目的是让人创新,视野的扩大是促人清醒。
一个来自农村的懵懂少年,在求学和写作道路上不断地奔跑,毫不顾忌身边无数个沟沟坎坎和曲曲折折,想起来都能令自己发笑一阵子。这是不是意味着自己日渐觉悟,知道其中的深浅,也象征着从此以后必有大的作为?我还真的说不清楚。
自二十一世纪伊始,我已经走过二十余年了,其中在简书平台上又走过了三年多的时间,按照目前的态势,估计还能行走几个若干年。真到了自己不想写的时候,再来回望吧,再来总结吧。但愿在那个生机勃发的年代,还有大文学的存在,还有全民文学热的风潮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