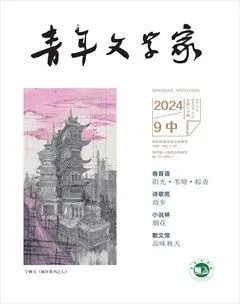艰苦岁月探亲记
1961年夏,学校刚放暑假,我们立马准备回无锡农村老家探亲。此前收到来信,说我舅舅去世了,舅舅只有三十岁左右,是个勤快而又本分的人,实在有点儿出人意料。
在把口粮换成了全国通用粮票后,母亲就带着我们兄妹二人踏上了回乡的路。列车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奔驰,连绵八百公里的祁连山,一路伴随着我们前行。嘉峪关、酒泉、张掖、武威,一个个沉淀着辉煌历史、威名显赫的地方接连闪过……金戈铁马,漫漫黄沙,这里曾是汉朝大将霍去病击败匈奴、建功立业的古战场,也是唐朝高僧西天取经的磨难之路。当车行驶到河西走廊东端时,突然大雨滂沱,汹涌的洪水冲垮了路基,火车被迫在乌鞘岭上滞留了两天。这在以干旱著称的西北地区,实属罕见。
虽是盛夏,但因海拔高,又下着雨,周围雪山上的寒气侵袭而来,气温急剧下降。车上也不开暖气,我穿上了所有的衣裤,又裹着一条小棉被,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车上不但冷,还没有食物供应。出发时带的干粮已经吃完,停靠地点也买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我妹妹饿得哭闹起来,后来还是同车厢的一位乘客给了点儿吃的东西,她才安定下来。
到兰州后需要转车,一走出车站,映入眼帘的是成群的逃难农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要到何处去。我看到一个中年人在车站门口吃东西,有人蹲在他脚下,捡拾掉下来的碎渣子吃。那一幕,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到了河南郑州再次转车,我们去了郑州车站附近的小饭馆里吃饭。邻桌一位中年男子正在吃饭,旁边站立已久的小乞丐猛地把黑乎乎的手伸向他的碗中,抓了一把拼命往嘴里塞。被抢的人无奈地摇了摇头,并没有责怪他,把碗中剩余的食物都给了他,小乞丐算是遇上好人了。
通过多次转乘,跨越了千山万水,历经整整七天时间,我们终于从干旱荒凉的大西北回到了江南水乡无锡城。去前洲乡下,还需坐船前往。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航行,我们到达了前洲,接着又步行了五里多弯曲的小路,最终回到了思念已久的浮舟村老家。一走进家门,皮包骨头的姥姥颤颤巍巍地迎了上来,流着泪道:“哑巴已经走了(舅舅是个哑巴)…99436a810a61c3787f6ef0f04bf193766b275eecf21cafe6687611e734e177c0…”
看到姥姥家吃的糠饼,我出于好奇尝了一口,那感觉就像是在吃锯末!我立马全吐了出来,引起了旁人的讥笑。后来,听多人说过,当时只有饿得浮肿了的人,才能得到一点儿“清糠”。清糠是稻谷脱下来的第二层壳,也很难吃。为了填肚子,大伙儿到生产队地里,去偷割一种当作肥料的红花草吃。望着姥姥那骨瘦如柴的身子,母亲决定马上带她出去吃几天饱饭。那个时候到任何地方去吃饭都是要粮票的,幸好我们带着全国通用粮票,否则将寸步难行。
我们四人来到上海,住进了安东旅馆。为了省钱,我们基本上三餐都喝粥,偶尔也去吃一顿米饭,点两个最便宜的小菜,这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已算是很奢侈了!走进饭店,姥姥总是情不自禁地去拿别人吃剩的东西吃。在她眼里,剩饭剩菜就是美味佳肴,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我年龄虽小,但也懂得要面子,不能让别人看不起我们。我动员母亲一起说服了姥姥。吃了近三十天的饱饭,姥姥明显好转了许多,后又多活了十余年。
从上海回来后,我们又去探望了无锡城里的表姨,表姨正在喂鸡。看得出来,城市居民的生活比农村要好一些。表姨陪母亲出去买干粮,准备回西北时路上吃。剩下了我和同去的小表弟,表弟就去抓鸡食吃(菜叶拌麸皮)。而买回来的干粮,则被我们俩偷吃了一大半。表弟当时还年幼,现在应该不记得了。
过了1962年,经济开始慢慢好转,我们再回老家探亲,列车上的食品供应基本有了保障,沿途停靠地点也能买到吃的东西了。对于那段历史,七八十岁的人都记忆犹新,老农民更是刻骨铭心!
改革开放后,农民终于吃上了饱饭。就连现在家养的猫狗宠物,都比那时候的人吃得好多了。相信国家会一直和平稳定地向前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