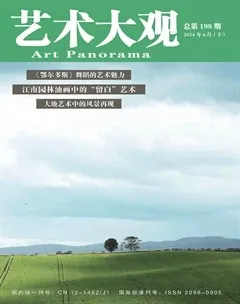生命的拼图
最近几个月,基本处于闭门不出的状态。焦头烂额地忙,加上身体不好,下了决心:哪儿都不去,谁都不见。因为即使勉强去了,见了,整个人也是形不散神散,对别人不礼貌。
从父母那里传来消息:一位父亲的老朋友要来。这位伯伯姓吴名长辉,是我们的同乡,父亲大学时代的好朋友,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去了香港,从此很少见面。这次他偕夫人回内地,先到上海,再回福建老家。心想:可惜我不能见了。
吴伯伯来了,不住宾馆,就住在家里。第二天,妈妈给我来电话,说:“他们想见你,你不能来吧?”我说:“不能。找个时间通一个电话好了。”
第三天,妈妈又来电话,说:“你吴伯伯还是想见你。他说当年他去香港的时候,你放了学赶来送他,但是没有赶上,他从车窗里看到你失望的样子,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忘记,所以很想见见你。”我愣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明天回家见他们。”那是真的,因为当时我确实在泉州读书,所以他没有记错。那真的发生过,而且被一个人在心里记了二十多年。所有闭门谢客的理由都融化了。
“打的”回了父母家,客人去浦东参观还没有回来。等了几个小时之后,见到了他们。吴伯伯的轮廓没有大变,只有头发和体态泄露了岁月的秘密。伯母不复我童年记忆中的天仙美女(我看过她的婚纱照),但是有着这个年纪的女人少有的单纯的笑容。吴伯伯看了我一会儿,说:“你没有变,如果在路上遇到,我会认出你。”我想:是不是他曾经想象过我们在街头的人流中偶然相遇?
提起当年的那一幕,吴伯伯说:“那时候,你在泉州北门读书,放学以后赶到华侨大厦门口送我,车已经开了,我看见你远远跑过来,看见车开了很失望,几乎要哭出来的样子。那个样子我一直记得,这么多年一直记得。”之所以记得,不仅仅因为当年的我是一个小小的孩子,也不仅因为我是他的好朋友的女儿——而是在一个离开家乡的人的心中,我的面容和对家乡的最后一瞥重叠在了一起。
而当年,我是那么重视那次分别,因为当时父亲不在泉州,不存在父亲命令我去送行的可能,是我自己要去送行,而且一定在上课时心神不定,下课之后一溜烟地跑到华侨大厦——就是骑自行车也要二十分钟的路程。在当年的我的心目中也许觉得会是永别,因为那时的香港,还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像月球一样遥远、陌生而难以到达。没有能够见上“最后”一面,我的失望和伤心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岁月已经把这一节抹去了。关于这个吴伯伯,我记得的,是我更小的时候,和父亲一起到他在石狮的家里做客。那里保留了当时全国少有的繁华热闹的自由集市,我自从出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那么丰富的蔬果,那么生猛的海鲜,记得摊贩们纷纷大声招呼吴伯伯,说自己的货好、新鲜。吴伯伯出手阔绰,根本不还价,买了许多鸡鸭鱼肉和海鲜,还有我从未见过的大芦柑。他的家是一幢石头的大楼房,今天想起来就是别墅,底层养着一条大狗,我很害怕,所以上了楼就不敢自己下来,吃过丰盛的午餐,当爸爸和吴伯伯聊天的时候,我就在楼上从一间房间走到另一间房间,手里不停地剥着芦柑。再后来,关于吴伯伯的记忆就是1994年我去香港,从爸爸那里要了他们的电话号码,打了几次,不论白天晚上都没有人接,就没有能见上。说起来才知道,那时他们去了美国女儿家。
我们一边吃着螃蟹,一边聊天,感觉似乎没有分别过那么多年。他说想看我写的书,我在家里找到了三本,都送给了他们。往扉页上题词的时候,心里既没有骄傲也没有自卑,因为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写作者最渴望的朴素的接纳。
回家的路上,我的心里还充满了重逢的温热。但是,那让他难忘的一幕,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在这以前,我一直觉得我的记性很好,而且很早就开始记事。现在看来,也许并不是这样。
生命是一幅拼图,由许多块小拼板组成。人总是想争取更多更好的拼板,好将自己的人生拼出美好的图案。但是在我们成长、奋斗的过程中,有一些拼板却被遗落了,有的散落在岁月的某个角落,谁都不能再到达的角落,永远无法回到我们生命的拼图上;有的握在了某一个故人的手里。没有他们手里的那块小拼板,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不完整的。寻找那些小拼板,然后放回至生命里应该的位置,让生命少一些空虚和遗憾,这也许就是重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