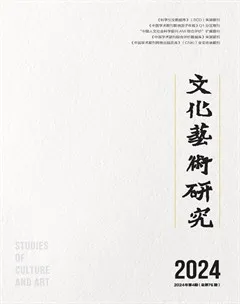另眼相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剧人眼中的话剧观众
摘要:新世纪以来,社会文化生态的急剧调整,使戏剧实践更趋向于迎合大众的感官享受、娱乐游戏等需求,导致戏剧文学边缘化,观众的精神结构随之呈现扁平化、单向度特征,深度审美与价值认知有所淡化。通过考察报刊中20 世纪30 至40 年代中国剧人对话剧观众的看法,可还原当时观众与戏剧的关系动态。其时,剧人普遍认同“无观众,不戏剧”的观点,观众观演的习惯、动机和方式也得到关注和探讨,呈现复杂性、多样性和发展性之特点。戏剧创作取向上,存在迎合或培育观众两类目标。而作为剧作家及戏剧教育家的熊佛西则提出综合策略,强调创作者应同时关注市场需求与艺术深度,以建立良性互动关系。这些历史观点及其生成语境的探讨对重新审视当代戏剧创排和演出管理提供了经验参照。
关键词:话剧观众;20 世纪中国;观众动机;观众素养;观众培育
中图分类号:J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24)04-0050-07
引 言
剧人,即从事戏剧创作与演出的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戏剧正处于转型期。剧人们在新剧(西方传入的话剧)发展浪潮中,积极探索与观众的关系及观众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报刊成为剧人们表达见解、探讨观众角色的核心媒介。
本文聚焦于这一阶段剧人对话剧观众的认知与评价,透过对报刊文献的深入挖掘,再现剧人眼中的观众身份、观演习惯及其对观众之态度,旨在通过分析当时剧人对观众的洞察,揭示在这一特殊历史阶段,观演关系的动态变化及戏剧生态在社会变迁中的内在逻辑。同时,针对“眼中”观众与实际观众的差异,以及代表性、典型性与普遍性、一般性之间的界限问题进行辨析,亦关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观众特征相对于前后时代的连贯性与革新性变化。
一、无观众,不戏剧:对观众身份的认知
在中国戏剧的发展历程中,观众身份始终与之紧密相连,形成了一种植根于群众的艺术生态观——无观众,不戏剧,即戏剧艺术的生命力源自观众并围绕着观众存在。这一理念起初反映在实际的戏剧运作与反响中,随着剧人们持续的理论提炼与艺术探索,观众地位逐渐被理论明晰化,并被提升至不可或缺的核心层面。
中国传统戏曲不论内容、形式,还是演出方式,都表现出亲民性和互动性。而话剧传入中国后,在早期便承袭了这种重视群众的传统,在戏剧结构和表现手段上效法传统戏曲,力图使其贴近大众审美情趣,使大众产生共鸣。例如,无论是进化团还是春柳社的演剧,都习惯于传奇体、章回体的编剧手法,即“开放式”结构,极少采用欧洲近代话剧“锁闭式”的倒叙方法,或“人像展览式”的散文化方法。同时,在结构上使用大量“插科打诨”和“背躬”等传统戏剧手法,以活跃剧场气氛,增强喜剧的讽刺效果,使演员和观众打成一片。这和近代欧洲剧场筑起假设的“第四堵墙”,致力于造成“生活幻觉”的原则完全不同。[1]
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实践的不断革新,中国剧人对观众地位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这反映在关于戏剧本体的论说中。他们广泛认同剧作家、演员、观众构成“三位一体”的关系。[2]戏剧教育家、剧作家陈瘦竹与熊佛西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从不同角度阐明了观众之于戏剧的重要性。
陈瘦竹在《观察》a 上发表的《戏剧与观众》明确指出,戏剧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剧本和演员,更需要戏剧从业者认识观众的心理,明白观众的需求。正如商人在出售商品前应了解顾客的需求一样,戏剧从业者需要在创作之初就考虑到观众的期望。[3]
熊佛西在《民国日报》b 发表的《观众与批判》一文进一步提出:“我是一个相信‘宁可无戏剧不可无观众’的人。无论哪位成功的戏剧家,是没有不重视观众的。”[4]这一立场强调了观众在戏剧生态系统中至关重要。他指出,即便像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这样的杰出戏剧家,也都高度重视观众的反馈和期待。这种对观众的深入了解并不是为了谄媚观众,而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他们的欣赏需求,使戏剧能够顺利地传达情感并引发共鸣效应。
熊佛西和陈瘦竹的观众说来源于不同的经验与理解。1923 年,熊佛西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受到戏剧教授布兰达·马修斯的指导,其戏剧理念亦受到马修斯的深刻影响。马修斯强调观众在戏剧中的重要性,曾在其著作《做戏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Playmaking)中以一个章节论述对萨塞戏剧观的赞同,他指出:“戏剧一词本带有观众的概念。我们无法构想一出没有观众的戏剧。”(The wordplay carries with it the idea of an audience. We cannot conceive of a play without an audience.)c
陈瘦竹的观众说则主要关注戏剧的社会功用,强调戏剧的民主性质及戏剧在社会变革中应起到的作用。他认为,戏剧是一种民主的艺术,最能表现人生真相,而观众的冷漠与对现实问题的忽视会使戏剧失去其社会价值。[5]
无论是陈瘦竹对社会变革与戏剧关系的关注,还是熊佛西对观众、对戏剧本身不可或缺性的强调,都呼应了“无观众,不戏剧”的共同信念。两位学者虽站在不同的视角,但殊途同归——戏剧不仅是创作者的个人表达,更是与观众共同构建的社会文化现象;戏剧的存与立,必得切近观众。
二、局限而多元:对观众习惯的剖析
陈军在其著作《戏剧内外:中国话剧接受研究》中,梳理了话剧观众特点与成因随历史变迁的变化:早期,观众局限于校园与部分城市新兴市民,颇为小众,随着20 世纪30 年代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推进,各地涌现出诸多面向基层民众的戏剧实践探索,这些努力不仅拓宽了戏剧的社会接触层面,而且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对戏剧的接纳热情与参与度。伴随着曹禺等剧作家的杰出贡献和职业剧团的迅速发展,观众对戏剧的认知层次和欣赏能力也不断提升。至20 世纪40 年代,中国话剧迎来了一个公认的黄金时代,这时期的辉煌成就不仅体现在创作与演出的繁盛,更在于戏剧运动深入人心,观众群的涵盖范围不断扩大,审美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提升态势。[6]105
在当时剧人的眼中,话剧观众既有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局限性,又呈现出个性多元的特质,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发展性。
(一)观演习惯尤未普及
1946 年4 月23 日,《联合晚报》a 中《话剧与观念》一文记录了上月电影、戏曲与话剧的税额数目,其中电影“八千七百万元”,越剧“六百万元”,话剧仅“二百七十万元”,可见当时戏剧观众数量相对稀少,反映出群众对戏剧整体兴趣不高。“话剧所拥有的观众,较之电影,固然是望尘莫及,就是和‘苦是苦来希’的绍兴戏相比,相差也有一倍多,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7]文章还引述著名剧作家曹禺的观点,指出当时中国观众对于话剧的观演习惯尚处于发展阶段,普遍不易接纳较为深邃的话剧艺术形式,导致话剧表现为一种曲高和寡的文艺审美现象。
曹禺说,我们的话剧还没有做到一个话字,中国这许多字,在台上说,台下能懂的只有一千多个字,很少能每一个字听得懂的。这话就指出当前话剧与人隔阂的一大原因。有一次,我座旁一位夫人问我:“活该是什么意思?”天哪!她连“活该”都不知道,活该![2]
关于这一点,《神州日报》b 刊文称,戏剧观众惨淡,主要由于其在中国之历史相对较短,除青年学子和文化水平较高者,大部分人仍将其视为文明戏、“说白滩簧”,中国观众对话剧的接受仅限于足够刺激或足够悲哀的内容。[8]
(二)观演动机复杂多元
中山大学外文系教授、编剧胡春冰曾引爱尔兰诗人奥利弗·戈德史密斯的话:“观众是一个难以取悦的多头的怪物”[9],强调观众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对于观众的类别,也有不同的分类说。有人赞成雨果的说法,将观众分为三类——为感情沉醉的妇女、看人物性格描写的思想家与要求动作戏的一般群众[2]。作家卜少夫将观众分为“为研究欣赏而来的”“为时髦、摩登而来的”和“整个地来消遣的”[10]。熊佛西则说观众到剧场的目的,不外以下四项:(一)因厌烦例行事务而到戏场去开心解闷;(二)看台柱,尤其是漂亮的女台柱;(三)从高尚娱乐寻求心灵满足,尤其是“道德的公平的裁判”;(四)以批评家的态度前去,只求戏剧本身的欣赏。[11]119-120
总的来说,其时观众可根据动机分为“娱乐消遣”与“欣赏批评”两种:少部分观众注重对戏剧的鉴赏和学习,以批评家的态度来观看戏剧,关注剧本、表演、装饰等方面的细节;大部分观众则寻求娱乐,一些将观剧看作一种社交活动,一些追求官能的刺激、情感的共鸣和群体的认同。
另外,有剧人观察到,女性观众在话剧观众中占较大比例,她们对戏剧的情感表达和人物命运的关注程度甚于男性观众,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剧目的创作方向和市场表现。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宋春舫认为,剧本成功与否,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抓住女性观众的喜好。不过,他也希望观众群体的构成能够更加均衡,鼓励更多观众以批判性眼光欣赏戏剧,提升整个观众群体的艺术鉴赏能力和剧场文化的整体水平。[12]
(三)观演方式尚待规范
小说家、剧作家老舍1942 年在《时事新报》发表了《话剧观众须知廿则》,以反语戏谑地描述了观演现场的一系列不文明行为,这些行为反映了当时观众对于剧场这一公共场所应有的礼仪和文化氛围认知上的欠缺。文中提到的一些典型问题包括:咳嗽吐痰、饮食并乱扔果皮杂物、座位混乱、噪音干扰、不当互动、儿童哭闹、迟到早退等。
家事、官司、世界大战,均宜于开幕后开始讨论,且务须声震屋瓦。……每次台上一人跌倒,或二人打架,均须笑一刻钟,至半点钟,以便天亮以前散戏。……入场务须至少携带幼童五个,且务使同时哭闹,以壮声势,最好能开一个临时的幼稚园。[13]
《联合晚报》也载文称,戏剧幕启时,剧场往往充斥着各种杂音,包括吃食声、关于剧情的议论声、交谈声、关于买卖的交流声,乃至对演员私生活的批评声,好一阵才能安静下来。观赏演出时,对于某位演员过于夸张的动作和使用奇怪腔调的台词表达,场下竟会涌起如潮掌声,不知是对表演的赞赏,还是对噱头的追捧。剧情高潮以后,观众不等结尾,便起立欠伸、戴帽、招呼孩儿,纷纷走散去了。[7]
总体上,剧人们的分析表明,当时观众在观演习惯、动机及方式上的特点并非独立割裂的,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他们通过深切观察,描绘出一幅生动立体的观众群像,既看到观众群体在观剧文化普及、动机多元化以及观演行为规范等方面的不足,也洞察到这些特点背后的社会文化及个体心理的深层原因。
三、迎合或培育:对观众态度的取向
在探讨戏剧创作中对观众的态度取向时,出现了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迎合观众,二是培育观众。这两种观点分别代表了剧人面对市场需求和艺术追求的不同立场。
(一)迎合观众的现实考量
一些观点强调迎合观众的必要性:观众的口味和文化水平是关键因素,影响着戏剧的票房和认可程度;观众对戏剧的需求需要被重视,创作者应努力理解观众的社会背景和经济状况,以更好地适应他们的口味。
如编剧陶熊在《时事新报·晚刊》a 中所言:“一个正确的主题和严肃的内容的剧本,只能给少数观众所欢迎,是太可惜了。若因为形式和技巧的帮助,能使多数人欢迎,这剧本所写的主题不是收到了较大的效果吗?这当然是剧作者所乐于做到的了!所以,话剧的危机,电影专业的兴盛,不要怪其他的原因,只要看自己有没有错误!为了观众是永远没有错的,除了那些特殊阶级的观众之外!”[14]
(二)培育观众的艺术追求
另有一些观点认为,戏剧创作者的责任不在于迎合观众,而在于培育观众。提高观众的文化水平被认为是戏剧成功的关键因素。此类观点强调了创作者的责任,即要通过作品引导观众,提升观众对戏剧的理解和欣赏水平。
如《榴花》文学周刊主编、木刻家唐诃在《立报》b 发文称,观众更关注演员面孔与戏剧娱乐性,“不是观众堕落”,而是创作者把艺术当作纯粹商品的缘故;创作者之“堕落”使得观众水准愈发低下,使他们更倾向于关注“表面”而非深层的戏剧内涵。[15]
(三)兼顾与融合的综合策略
迎合的观点多站在强调实际市场需求和观众口味的现实主义立场,培育的观点多站在注重戏剧艺术性和提升观众素养的理想主义立场。创作者与观众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涉戏剧创作中迎合还是培育的讨论,熊佛西综合的观点属于这一辩论中的平衡者。他在《写剧原理》中提出,观众的品位与期望是创作者需要关注的重要因素,迎合观众是为满足他们的需求,使戏剧能够贴近观众,引发共鸣。他明确指出:“‘迎合’并不下流,‘诱惑’才真正下流。”[11]121
但其观点不止于迎合,熊佛西还强调通过一系列精彩演出逐步提升观众艺术鉴赏力的重要性。他主张应立即开始观众的培训工作,并由戏剧家来承担这一责任,不断展示高质量的戏剧作品,即使最开始观众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艺术鉴赏能力将会逐步提高。
“乡巴佬”初看唐伯虎、赵子昂的画,正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除了莫名其妙,还是莫名其妙。这并不是说乡巴佬不能看画,实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看画。假如他虽为乡巴佬,是生在画家之家,常有机会看画,从十八岁看到六十四岁的画,每天至少要看三五张画,这样,漫说唐伯虎赵子昂吓不倒他,就是米淇安菓老(米开朗琪罗)与塞尚,他还要大批评而特批评呢!欣赏戏剧的习惯也是如此养成的。多写好戏,多演好戏,多看好戏,是训练中国观众唯一的方法。但不可希望过急。急,定糟。要慢慢的开导,心理的迎合,切实的实验。……中国的观众现在虽不好,将来终有好的一日,只看当代的戏剧家如何努力。[11]122-123
另外,他还提及观众亦有应尽的责任,在于“指正与批评”。“带诱惑性的戏剧观众应该自动的起来打倒。意味深长的戏剧观众应该自动的尽力拥护。总之,戏剧家有戏剧家的责任,观众有观众的义务。希望各尽其责,各竭其力。”[11]124
马克思曾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16]熊佛西所倡即如此,他主张戏剧创作者既要关注并适应观众的现实需求和审美口味,以保证戏剧作品的市场接受度,同时也要积极履行教育和引导职能,通过优质的戏剧作品来提高观众的艺术鉴赏能力和审美层次。这种兼顾市场需求与艺术深度的做法,旨在建立起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既保障戏剧艺术在商业上的生存空间,又推动戏剧艺术的长远发展和社会影响力的扩大。通过这样的平衡策略,戏剧艺术不仅能与时俱进,也能保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持久的生命力。
新世纪以来,人们的精神生活、社会观念、文化选择趋向多元,大众文化、网络文化异军突起,物质发展与精神世界之间出现的错位,带来了整个社会精神文化结构的变化,思考、思想让位于娱乐、肤浅,成为这个时代的奢侈品。[17]当今的戏剧实践多追求感官化、游戏化和娱乐化,大量采用戏仿、拼贴、即兴表演、多媒体制作等新的方式,话剧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由此带来的观众接受的精神走向是:观众的精神结构更加扁平化、单向度,表现出深度模式的欠缺,内心浮躁,重形式而轻内容,造成意义和价值缺失,审美趣味碎片化、娱乐化和时尚化,后现代语境下大众娱乐消费倾向日益凸显。[6]104-105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和定位观众的角色至关重要。观众,作为戏剧的活力源泉,其角色不仅是被动接受的一方,更是与创作者共同构建剧场世界的合作者。过去剧人对观众的论说提醒我们,创作者在尊重市场规律和观众选择的同时,也应负起培养观众、提升文化生态的责任。这意味着,戏剧艺术家不仅要关注如何通过作品吸引观众,更要致力于通过优质的作品和丰富的艺术实践,引领观众走向更深邃、更广阔的艺术领域,从而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推动戏剧艺术向着更高层次、更深远的意义迈进。
结 语
无论是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戏剧还是20 世纪之后戏剧语境下对“文本”的轻视和对“剧场”的强调,实际都逃不过演员和观众之间的紧密联系,即“看”与“被看”的互动。不能孤立地把剧作家的剧本看作戏剧,也不能把导演指挥下的演出看作戏剧,而应把剧作家的创作、演员的演出、在观众中发生效应的整个精神过程看作一个完整的戏剧流程。戏剧的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观演关系的变化史。20 世纪30 至40 年代中国戏剧界的多元视角揭示了当时对观众作用的不同认识,为当下戏剧界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参照和启示。
当前,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为戏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AI 生成的戏剧作品、AI 辅助的个性化戏剧体验及AI 引领的公共戏剧教育的智能化,都在推动艺术与技术的融合,并促进艺术的普及。未来的观众分析与研究,可能更多地基于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算法,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观众行为的潜在模式,实现对观众未来行为趋势的预测。
在今后的演出创排和运营中,面对观众审美需求的多元化趋势与不断迭代的技术对戏剧及其观众面貌的革新,戏剧界应兼具灵活性与前瞻性,以更高的智慧妥善处理艺术性与市场化、传统与创新、观众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微妙关系,既要注重艺术创新,紧跟时代步伐,通过视觉冲击、即时快感和互动参与等形式满足观众的多元诉求,同时坚守艺术品质,强化作品的人文内涵和深度思考,通过丰富多样的戏剧形式和内容激活观众的审美潜能,提升其文化修养与艺术鉴赏力,搭建更具包容性和互动性的观演平台,重构和谐健康的观演关系,使戏剧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更为丰富且深刻,从而营造一个既能推动艺术繁荣,又能顺应市场需求,并有利于戏剧艺术长远发展的戏剧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丁罗男. 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整体观[M]. 上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15-18.
[2]梦九. 观众[J]. 中国公论(北京),1940(6).
[3]陈瘦竹. 戏剧与观众[J]. 观察,1946(10).
[4]熊佛西. 观众与批评[N]. 民国日报,1946-09-05(6).
[5]陈瘦竹. 戏剧中的民主倾向[J]. 客观,1945(7).
[6]陈军. 戏剧内外:中国话剧的接受研究[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23.
[7]王克. 话剧与观众[N]. 联合晚报,1946-04-23(2).
[8]小立. 从观众说到剧目[N]. 神州日报,1941-03-01(4).
[9]胡春冰. 观众心理[J]. 文艺月刊,1937(4,5).
[10]卜少夫. 关于观众[N]. 中央日报,1933-07-02(1).
[11]熊佛西. 写剧原理[M]. 上海:中华书局,1933.
[12]西方蕋蕊. 观众的成分[N]. 社会日报,1945-07-08(4).
[13]老舍. 话剧观众须知廿则[N]. 时事新报,1942-05-05(4).
[14]陶熊. 观众和戏剧形式[N]. 时事新报晚刊,1947-11-26(3).
[15]唐诃. 不是观众堕落[N]. 立报,1948-03-23(2).
[1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
[17]徐健.“西潮东渐”与“守正创新”:对近十年外国戏剧引进潮的思考[J]. 戏剧艺术,2016(3).
(责任编辑:冯静芳)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高校学位点培优培育专项计划(项目编号:AZ1-9201-24-020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