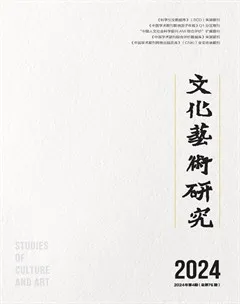《维纳斯》历史意义的再生机制研究
摘要:当代美国非裔女剧作家苏珊- 洛里·帕克斯的代表作《维纳斯》是一部基于真实历史改编的戏剧。该剧通过丰富的文化符号,再现了南非土著妇女巴特曼的一生,重新诠释了历史文本。运用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跨语境解读《维纳斯》中独特的符号体系,揭示出动态文本观的重要性,有助于系统理解该剧的历史意义衍生机制。戏剧文本的创造功能与记忆功能的相互作用实现了历史意义的挖掘,创新的交际模式在信息传递与创造的过程中有效修订了原有历史,空间模拟复现了非裔群体作为边缘人的双重困境。《维纳斯》不仅激发了读者和观众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意识,还鼓励人们审视和思考历史的真实性,从而实现了历史书写的更深层次意义。
关键词:《维纳斯》;苏珊- 洛里·帕克斯;历史意义;再生机制
中图分类号:J83;I7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24)04-0042-08
当代美国非裔女剧作家苏珊- 洛里·帕克斯(Suzan-Lori Parks, 1963—)因其独树一帜的现代写作风格以及对非裔群体生存现状的审视与深思而广受瞩目。作为美国戏剧史上首位获得普利策戏剧奖的非裔女剧作家,她将戏剧作为“创作历史事件的孵化器”[1]5,在其实验性剧作《维纳斯》(Venus, 1997)中,叙说了南非土著妇女萨尔特杰·巴特曼(Saartje Barrtman)坎坷跌宕的一生。国内外学界多从后现代戏剧手法、戏剧主题等角度阐释该部作品。基于学界已有研究,本文聚焦该剧蕴含的纷繁复杂的符号系统,梳理帕克斯书写历史的新方式,探析剧作家是如何令维纳斯的故事在历经漫长岁月后,仍旧可以在现代语境中实现历史意义的再生。
符号学自诞生以来,逐步发展成一种广泛应用于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工具,展现出跨学科、跨语境研究的潜力。20 世纪塔尔图符号学派的领军人物尤里·洛特曼(Yuri Lotman, 1922 — 1993)开创的文化符号学,融合了科学性与人文性,其强大的符号域穿透力为研究具有叙事复杂性的当代戏剧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强调符号的多层次、多维度解释,超越语言符号的表层意义,更深入地关注符号在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深层含义和作用。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通过空间模拟和符号的互动,能够让观众深入体验和理解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性,进而激发他们对历史的思考和反思。将塔尔图- 莫斯科学派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与美国非裔戏剧研究结合,可以在探讨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跨语境阐释的同时,深入分析戏剧文本意义生成机制下的历史挖掘、互动机制下的历史修订以及空间模拟机制下的历史重现。
一、文本意义生成机制下的历史挖掘
尤里·洛特曼开创的文化符号学以意义生成的问题为核心,将文本(text)定义为“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的携带者”[2]19,并将其视为文化符号学的核心要素以及pTFADd98tJ45rmfFBvXnqKjJwemmpj1pB70oIrgG87Q=“文化的基本元素”[3]7。洛特曼在其前期学术思想精华——《在思维的世界里》(Universe of the Mind)中指出文本的三大功能,即文本的信息传递功能(the transfer of the message)、创造性功能(the creative function)和记忆功能(thefunction of memory),这三种功能使文本意义生成机制得以运作。洛特曼认为,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两个参与者即便采用相同的自然语言、同等的记忆维度与共同的准则理解,也无法确保代码的同一性”[4]13。因此,在戏剧文本中,创造功能与记忆功能更能灵活地促进戏剧文本的阐释与传播。
由于黑人对创伤历史的潜意识逃避以及白人对自身错误的有意掩盖,关于萨尔特杰·巴特曼及其痛苦经历的详细记录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对巴特曼的许多学术研究都“集中在其身体上,而人们对她的展览和背景细节知之甚少”[5]189。受白人主导的主流历史叙述所控制,非裔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存在广泛争议。面对现实中的多重阻碍,以及可能被视为“消费巴特曼”的风险,帕克斯在她的戏剧文本中融合了个人的民族情感与艺术追求,将文本作为传递历史意义的载体,从而使其内在结构更为复杂。相对于结构主义的相对封闭性和解构主义的过度颠覆性,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因其强调“文本的功能化与智能化”[2]183,为解读这一作品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在《维纳斯》中,帕克斯通过实验性的戏剧手法突破了传统语言的束缚,充分发挥该戏剧文本的创造功能与记忆功能,通过戏剧形式实现了能指和所指的具象表征和意义共通。
《维纳斯》中,隐喻性的戏剧结构与异质性的戏剧对话相互交织,充分发挥了戏剧文本的创造功能,从而实现了对特定历史段落的深入挖掘,这种处理方式使文本的历史意义获得新生和更新。文本作为“一个满足所有符号可能性的系统,不仅可以传递现成的信息,而且是新信息的生成器”[4]13。文本的成分结构越复杂,其产生意义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在叙事手法方面,《维纳斯》戏剧结构中惯性和非惯性之间的矛盾为挖掘历史提供了新契机。帕克斯曾对该剧非常规的戏剧结构予以解释:“通过每一行文字,我都在重写时间线——创造历史,这段(历史)就在那里,一直在那里,但尚未被窥探到”[1]5。有别于常规的传统戏剧的顺序排序,该剧采用了反常规化的降序场景排序,戏剧由第31 幕开始,到第1 幕结束,倒叙结构破坏了剧情惯性的发展规律,增加了剧作的信息量,也映射了这段未被窥探的历史将以新颖的方式再次进入读者和观众的视野。此外,在戏剧的开篇和结尾,死去的维纳斯以相同的方式出现,该循环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过去与现在紧密联系。这一设计突破了传统戏剧舞台对时间与空间的桎梏,在同一文本中达成了穿越不同时空语境的协作。循环的舞台指令使意义的解释得以持续进行,提醒人们审视历史的同时不要忘记现实的立足点。同时,这也隐晦地指出白人对非裔群体造成的创伤是长期存在且难以消解的。
在语言风格上,《维纳斯》戏剧对话中语言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成为非裔群体遭受迫害的屈辱历史意义再生的语言表征。“符号圈以其异质性为标志,填充符号空间的语言是多种多样的。”[4]125作为文本符号,《维纳斯》文本空间中的戏剧语言表现形态多样,不仅有字典中查阅不到的词语,还包含了音乐术语、医学术语、黑人常用俚语等,构建出多个异质话语层,为挖掘历史提供了诸多素材,其中最具创新性的戏剧语言表现形式是帕克斯的文字游戏。例如,当维纳斯向马戏团老板讨要薪酬却惨遭拒绝时,她用“Gimmmmmie!”替代了“Give me!”的常规表达[6]95。帕克斯在吉格茨(Jiggetts)的采访中解释了在戏剧中运用这种非传统语言进行表达的目的,“这不仅仅是人们所谓的‘黑人英语’与‘标准英语’的对比……试图非常具体地表达人物的情感变化”[7]。她通过独创的偏离语言规范的话语方式,将文字符号转化为情感表征的符码,实现了情感传递。这种方式投射出维纳斯面对资本掌控者的丑恶嘴脸时所产生的愤怒情感。在该剧中,类似这样非常规语言的表达频繁出现,既是对已有历史的重新拼接和改编,也是对所传达情绪价值的扩容,同时增加了读者与观众对人物情感把控的难度。解读文学文本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翻译活动,“翻译是意识的主要机制”,但因为“符号域中的不同语言在符号学上是不对称的,即它们没有相互的语义对应关系,所以整个符号域可以被视为意义的生成器”。[4]127 在《维纳斯》中,非常规语言表达虽加剧了符号圈不匀质性,为文本解读带来了困难,但在解码与翻译的过程中,读者和观众对剧作家想要传达的信息进行再考量,反而促使文本可阐释空间的延展,推动了历史意义的再生。
此外,维纳斯的身体作为一个可独立迁移的象征符号,在不同语境下保存原有信息并赋予新的含义,成功实现了对原有记忆的重塑。这种处理方式促成了《维纳斯》这一文本的记忆功能,激发了非裔族群对这段历史意义的反思和更新。“文本不仅是新意义的生成者,也是文化记忆的凝聚者。”[4]18为印证文本记忆功能的跨语境阐释能力,洛特曼曾以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巅峰之作《哈姆雷特》为例,解释文本记忆功能的持续性影响:“尽管我们可能忘记了莎士比亚和他的观众们所知道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那个时代以来我们所学到的东西,这就是赋予文本的新意义。”[4]19 这种解读方式为分析当代戏剧文本中的助记功能提供了可能性。
在《维纳斯》中,帕克斯将维纳斯的身体塑造成对该历史产生记忆的媒介。同时,该媒介本身也具有符号性质,“通过象征载体实现的符号化是文化记忆行为与结果的核心特质”[8]。在剧中,身体符号使文化记忆的象征以戏剧的方式呈现。首先,置身于资本营利的语境中,维纳斯的身体成为流通的活体资本。畸形秀的文化现象19 世纪曾在西方风靡一时,这种表演貌似为畸形症群体提供了谋生方式,实际上却是极具剥削性的非人性化行为。观众们认为锁在笼子里供人观赏的维纳斯是“可耻的、有原罪的”[6]87,畸形秀老板也时常对维纳斯恶语相向,但是他们在嫌弃辱骂她的同时,却又千方百计地从她身上获利。这种两面派的行为映射出白人对维纳斯身体的欲望投射,暴露出白人对非裔群体显性和隐性剥削的实质,揭示了受益者对金钱与欲望的渴望是建立在泯灭人性的历史现实之上。当资本掌控者意识到“(观众)愿意为观看一个拥有硕大臀部的黑人付钱”[6]87 这一商机时,为使利益最大化,他们迎合观众的猎奇心理,又推出了“多花多得”的营销策略:“如果我多付一点儿钱,我就能多看一会儿,如果再多付一点儿钱,我就能站在特别的地方观看。”[6]24 久而久之,维纳斯的身体任人摆布,不再受个人的支配,成为符号化的产物和白人操控的对象。
随着剧情的发展,维纳斯所处语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科学”的语境中,她的身体在负载符号的同时,成为种族主义者刀下的活标本。当她被转卖到男爵医生手中时,身体作为一种意象符号,其所处语境开始变化。她曾反复询问男爵医生:“爱我吗?”男爵回应:“我爱你。”但随即又补充道:“我喜欢你!当然,只是在我特定的圈子里。”[6]162 这个“圈子”即男爵的“科学领域”。他利用维纳斯的爱与信任,企图实现成为“解剖学界哥伦布”[6]191 的幻想。在“伪科学”的保护下,维纳斯的身体再一次被公开在大众视野之中,男爵医生及其同伴们不仅对维纳斯的身体进行测量,而且还实施了侵犯,在这具身体上再度留下了罪恶的痕迹。这种“伤痕和伤疤代表的身体记忆比头脑的记忆更可靠”[9]280,令这段创伤史在时间的尘封下,在非裔群体的代际传递中不断引发“疼痛”。因此,随着在不同语境中的迁移,文本中身体象征所映射的记忆功能,在不同时间与地点均保持了文本与代码的多样性,使读者与观众切实了解到文本以及文本外所发生的历史实践与记忆,达成了文本可阐释空间的延展。在帕克斯的戏剧实践中,艺术手法的创造功能及维纳斯身体符号的记忆功能在同一文本中协同运作,“区别只是方法论上的,因为实际上,所有功能都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无法独立运作”[10]9。它们共同将非裔群体在历史上缺失的一页以独特的形式展现在读者与观众面前,通过在文本这一有机生命体中的相互作用实现了历史意义的挖掘与更新。
二、文本互动机制下的历史修订
洛特曼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提出了“我—他/ 她”型交际模式("I-s/he" system)和“我—我”型交际模式("I-I" system)的概念。在“我—他/ 她”型交际模式中,假设“我”自己拥有信息,而“他/ 她”是信息的接收者,这种模式通常在文化交流中占主导地位,但也存在理想化和局限性。基于雅各布森的交际理论,洛特曼更深入地探讨了“我—我”型交际模式,即向已经知道信息的人传递信息。虽然这种模式看似与“我—他/ 她”型相矛盾,但实际上二者有共通之处。通过这种交际模式,创作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信息传递不对称性成为意义创新的机会。
在“我—他/ 她”的交际过程中,《维纳斯》中蕴含的多重符号被个性化解读,打破了原有意象符号的简单物质内涵。“我—他/ 她”交际模式着重信息的传递功能[2]126,剧作家通过输入大量外来信息,使戏剧呈现多层次的符号体系,这些符号帮助读者和观众熟悉历史事实,并扩展其知识储备。然而,由于剧作家与读者、观众之间存在知识和信息的不完全对等,个体理解上的差异使符号编码具有了创造性。因此,读者和观众对戏剧的解读并非简单地还原了剧作家帕克斯作为信息发出者想要传递的意义。他们在参考符号本身的含义的同时,经常会增加符号编码的丰富性,进行多重解释。这样做不仅传递了基本的信息,还弥补了历史意义中被忽视或误读的部分。这种多重阐释的过程使得戏剧在传达历史意义的同时,也呈现了创造的可能性以及读者与观众的主观参与。
首先,《维纳斯》中,萨尔特杰·巴特曼的艺名“维纳斯”在表现明显的戏讽意味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个具象生动的维纳斯形象。在罗马神话语境下,维纳斯是美的女神。然而,当这种本该受人仰望的魅力投射到戏剧中的维纳斯身上时,却被解读为对非裔女性充满偏见且带有色情的想象,体现了白人对非裔族群的固化印象。与此同时,帕克斯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维纳斯,她渴望被爱、被抚摸、被亲吻。这种意象的所指成功打破了原有刻板的历史印象,向读者和观众传递了一个渴望爱情并勇于表达爱情的维纳斯形象。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丰富了历史的意义,使人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和体验非裔群体在历史中的情感和人性。其次,帕克斯将戏剧物体“巧克力”作为历史意义的具体指向载体,映射了维纳斯的悲剧。一方面,马戏团老板采用侮辱性的方式将巧克力作为给予维纳斯的奖励,他“把零食放在她的脚边,看着她喂食”[6]101,这一戏剧物体传递了受益者对表演者虐待与歧视的信息。另一方面,巧克力可以被解码为甜蜜与脂肪并存的商品,它使人们在获得满足和愉悦的同时,也陷入放纵和沉迷。男爵与维纳斯初次见面时赠予她“红色心形盒子巧克力”[6]137,在这里,巧克力并不是爱情的象征,男爵从未真正爱慕过维纳斯,“就像维纳斯为获取快乐而沉迷于巧克力一样,伪善的男爵将维纳斯视为一种为快乐而消费的商品”[11]74。在甜言蜜语及巧克力的诱惑下,维纳斯逐渐丧失对情感与人性的判断。她对巧克力的沉迷隐喻了“对自己身体的消耗”[5],也同时暗示她无法摆脱被压迫和奴役的命运,最终沦为供他人消费的商品。传统语境中代表甜蜜浪漫的巧克力使读者和观众超越其本意,通过阅读的体验和反思,产生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凸显了这段历史的悲剧性走向。剧中另一个戏剧物体“铁链”的寓意也超越了原有语义的相关性,创造出更多的信息。在剧中,维纳斯一直被铁链所束缚,她对金钱与名声的渴望成为一条无形的铁链,将她拽向深渊。她渴望在殖民者的土地上实现自我价值,然而身处剥削与权力不平衡的关系中,这种遐想本就是不切实际的。此外,伟大的存在锁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是十八世纪欧洲神学对万物自上而下的分级,位于最底端的是岩石以及无生命的物质。剧中畸形秀老板称维纳斯及八位畸形秀表演者为“上帝存在锁链中最底端的九位”[6]60。帕克斯利用这一概念隐晦传达了白人对非裔族群及残障群体的蔑视。她采用碎片化的话语设置打破了语言布局规律,“八大奇观”反复合唱的“铁链、铁链、铁链”[6]59 使这一意象在被读者和观众解读时衍生出新的意义。舞台上,反复响起的关于铁链的吟唱“呈现了‘存在锁链’的神学概念,也让观众联想到被奴役的维纳斯”[11]。因此,这一意象符号在互动中被阐释为被奴役和被轻侮,戳穿了在畸形秀历史上,资本掌控者为牟取暴利而编织的谎言。最后,“铁链”隐形的奴役在舞台上被显化为有形的囚禁,“维纳斯再次被囚禁,不是笼子,而是像狗一样被拴在院子里”[6]59。此时,铁链永久地拴住了维纳斯的命运,它从无形到有形,含义在互动中逐层递进,成为维纳斯悲剧的终结。
相较于“我—他/ 她”交际模式的传递功能,《维纳斯》中的附加代码在“我—我”的交际模式下充分发挥其创造功能,更有力地将沉默叙事转变为有声叙事,将单薄的历史叙事化身为更丰满的历史叙事,实现了历史意义的修订。“我—我”交际模式指“受试者向自己,即向已经知道信息的人传递信息”,这一模式主要是“引入第二个补充代码的结果”[4]22。基于“我—他/ 她”型交际模式,读者和观众已经对维纳斯的故事背景有了简要了解。然而,介于对维纳斯历史记载的片面性以及剧中主线情节的局限性,对剧作的意义理解仍略显封闭。因此,借助“我—我”交际模式来解码剧作家为该剧引入的一系列附加代码,可以为戏剧赋予补充的意义。这种方法帮助信息接收者解构他们心中原有的信息框架,从而获得新的认知。
“戏中戏”作为一段附加的虚构副线故事,其中所包含的信息为读者和观众提供了解码原情节以外的附加代码,并获取具有补充价值的信息。《维纳斯》的“戏中戏”里的一对英国情侣是维纳斯与男爵的缩影。在“我—我”互动下,读者和观众得到耳目一新的信息,作为旁观者来观戏的维纳斯同样实现了与自我的互动。历史上,维纳斯始终作为一个失语的表演者供他人凝视,但当她从剧中脱离而成为“戏中戏”的一名观众时,她看清了残酷的真相:为满足未婚夫的猎奇心态,“戏中戏”里的未婚妻伪装成维纳斯来吸引对方,重获未婚夫的爱。通过“戏中戏”这一附加代码,读者和观众可以在与自我交际的过程中,补充除“我—他/ 她”交际之外原文本中的内隐信息。其一,男爵对维纳斯的爱与“戏中戏”里未婚夫的爱一样具有伪装性和欺骗性。其二,白人认为非裔女性的气质可轻而易举地被模仿与伪造。因此,在以白人为主导的场域下,维纳斯想通过外表获得认可的愿望是难以实现的。不同于在空间中传输信息的“我—他/ 她”交际模式,“我—我”交际模式往往是在时间中进行传输。同作为非裔女性,帕克斯通过“戏中戏”的附加代码与维纳斯实现了跨越时间的对话:权能不平衡下,本就不存在公平,唯有认清真相,非裔女性才能展露其独特气质。此外,在原有历史记载中,“没有任何有关维纳斯爱上男爵的记录”[12]43。帕克斯通过添加与原历史文本无关的情节信息——“男爵与维纳斯的爱情故事”,再次为读者和观众重新解读历史提供了附加代码,成为其书写历史的新方式。历史霸权下有关维纳斯的刻画囊括了长期以来白人对非裔女性固定模型的积累:“自奴隶贸易时起,黑人女性的身体便一直是白人凝视目光下的欲望客体,是原始蒙昧的性欲化符号。”[13]此类固定文本建模存在种族偏见,因此附加代码的介入为帕克斯“修订”历史意义提供了文本空间。帕克斯打破维纳斯的刻板形象,读者和观众自身的原有记忆与剧中呈现的灵动鲜活的维纳斯之间的巨大反差成为新意义迸发的契机。
回溯剧中两条交际线路,《维纳斯》中多元的意象符号以及虚构的附加代码与主线真实的历史故事多重杂糅,协同实现了文本的互动机制。“艺术不是从‘我—他/ 她’系统或‘我—我’系统中诞生的”[4]32。该剧的戏剧艺术在两个系统中共生,在信息传递与创造的过程中修订了原有扁平化的历史,翻转了维纳斯在历史上长期失语的状态,填补了原有历史书写的空白,达成了历史意义的修订。
三、空间模拟机制中的历史再现
作为意义再生的手段之一,文本的空间模拟机制可以通过对现实空间形式的模仿实现。洛特曼拥有独特的时空观,他将物理世界抽象化,将空间与文化相联结,指出“文化与空间虽为本质上不同类型的存在,但具有内在的对应关系”[14]。基于这样的空间模拟机制,洛特曼将符号外推至更广阔的符号空间,诞生了其核心观点“符号域”(semiosphere),即“语言存在和运作所必需的符号空间”(semiosphere)[4]123。在符号域中,二元对立的中心(center)与边缘(periphery)以及边界(boundary)的存在,令有限的文本空间语言呈现出对文化世界图景(culture's world-picture)的无限模拟,实现抽象现实世界的具象化再现。
《维纳斯》这部富含艺术性的戏剧文本,在具有交际性能的同时,也兼具空间特性。作为意义再生的手段之一,文本的空间模拟机制能够通过对现实空间形式的模仿来实现文本中的空间建模。洛特曼的文化空间观深化了文化符号学的核心理论,即“符号域”,这一理论不仅具有抽象性质,还具备实际的空间意义。因此,在这样既具象又抽象的符号域中,“中心”“边缘”的对立以及对“界限”的穿越交错地分布在戏剧文本空间中,在《维纳斯》有限的篇幅与框架下再现了现实空间与抽象空间中非裔群体的历史记忆。
在现实空间层面,维纳斯在“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位移以及两者间存在的鸿沟,真实呈现了非裔女性的生存困境。“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是符号域中最为本质的特性。尽管这种符号域具有抽象性质,但“绝不意味这个空间本身不具备实际意义”[2]39。在《维纳斯》这一戏剧符号域中,维纳斯的第一次空间位移是从非洲来到英国,差距巨大的社会空间景象揭示出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社会环境的侵扰与破坏。维纳斯在被贩卖之前曾是非洲种植园的普通奴隶,她深知非洲的土地无法使其获得名利,因此,当白人商人向她描绘“铺满了黄金”[6]37 的英国大街时,长期存在的“边缘”地带贫困使她立刻被“中心”地带虚幻的金钱所迷惑。维纳斯被引诱的原因归根结底是“边缘”与“中心”社会经济极不平等的历史事实。然而,当维纳斯到达“中心”时,她发现英国的现实与白人商人所描绘的金碧辉煌大相径庭。尽管到达了中心地带,但她所面对的环境比边缘地带更为糟糕。“空间建模可以成为一种表达非空间思想的语言”[4]150,在帕克斯的笔触下,维纳斯的首次空间转换成为对残酷现实的揭露,即:“中心”的美好并不属于“边缘”群体。维纳斯的第二次位移是在“畸形秀舞台”与“舞台背后”间的穿梭。畸形秀舞台是白人主导的中心地带,白人商人曾向维纳斯许诺:在这里,“人们看你。人们拍手。人们给你金子”[6]37。因此,维纳斯幻想自己在这一中心地带,将以“非洲舞蹈公主”[6]30 的形象成为焦点。然而,来自边缘地带的人群很难改变在中心地带受到歧视与迫害的状况。舞台指令提示,当维纳斯首次出场时,“站在半明半暗中”[6]66。虽然她已脱离了原有的“黑暗”,但“半明半暗”的舞台空间预示着她第二次阶级跨越的失败。“非洲舞蹈公主”最终被关在舞台中央的笼子里,遭受观众的讥笑。“边缘”与“中心”的差异在于“价值较低的社会群体被安置在边缘”[4]140。作为白人眼中“上帝失败的作品”,维纳斯虽然来到了“中心”地带,但因价值较低,仍旧被安置在不受尊重与保护的边缘地带。当她走下舞台时,等待她的是更为压迫的生存空间。她向畸形秀老板乞求道:“给我更多的食物,呃,锁上我的门,呃,并且给我新的衣服。”[6]91 她不停地埋怨:“在我睡觉的时候,他们醉酒进来。”[6]96 这些表明了维纳斯深陷备受挤压的生存空间。帕克斯通过呈现维纳斯在舞台中央以及舞台背后的遭遇,再现了边缘群体举步维艰的生存空间。剧中的另一处空间位移复刻了维纳斯自始至终处于白人男爵控制下的生活图景。她天真地以为跟随男爵离开畸形秀后,会获得尊敬与自由,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男爵虚伪的爱情不会让她梦想成真,也不会令其成功进入中心地带。在男爵多次诓骗下,维纳斯再次经历空间位移,站到了医生的测量台上。她被人利用,直至被解剖,从未真正融入以白人男爵为主导的中心地带。“文化模拟的核心在于提取文化对象中具有共性的抽象元素”[14],帕克斯从众多非裔女性中提取维纳斯作为具有共性的代表,完成对试图进入中心地带却饱受欺辱的非裔群体的侧写。
在抽象空间层面,维纳斯对自我“界限”的不断跨越再现了非裔女性的身份困境。基于符号域的抽象性质,“边界”不仅能够被实际地感受,而且也可以被抽象地理解:“符号学个体化的主要机制之一是边界,边界可以定义为第一人称形式的外部界限。”[4]131 维纳斯对“身份界限”的不断跨越勾画出了以维纳斯为缩影的诸多非裔女性的心理困境。起初,维纳斯作为来自非洲的异国舞者,对其非裔女性身份保持认同与自信。白人商人对她的许诺使她更加坚信自己在畸形秀的舞台上可以“一夜之间成为公主”[6]38。但一切幻想却在长期压榨与欺辱后逐一破灭。在畸形秀所遭受的身心霸凌成为一段难以抹去的痛苦回忆,这样的创伤记忆在她身上谱写的“身体文字会毁坏其建立身份认同的可能性”[9]282,令她对自我身份界限认知逐渐变得模糊。最终,在法庭上,她恳求:“如果我有不好的标记,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清除它?……我可以洗去我的黑暗印记。我黑着身子来到这里,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白着离开。”[6]123 这时的维纳斯已彻底跨越非裔女性对个人身份认同的界限,她憎恶自己的肤色,误认为伤害自己的白人是“最好最诚实的人”[6]123。尽管她最后短暂逃离畸形秀,但是长久的伤害难以让她穿回原来的界限,拥有曾经的自信。最终,她被爱情蒙蔽双眼,默认男爵的冷漠和虚伪,致使身份彻底流散。维纳斯自身界限的不断跨越最终导致她走向死亡。帕克斯在重塑这一故事时,将维纳斯认定为一个复杂人物。在与蒙特(Monte)的采访中,她说道:“我可以把维纳斯作为一个受害者,为她写一个两小时的个人史诗。但是她是多面性的,她无辜、美丽、聪慧,但的确也是同谋。我所写的世界就是我经历的世界……这只是我们现实的一部分。作为黑人,我们被鼓励狭隘并简单地解决问题。但我们应该得到更多。”[12]39 这样具有矛盾感的人物塑造,以及最终朝向消极“界限”的跨越看似令维纳斯成为杀害自己的“同谋”,但实际上,在这一戏剧人物的符号域中,她对“界限”的穿越展现了主动与被动并存的复杂性,隐晦地复现了作为非裔女性在遭受殖民者的掠夺与压迫时所面临的心理选择困境。因此,将洛特曼对“界限”的揭示迁移到具体的文本分析实践时,可以发现剧中人物在心理空间界限穿越的多个节点,进而觉察剧作家已悄然以艺术文本的形式让非裔族群聚焦到更为深刻的问题上:解决种族问题不应止步于表面,而需要正视历史的多面性,找到问题的根源,这才是书写历史的终极意义。
以洛特曼对艺术文本空间的延展性视角,跨语境分析《维纳斯》中的空间性,作品的文化模拟被扩展至更为广阔的世界图景。在《维纳斯》这一符号域中,以维纳斯个人建模为出发点,中心与边缘的显著差异与人物身份界限的不断跨越、相互作用、彼此关联,扩散地模拟出现实世界中非裔边缘族群在以白人为主导的中心社会中面临的双重困境。剧作家在该空间模拟的引导下,对情节与命运的意义进行了阐释,实现了有限文本的无限释放,达成了该段历史图景的意义复现与迸发。
结 语
在《维纳斯》中,帕克斯通过戏剧形式将维纳斯的一生再度引入公众视野。作为一位非裔剧作家,她承担了“重建历史事件,以填补由于排除任何非裔美国人的存在而造成的历史缺失或漏洞”[15]的使命,创作了这部具有复杂叙事性的现代戏剧。本文将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跨语境地应用于该戏剧文本研究中,发现动态文本观可以引导读者和观众系统理解该剧中不同层级的艺术结构与象征的协同运作。剧中创新的交际模式有效传递了剧作家的个人情感与艺术追求,通过绘制“世界图景”的空间模拟,再现了非裔群体作为边缘人的困境,以维纳斯为代表的非裔女性身份的离散,实现戏剧文本意义在时空上的拓展,使原有的历史意义得以衍生和复现。作为“历史事件的孵化器”,《维纳斯》不仅激发了读者和观众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意识,而且鼓励人们回望历史,正视历史,思考历史的真实性,以实现历史书写的最终意义。
参考文献:
[1]Parks, S. L. The American Play and Other Works[M].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1995.
[2]康澄. 文化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M].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6.
[3]Tamm, M., and T. Peeter, eds. The Companion to Juri Lotman: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C].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2.
[4]Lotman, Y. M.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5]McCormick, S. "Witnessing and Wounding in Suzan-Lori Parks's Venus"[J]. MELUS, 2014(2).
[6]Parks, S. L. Venus[M].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1997.
[7]Jiggetts, S., and S. L. Parks. "Interview with Suzan-Lori Parks"[J]. Callaloo, 1996(2).
[8]余红兵. 文化记忆的符号机制初论[J]. 山东外语教学,2019(5).
[9]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与变迁[M]. 潘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0] Tamm, M. "Introduction: Juri Lotman's Semiotic Theory of History and Cultural Memory"[M]. Culture, Memory and History: Essays in Cultural Semiotics, Ed. M. Tam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9.
[11] Kornweibel, K. R. "A Complex Resurrection: Race, Spectacle, and Complicity in Suzan-Lori Parks's Venus"[J]. South Atlantic Review, 2009(3).
[12] Griffiths, J. L. Traumatic Possessions: The Body and Memory in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and Performance[M]. Charla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9.
[13]隋红升,周宁. 《维纳斯》对非裔女性身体刻板形象的解构与女性气质重塑[J]. 当代外国文学,2021(2).
[14]康澄.“空间模拟”思想: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一种独特方法论[J]. 当代外国文学,2023(3).
[15]Schafer, C. "Staging a New Literary History: Suzan-Lori Parks's Venus, In the Blood, and Fucking A"[J]. Comparative Drama, 2008(2).
(责任编辑:冯静芳)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 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重点项目)“当代美国非裔戏剧中种族困境的数字人文研究”(项目编号:L21AWW002)的阶段性成果。